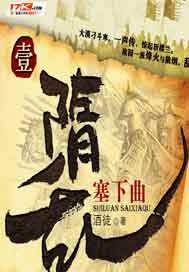宗教改革以前,西欧地区发生了两次叛离教会的事情。
第一次为法兰西部落南部异端阿比尔派叛乱;第二次为二百年后波西米亚与罗马教会的分离。
第一次法兰西南部异端阿比尔派被罗马教会被血腥镇压;第二次波西米亚成功抵制了罗马教会及日耳曼的攻击,且还入侵到日耳曼部落内,成功叛离罗马教会。
真正对罗马教会产生影响的是第二次,也正是这次波西米亚人成功抵抗住了日耳曼部落及十字军的武力清剿。
这次叛离罗马教会及抵抗住武力清剿,且还以武力进入日耳曼部落,导致的结果是罗马教会同波西米亚人新教达成协议。使得西欧其它地区的新教得以继续传播且可以讨论,为日后所谓路德的宗教改革提供了现实基础。
不得不说波西米亚人及波西米亚新教教士胡斯的贡献,远大于路德的宗教改革。
罗马教会及教士阶层的腐化堕落,其权威信用已经不能够使西部欧洲一带信仰归于统一。
而对于罗马教会的反抗,以各部落酋长同罗马教会的斗争最先开始。
即以宗教大会的权力,代替罗马教会教主的唯一至高无上的权力。
至此罗马教会虽然有着组织严密的等级制教士阶层,然而再也没有了中古时期的权威。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以所谓的异端开始发力,促成了宗教大会的最高权力地位。
而宗教大会为世俗酋长和罗马教会相抗衡的地方,这是一种制衡罗马教会权力的手段。
也正是这种制衡,使得所谓的异端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也为后来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这种改变又出现在罗马教会控制最强大的地方,也是掠夺最严重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日耳曼部落,只因日耳曼部落大汗及主教遵从罗马教会的教规最为彻底。
公元1520年秋天,维滕贝格神学院的神学教士马丁·路德带领神学院带领未来的教士,去城外焚毁了罗马教会颁布的法律教规。
且马丁·路德教士并焚毁了罗马教主对他所颁布的命令,以示其不服从罗马教会。
所谓异端的兴起,是与罗马教会势力太过于庞大,且教士阶层腐化堕落有关的。
与其说是部落酋长及民众对此反感,不如说是教士阶层内部的利益不均衡,导致教士内部出现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
而教士阶层内部利益的不均衡,导致就教义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教派。
一派既得利益派,享受最大的利益且有实力;
而另一派属于底层,只能够提出符合顺应世俗酋长和各部落民众利益主张。
所以就有了实力派把非实力派称为异端的事情,也就有了打击异端的事情。
在宗教改革之前,法兰西部落南部出现的所谓异端被镇压,但是波西米亚的异端没有镇压掉。
这样带给罗马教会和各世俗酋长现实威胁,如何来平衡这一突变的局势。
最后的结果是世俗酋长和中层教士以分权制衡罗马教会,让宗教大会的权力置于罗马教主权威之上。
这是一种妥协办法,但不是最终解决办法。
罗马教会权威丧失了一些,各部落酋长的腰杆硬气了一些,一些中层教士也获得一些利益。
但是各部落民众即奴隶及底层教士是没有获得的,所以所谓的异端还是迅速的扩展开来。
在这一系列的平衡过程中,罗马教会教士阶层利益没有受太大损失,各部落酋长得利,中层教士也获得一部分利益。
各部落奴隶及底层教士成为推动这一转变的力量来源,然而却没有获益。
这也是最后导致宗教改革的本质原因,因为所谓的异端有其生存的土壤,而日耳曼部落成为了宗教改革的火、药桶。
马丁·路德教士成为手持火柴点火的人,没有马丁·路德会有狗蛋·路德、或者狗剩·路德。
罗马教会教主和各部落酋长对法兰西南部异端的血腥镇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波西米亚信仰新教,且抵抗住罗马教会和日耳曼部落的入侵,导致宗教的首次变革,即宗教大会的权力置于罗马教会教主之上,且西欧其它地区的新教可以存在。
要按照真实历史来书写,应该这才是真正改变的开始,但是话语权在西方手中,不可能大书特书匈奴人的后代的。
所以就有了路德这么一个人,而不是波西米亚或者匈牙利的某个酋长成为勇士,维护了新教的革命果实。
西部欧洲拥有现实的土壤,因为新教所宣传的只要你信仰耶稣,在哪里都可以信仰,家里、马棚等地方,不必非得到教堂经过教士牧师神父才算是真的信仰。
这种主张严重挑战了罗马教会的权威,也难怪罗马教会会把新教当成是异端,这是砸教士既得利益阶层的饭碗来了。
大家如果都可以自己信仰了,那要教士阶层做什么?
教士阶层中的税收、封地到底还能不能够存在了,各部落酋长还听不听话了。
新教的主张受到西欧地区各部落奴隶的欢迎,因为彼时奴隶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受教士的管控。
出生要做浸礼要收钱,结婚要念几句要收钱,去世要念几句要收钱,还有一系列收钱的项目。
你要说没钱,给东西也行;你要说不做,你不做你就是异端,对待异端就是烧死你。
西欧各部落奴隶不仅要经受分封贵族的盘剥,还要经受罗马教会教士阶层的盘剥,这是两个系统。
所以当新教宣传之后,有其深层次的土壤能够使这种主张扎根,因为这切实的符合各部落大多数奴隶的利益。
十六世纪的日耳曼部落与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这种差别是一个是由两三百个血缘氏族组成的部落,另一个是跨越到类国家层次的国家。
十六世纪的日耳曼部落,法兰西人称为诸日耳曼部落,都是所谓的公、伯、主教教区、牧师领地。
例如,纽伦堡、奥格斯堡、法兰克福、科隆等,同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等,都为独立的氏族或多氏族部落。
另外还有所谓的骑士,领地仅有城堡一座及附近的几个村庄,这也是独立的地盘。
至于日耳曼部落大汗,虽然名号比较响亮,但是既无财力,也无军队。
这样的境况之下,如何能够使两三百个氏族部落信服呢?
在马丁·路德出生的时候,当时日耳曼大汗穷到常常赶着牛车到教堂蹭饭。
所以说不能够以中华的视野去看待其它地区的历史,盖因为中华的历史发展比较超前。
19世纪西方开始编撰历史的时候,多以中华的历史为其标杆来修饰。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如何修饰与粉饰都会还原到本来的面目,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十六世纪日耳曼部落的实权,其实掌握在这些小部落酋长的手中。
而在这两三百个小酋长中,又有实力比较强大的七个酋长和大主教,被称为七选候。
选候是自十三世纪以来,能够推举大汗的酋长。
七个选候中有三个是大主教,拥有莱茵河一带领地,即美因茨大主教、特里佛斯大主教、科隆大主教。
莱茵河以南为公、伯之领地,东北为勃兰登堡和萨克森两个选候领地,再加上波西米亚酋长也为选候。
其它不是选候的酋长也有实力比较强大者,例如,符腾保、黑森、巴伐利亚及巴登。
各个小部落在十六世纪以后,互相兼并,领土逐渐增加。
这个类似于春秋时期,先是争霸,然后大部落兼并小部落,最后实现统一。
只不过德国的领土本就不大,如果按照春秋来比较应该放到整个欧洲地区。
如果要就当地的一个部落统称的话,应该和夏商或尧舜禹时期进行比较。
同样了解欧洲地区的历史,或者欧洲地区某一个部落的发展历史,也可以让我们推断了解尧舜禹或者尧舜禹以前,夏商周时期历史发展演化。
当十五世纪末年十六世纪初年时期,日耳曼部落遵从中古罗马教会的仪式达到了顶点。
这也说明了一点,当日各小部落酋长及教士洗脑洗的比较成功。
各部落教徒赴各处圣地拜谒的人络绎不绝,多时能够达到千人。
这些去圣地拜谒的人多为所谓的贵族教士,奴隶是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拜谒且捐钱的。
盖因宗教的仪式收费及分封租税及徭役,已经束缚了这些奴隶一辈子都得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生死死。
日耳曼部落内各酋长无不以收集圣人遗物为兴趣,以为如此可上天堂。
例如,萨克森选候就收集了五千种圣人遗物,据说有摩西之棒、圣母之纺线等;
美因茨大主教收藏更加丰富,收藏圣人尸体42具,大马士革附近地上之土一堆,这位大主教相信这是上帝造人之初的土,不是一般的土。
然后呢?
以死人之遗物来向奴隶显摆,我们统治你们有合法性,老老实实的去做奴隶吧!
这些酋长不修自身灵魂,而仅图形式外表之行为,以为去礼拜堂念几句、给教堂捐助、崇拜遗物、拜谒圣地就可以让自己上天堂。
其实这是一种通过形式上的依靠,来掩盖现实的恶行的一种行为。
如果真正行善,就不会有现实行恶的事情,真不知道那个时期的耶稣是不是讲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而彼时的佛教可是讲究众生平等,所谓基督教、阿拉伯教都是由氏族向部落过渡时期的一种思想粘合剂,有其历史作用,但都过于狭隘。
造纸术及印刷术的传入,使得欧洲地区能够识字的人逐渐增加,且书籍也可以广泛的流通。
这样一种结果就使得礼拜堂或教堂不再是唯一可以获得宗教知识的唯一场所,各地效仿阿拉伯教建立神学院,以教授未来的教士。
有人的地方就有讨论,有讨论的地方就有比较,有比较就会产生差距,有差距就会产生失落,有失落就会产生反抗的动力,有反抗的动力就会产生变革。
在马丁·路德焚烧罗马教会法律及教规前,对于中古教会的仪式、法律、教规就有讨论与思考。
当时的底层教士认为,教会注重仪式、偶像崇拜这些外表的行动及礼节,并不能够使教徒死后上天堂。
而应该更加的注重善行,这样才能够获得耶稣的宽恕,死后才能够上天堂。
盖彼时教会腐败堕落到极点,为了修建豪华的大教堂,就在各部落搜刮钱财,宣扬只有教士可以为教徒赎罪。
最后发展到售卖赎罪券的地步,无论你干了多少邪恶的事情,买的越多罪孽洗的越干净。
后来马丁·路德的行为,只是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导、火索,或者是最先点燃其这场火的手持火柴者。
盖因为彼时世俗酋长和教士阶层对奴隶的压迫已经到了临界点,而教士阶层的势力比世俗酋长还要大。
所以干柴烈火之下,马丁路德成为第二次推动宗教改革陈胜吴广。
第一次宗教改革以波西米亚匈奴人的后代威胁,迫使罗马教会达成妥协,即宗教大会的权力置于罗马教会教主之上。
当时教会的神学院内,就基督教问题分成新旧两派,一派主张革新,一派主张坚持旧有传统。
两派都有支持的势力,然而都为教士,所以都是以理论进行论战。
有神学院讲授神学的教士伊拉莫斯,就提出了信仰外表行动不足以弥补自身罪过,而更多应该讲究善行的主张。
伊拉莫斯虽然倡导和平改革宗教,然而其终身没有看到实现之日,因为他终身都认为只要人人都开智了,然后就可以实现改革的目的。
宗教改革的基础是日耳曼部落受到罗马教会的盘剥最狠,路德出生前三百年已经有人讽刺罗马教会教主愚弄愚钝的日耳曼部落之人。
“所有若辈之财产,均为吾所有,若辈之银源源流入吾之柜中;若辈之牧师食鸡而饮酒,而愚钝之俗人则任其斋戒。”
日耳曼诗人同样发出这样的讽刺。
日耳曼部落大主教,例如美因茨、特里维斯、科隆、萨尔斯堡等地大主教,凡是被选为大主教,均需缴纳一万金币给罗马教会教主;
且这些大主教接受领带的时候,也需要缴纳巨款。
罗马教会教主有任命教士的权力,而多派意大利半岛地区的人出任大主教。
这些被任命的大主教,仅仅是享受搜刮的钱财,并没有履行职务的意思。
更为甚者,有的大主教一人可以兼任教会中数职。
例如,十六世纪初年,美因茨大主教同时兼任马格德堡大主教及哈尔的斯塔德大主教;有时一位大主教可以兼职二十多处之多。
所以日耳曼部落内,酋长之类的所谓贵族是眼红,这些教士太有钱了;而底层奴隶是期待改变,不能够盘剥的太狠。
当日对于教士阶层不满者,已经充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对于教士阶层中的另一个系统类似于佛教的托钵僧,例如芳济派、多明我派及奥古斯丁派,也被各阶层所蔑视。
盖因为托钵僧虽然没有教士阶层富有,但是其行乞如盗贼,频繁可恶。
日后宗教改革的领袖,即出自奥古斯丁派的托钵僧。
宗教改革有伊拉莫斯之主张,也有胡登之批评,批评皆以教会宣传与教会腐化为对比,使日耳曼部落各阶层看到这种不公的严重性。
后马丁·路德犹如一颗火星点燃了熊熊大火,呈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