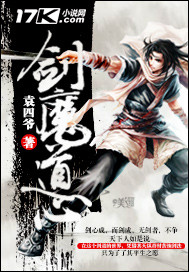千寻淡淡一笑:“不多不少,就一件。”说得异常肯定,不免叫李公公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本宫这会儿还没想好,等想好了再告诉你。”千寻补充道。
李公公刚刚得到松缓的神经立刻重新绷成了一条直线,额间已不知不觉渗出一层薄汗。都说被人吊着的滋味儿可不好受,万一哪天这要办的是件掉脑袋的差事,可如何是好?
千寻看出了他的疑虑,不紧不慢得说:“放心,要你办的,肯定是在你能力范围内的,不会害你赔上小命儿的。”
李公公受宠若惊,连连谢道:“王后菩萨心肠,奴才先在这儿谢过您了。”
话说到这儿,千寻心中一阵窃喜。这李公公好歹也算的上是后宫奴才里的一把手,万一哪天有个用得着的时候,指不定还能派上大用场呢!
千寻在御书房呆了近两个时辰,才从里面走出来。没有人知道,这两个时辰里他们究竟在谈些什么。只因在千寻刚踏进御书房的那一刻,南宫奕便摒退了御书房内所有人。只是在她走后不久,黎王却又下了一道圣旨:王后言行有失,罚禁足十日,以示惩戒。
千寻走后,南宫奕默然无语得坐在御书房内,昏暗的光线将他的面容映得一片暗沉。他本是希望她远离这场纷争的,可是不知为何,听到从她口中说要离开,心里终是不舍。素来行事决绝的他,此刻竟然显得如此优柔寡断,也许,他真的并不适合这个位置。
南宫奕心中低声叹道:“三哥,四弟终于知道你为何死也不愿再回来了。”
十日后,禁足之令已解,整个昭庆宫却依旧显得冷冷清清。千寻凭着模糊的记忆,来到整个王宫最西面的一处宫苑门前。与想象中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因为主人的离开而就此荒废。依然整洁干净,一如从前那样。
千寻站在紧闭的宫门前呆呆地望了许久,正要离开之际,忽见一抹明黄色的身影正朝这边走来。心里蓦然一愣,他来这里做什么。此刻,真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略一寻思,干脆隐在了一棵粗壯的榕树后面,就在南宫奕将要踏入宫门之际,一只乌鸦扑腾着双翅从榕树上飞了下来。千寻吓得身子一缩,却被眼尖的李公公瞧个正着,只听他厉声道:“是谁鬼鬼祟祟地躲在那儿,还不出来?”
千寻心中一紧,缓缓从榕树后面走了出来,却对上南宫奕一双清冷的眸子。
“不在昭和宫好好待着,来这里做什么?”南宫奕眼神锐利地盯着她道。
“我,我迷路了。”千寻埋头看着地面,信口胡诌道。
“来人,送王后回昭和宫。”他的声音依旧如此冷淡,听不出是喜是悲,只是凝视她目光里,却有着难言的伤感。
入夜,千寻辗转反侧,却不能寐。她总觉得南宫奕仿佛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就连白天见到她时,说话的语气也是怪怪的。还有那座宫殿本是南宫晨还是太子时的寝宫,他去那里做什么呢?
“彩雀,陪本宫出去走走吧。”千寻披了件单薄的外衣,朝外走去。
不知不觉,她与彩雀信步走到了御书房门外。只见里面灯火明亮,似有人影正在里面来回踱着步。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敲门时,“吱”得一声,大门从里面缓缓拉开了。千寻未做好进去的准备,赶紧拉着彩雀闪到了一旁的柱子后面。借着月光,她看清了那人的模样,风华一现,足已令万物失色。只见他的眉宇微蹙,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从她眼前走过。
回去的路上,彩雀自顾言道:“欧阳大人相貌堂堂,真是可惜了。”
千寻心中好奇,转过头问:“此话从何说起?”
彩雀自觉失言,看向千寻时已噤若寒蝉。谁知千寻却死缠着她问关于欧阳曜的事情,彩雀拗不过她,于是缓缓道: “娘娘可听过一句话,英雄难过美人关。”
千寻虽急于想要知道些关于他的事情,却依然颇有耐心道:“这与他又有何干?”
彩雀细声细语道:“娘娘当真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欧阳大人和您可是自小订过亲的。”
千寻眼中迷茫,宛若孩童般不解道:“那你可知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吗?”
彩雀低眉顺目得看着她,口中支支吾吾道:“奴婢听人说,是因为,因为……”
千寻终于按耐不住,心下焦急道:“你倒是说下去呀!”
彩雀这才小心翼翼得回道:“奴婢听人说,是娘娘在大婚前与人私奔,所以丞相府才决定上门退亲的”
没想到她以前的人生,居然如此富有戏剧性,千寻故作好奇道:“那后来呢?”
只见彩雀叹息着道:“再后来,欧阳大人便从此一蹶不振了,至今仍是孑然一身。”
千寻听完只觉心里酸酸的,特别不是滋味。到底是什么样的男子,能做到如此长情呢?目光无意间飘向远处的林子,成百上千株梅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却又亮丽的风景。不知为何,看在她的眼里,却是一片黯然失色。
一座高墙深院的大宅内,灯火通明,恍如白昼。
欧阳文若抿了口香茶,若有所思地看向坐在身旁的欧阳曜道:“兵部慕容大人即将告老还乡,王上也正为该派谁接任而烦忧。兵部责任重大,若非亲信之人,定不敢冒然委以重任,为父想推荐你继任兵部一职,不知你意下如何?”
“恐怕要让父亲大人失望了,这份差事,您还是另选贤能之人吧!”欧阳曜淡淡回道,他深知为官者最忌讳的便是独揽大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欧阳家如今的势力虽大不如前,但依然可说是遍布朝野。妹妹虽已是前朝废后,但父亲却依然是威震朝堂的一国之相,自己当初一心要将瀛洲军的军权交了出去,就是不想落人口实,如今又怎可再揽下这兵部大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