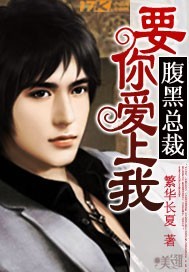“边上有一个家长过来说:‘希希妈妈,你不要再生气了,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正常的’,她又对我说:‘向往妈妈,你跟希希妈妈道个歉吧,道了歉就没事了。’我问我为什么事道歉,那家长说向往把希希咬伤了,希希妈妈生着气呢。向往咬那个叫希希的孩子的事我知道,是希希先动的手,她用玩具敲向往的头,向往头上鼓了一个鸡蛋大的包,那天我一回家她就告诉我了,我心疼的用热毛巾敷了好久,向往说她让希希住手的,但希希不肯,这才去咬的,我还夸向往了,我说向往你做得对,别人打你了,你就要还手。”
“我问希希妈妈,不是应该你先道歉吗,是你家孩子先动的手。”
“希希妈妈就开始骂,骂我们家向往,有爹生没爹养,是个野种,骂我们的家庭畸形,还说要发动家长让向往调班,不能让一粒老鼠屎糟蹋了一锅粥。我可以忍受别人来骂我,戳着我脊梁骨骂都没事,但她不能说我的孩子,她不能来伤害我的孩子,我受不了了,跟她打了起来。”
“打架,丢人吗?”
“要不是警察来了,我能把她骨头咬碎了。做了母亲经常会不知道如何是好,向往咬了人,我似乎领着她跟希希道歉,会显得我们很大度,很有礼貌,但是一个母亲的心不允许去做这样的行为,如果向往被欺压着一再忍让,她长大了会不会跟我一样懦弱,你知道的,在这个社会里,不是你能忍受,坏人就会收手的。况且相比跟一个男人上床,打架算什么呀,那个男人睡了我,嫌我技术不好,跟向往说你妈是个贱货。我居然一点都不难受,向往有学上了,我高兴,我不难受,我不丢人,现在的世道,谁有资格嘲笑谁啊。”
足足五分钟的缓冲时间,王照才被迫从她自己的回忆中挣脱出来。
继父住到她家的第一夜,早上出了房间的齐慧娴容光焕发。
王照在心里骂了一千遍贱货。
“别人不能伤害你的孩子,你自己就能打吗?”
“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打孩子,我是就事论事的。每次我打她都是有原因的,向往不听话,三天两头闯祸,不肯好好上学,背地里偷家里的生活费请同学大吃大喝。”
“你跟路向往沟通过吗?你听过孩子的解释吗?任何事不能心平气和的说吗?”
“我愿意跟向往沟通,可向往不是每次都能听进去的,有时我花很长的时间跟她讲一个道理,讲上十几遍,几十遍,以为她听懂了,她也告诉我她懂了,但转脸她就趴在商场的地上哭闹,要我给我买玩具。小孩子眼里的道理跟大人讲的道理是不同的,她会在我生病的时候为我倒水拿药,但她也会囔囔着要去外面的饭店吃饭,她知道妈妈辛苦,可别的小朋友有的她也想要,反复无常,时而懂事,时而不懂事。”
“既然你能感觉到她的懂事,一个知道克制的母亲就不能包容一个不会克制的孩子?”
“我试过,我试图去包容她,我试图做一个情绪温和的母亲,但当你筋疲力尽的下了班,迎接你的只有一个杂乱无章,等待你去收拾的家,还有一个正在搞破坏的孩子,你不让她看电视,她哭,喊她睡觉,她也哭,吃饭哭,洗澡哭,永远在哭,玩具扔的到处都是,你跟在她后面也来不及收拾,除了弄孩子,还要加班弄工作,我温和不了,做不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王照打断她的话:“那你就打她?”
“在家里吃苦,总比到外面吃苦好。”
王照的火腾地升了上来,谬论,她的谬论真多。
“伊程方,还记得你说过的疤和糖吗,路向往的不好对你来说是一个疤,始终烙在你心里,而你的好是路向往吃过最甜的糖,她想到你,就会想到那块糖,在你眼中如此不堪的孩子,在一个如此冷漠的家里,却学会了爱和感激。”
伊程方睁大眼睛:“冷漠,你说我对向往冷漠!为了她,我拼了命在做一个好母亲,我都是为了她好,要不是为了她,我早就不想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请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你要是真为向往着想,就不要再说什么为了她好!够了!够了,伊程方!”
“那我请问你律师,你一直在谴责我,难道我一个离异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五年,就没有一点值得你肯定的地方吗,所有人都在否定我,那谁来替我想一想呢!谁考虑过我!我知道,我知道我打了孩子,你们都在骂我,你们看不起我,但这么多年,五年,一千八百多天,一个女人的青春有多少个五年,我像囚笼里的鸟,不知疲倦的打转,无论刮风下雨,不能停,一刻也不能停,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哪怕说一句:伊程方,你辛苦了。”
“律师,我是为了谁呢?为了我自己吗?”
王照一言不发,闭上眼,大喘了几口气,失魂落魄地出了看守所。
恶人借口多,跟后妈似的把孩子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从整个人生来说比芝麻粒还小的破事,成了她们口诛笔伐亲生孩子的利剑和赤裸裸的情感勒索,喜欢让人背负着情感枷锁前行, 跟齐慧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她以为她值得被报答吗。
她根本不知道被她勒索的那个人有多痛。
跟今天一样冷的天,齐慧娴腌酸菜,洗菜时发现盆坏了,质问王照。王照说学校大扫除,要求每个人带件工具,她被安排擦玻璃,带了盆,窗户上的插销坏了,掉到盆里,盆裂了。
齐慧娴二话不说,操起擀面杖打,不挑地方打,擀面杖落到哪是哪,骂王照败家子,不学好,家里有旧盆不带,拿刚买的盆,也不跟她商量下。
她每打一下骂一句,骂一句,带一句她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