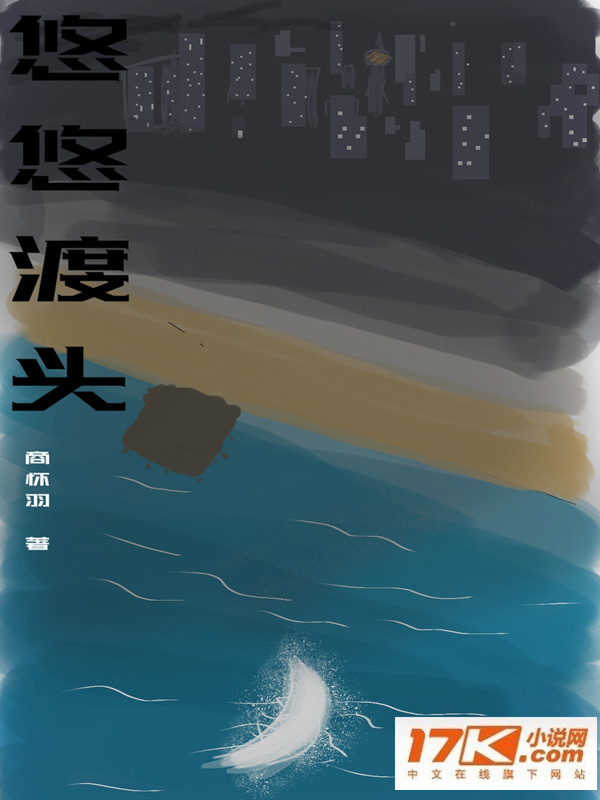帝王身穿宽大的道袍,枯草一般的头发散乱下来,披在肩头,脸上纵横着沟壑一般深深浅浅交叠的纹理。
他的儿子则身着玄袍,金冠玉带加身,周身气势凛冽,仿若芝兰玉树。
帝王用字来称呼自己的儿子,话语里却没有什么亲近的意味。
更多的是一种责怪,讽刺。
也的确讽刺。
给太子取字的,是从小教导他长大的老师,这位老师不仅教给太子做君王的本领,也教给他做人的道理。
可就在两年前,太子亲自处死了待他如至亲的老师,此后朝野上下,无人再敢唤他的字。
顾明华唤他慎己,意在提醒他是一个多么荒唐、胡闹的人。
毕竟,能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执剑斩杀自己的老师,一国重臣,悉数大邺开朝至今,可能也就只有顾远洲一人了。
顾远洲垂首静立,脸上神情淡漠,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拱手道:“儿臣知错。”
却也没有什么认错的态度,反而更多的是一种漫不经心,从他骨子里,眉眼间透露出来。他用这样沉默的方式告诉皇帝,他并不觉得自己错了,但如果硬要说他有错,那他便错了吧。
顾明华定定看着他,忽然抬手端起桌边的茶盏,直直朝他脸上摔过去。
顾远洲不躲不避,温热的鲜血从他额角缓缓流下来。
他嗤笑一声,抹了把脸上的血,笑着抬眼问榻上的顾明华:“您满意了吗?”
顾明华怔忪,还没来得及说话,顾远洲便已经昂首阔步,离开了大殿。
他按着腰间的剑,从马厩里牵了匹马,扬鞭策马,风驰电掣一般驰出皇城。
已经是宵禁时间,清平街陷入一片昏暗的阴影里,守城的侍卫跌坐在城门口,昏昏欲睡。
他渐渐地慢了下来,信马由缰地在清平街上逛着,腰间的剑沉寂在剑鞘中,发出阵阵铮鸣。
不知道走到哪里,他翻身下马,将马系在垂杨下,转身几个纵跃,掠进了姜府东南角的小院里。
姜蘅还没有睡着,听见窗下传来响声,她忍不住起身,提着灯走出去,却见着跌坐在梅花树下的顾远洲。
不甚明亮的灯光映照出男人脸上的血渍,姜蘅本应该转身就走。
她是不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就算有人死在她面前,她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可是看着顾远洲这样,她却忽然觉得他很可怜,朦胧的念头从脑海里闪过,她来不及思考地将顾远洲从地上拉起来。
将他带进了自己的屋子里,又从梳妆台下的抽屉里找出来伤药,给他处理伤口。
她做这些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垂着眉眼,仔细看着顾远洲额头上的伤。
顾远洲也不说话,静默地望着姜蘅的侧脸。
大邺储君有御前佩剑,纵马禁宫的特权,而方今天下,能朝顾远洲动手的人也唯独那一位。
不用多想也看得出来,他这是刚从宫里出来。只是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竟然让皇帝这般大动肝火,一点脸面不给自己儿子留。
“半夜三更,大小姐便这般不设防将男人拉到你房里?”顾远洲沙哑的声音在姜蘅耳畔响起。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芳汀苑,也没想到姜蘅会把他带进屋里给他上药。怔愣许久,他忽然话里带刺地问道。
姜蘅早已经习惯了,白他一眼,将纱布收起来:“好了,殿下请回吧。”
她没想那么多,甚至没有想起来刷好感度这回事,仅仅只是因为觉得顾远洲可怜,所以她愿意施舍她的怜悯。
她很少会觉得别人可怜。毕竟世道如此,人命比草都轻贱。
可是顾远洲不同,他是天之骄子,生来就应该高高在上,睥睨天下。可是他跌坐在梅花树下时,叫姜蘅瞧着,哪里有一点高高在上,不染淤泥的皎洁与无瑕?
顾远洲笑了笑,抬头看着姜蘅,唇边逸出漫不经心的笑意,有些懒倦的意味,他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姜蘅,你明不明白?”
与此同时,一抹寒光闪过,烛火忽地灭了下去,而姜蘅,脖颈上多了一丝凉意。
她气急败坏地盯着顾远洲,咬唇道:“第四次了!”
这是他第四次想杀她了。
顾远洲也明白她的意思,轻嗤一声,收回了剑,失望道:“是啊,第四次了。”
他还以为姜蘅有多经得起逗,没想到这才第四次,她就已经不耐烦了。
他低着头,将剑插入剑鞘,道:“姜小姐是聪明人,想必今天的事,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姜蘅抱臂而立,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看心情吧。”
见顾远洲的动作顿住,眼眸微眯地看向她,她鼓了鼓腮帮子,怒瞪回去。
怎么就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杀她,却不准她利用秘密要挟他?
欺负人也不是这么欺负吧。
顾远洲见威胁没用,也确实拿她没办法,满不在乎道:“随你。”
倒和姜蘅想的不一样,她还以为他又要抽剑架在她脖子上呢。
她翻了个白眼,转头回了床上,背对着顾远洲道:“我要睡了,殿下想待多久便待多久吧,只是等你离去时,记得要锁门。早晨雾气湿重,风也轻寒,我会受凉。”
顾远洲舌尖顶了顶牙齿,被姜蘅这么理所应当的态度惊住,错愕半晌,终究说不出什么话来,只得无言。
当然也不是没有什么想问的,只是他对姜蘅也算有所了解,已经预见有些话说出口就等于自取其辱的结局,实在没必要多说。
至于姜蘅,大半夜与顾远洲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她实在安心得很。
很显然顾远洲不可能对她有什么兴趣,毕竟是储君殿下,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她对顾远洲而言,想来和茅坑里的石头无异,又臭又硬,激不起他半分怜爱之心。
今夜注定是个不眠夜。
她这么想着,却沉沉闭上了眼,折腾一晚上,总算能入睡了。
顾远洲等了一会儿,听见她绵长的呼吸声,走上前去,发现她果然毫不担心地睡着了,一时也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