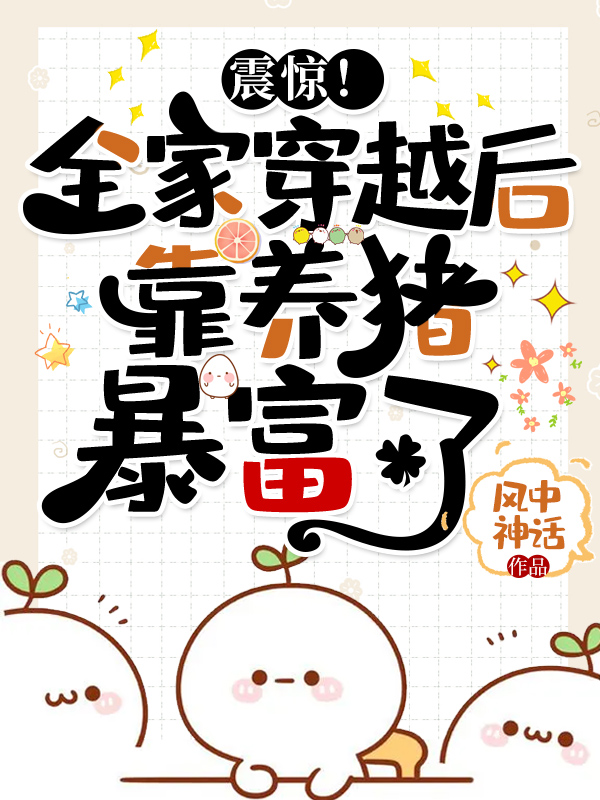贾氏坠崖的事,第二天便传到了姜府。
姜蓉自从宜霜居被姜蘅的人一通打砸之后,便一直闭门不出,如今听闻母亲坠崖,生死不明,顿时气急攻心,直直晕死过去。
待她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抓着身边丫鬟的手问姜蘅何在。
“一定是姜蘅做的,除了她……”她捂着胸口,又急又气,“去将她找过来!”
姜蓉面色潮红,声音里充斥着毫不遮掩的恨意。
她一直知道姜蘅狠辣,却没想到她居然真的对身边人也能下得去手,回想起两年前她险些就能令姜蘅沉尸江底,可惜棋差一着,教她活着回了玉京,这叫她如何能不狠?
冬青为难地看着自家小姐:“那位一早便出去了,听门房说,来接她的好像是太子殿下身边的侍卫大人,不过……没亲眼见着,奴婢也不知真假。”
她话一说完,姜蓉便狠狠抓住了她的手,尖锐的指甲在冬青手背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她扭过头,厉声问道:“门房真是这样说?”
冬青怯怯点头,不敢出声。
姜蓉急促地喘了口气,慢慢平躺下去,仰首望着帐顶:“我知道了,你先下去,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冬青担忧地看了她一眼,却也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只能转身出去,随即将门关上。
已经是五月的天,院子里的石榴花来得红艳胜火,浓荫下清幽的池塘里锦鲤游曳,繁茂的枝叶间蝉鸣声渐起,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
但是姜蓉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冷过,冷得好像她一颗心如坠冰窟,浑身血液都凝滞住。她缓缓裹紧了锦被,终于闭上眼睛,长长地呜咽了一声。
犹如困兽低泣。
……
禧华宫里,姜蘅已经给容嫔和七皇子诊完脉,她收起医箱:“娘娘与七皇子体内的余毒已经清理了快一半了,待余毒清除完毕,臣女会再为两位开张调理身子的药方,假以时日,两位便能与常人无异了。只是接下来,恐怕臣女不便出府,有些事情,少不得要太子殿下代劳。”
接收到她的目光,顾远洲点了点头:“这是自然。有什么事姜小姐尽管吩咐便是。”
姜蘅淡淡点了点头,与容嫔辞行。
容嫔抿了口茶,目送她出了正殿,又看了眼心神恍惚的储君殿下,笑着道:“臣妾看殿下是坐不住了,不如殿下送送姜小姐?”
顾远洲愣了愣,下意识看向姜蘅袅娜离去的背影,容嫔的话就在耳旁,他却又踌躇起来——他不确定姜蘅会不会愿意让他跟在身边,万一姜蘅给他甩冷脸……
“殿下还愣着做什么?您再等,小心姜小姐就走远了。”容嫔催促道。
顾远洲不再迟疑,起身离开了禧华宫,阔步追赶上姜蘅的脚步。
“殿下也要出宫?”姜蘅停下来,转过头看他。
顾远洲走在她身边,目视前方,声音中却夹杂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我送送你。”
“这条路,殿下已经送我走过好几次了,殿下实在没必要多此一举。毕竟有的路你能送,有的路,你送不了。”姜蘅口吻平淡,就像是在和相熟的人谈论今天的天气或者饭菜,而不是在拒绝如今大邺位高权重的储君殿下。
“我竟不知,这玉京城里,有什么路我走不得,有什么人我送不了?”顾远洲偏过头看她,“且不说别的,为美人效劳,我心甘情愿,怎么就叫多此一举了?”
姜蘅再度停下来,拦在他面前:“这么说来,殿下很乐意为我效劳?”
“当然。”顾远洲低头,看见她去蝶翼扑闪的长睫,与长睫下水光潋滟的一双眼,忽然往后退了半步,拉开两人的距离之后,他才清了清嗓子:“此前的事就让它翻篇如何?反正,姜小姐不也没什么损失,往后还是那句话,你姜蘅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好么?”
似乎是鬼使神差般,他如此说道。
但是等话音落下,他才恍如梦醒一般明白过来,这哪里是鬼使神差,就是他心中所想。
不然,为什么说出这些话后,他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姜蘅点头:“好啊。难得殿下亲自开口,我就却之不恭了。我希望殿下帮我办一件事,试探也好威逼也好,质问也罢利诱也罢,您找人帮我问一问我那位二叔,九月十八那天的事,他知道多少?”
她说完,转过身继续缓步走着,明媚的阳光从枝叶的间隙里洒落下来,落到她发间,肩颈,背上,轻灵而绚烂。
顾远洲看得失神,但很快他便收回心神,跟了上去,追问道:“九月十八?这个日子,有什么说法不成?”
姜蘅面上收了笑意:“这您就不必知道了。还有一件事,大多数事情,在我心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所以很显然,真正放不下的那个人是您。如果真的想让它翻篇,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再提,殿下明白了么?”
她顿了顿,看向眼前守卫森严的宫门:“我到了,殿下留步。”
顾远洲脚步顿住,没等姜蘅出宫登上马车,便像被戳中心事一般,转身往回走。
衡暝从禧华宫出来寻他,恰见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这多稀奇啊!
衡暝回想了一下,就连当初皇后薨逝的时候,自家殿下可都是冷着一张脸呢!难不成是天要塌下来了?不然他家殿下何至于此?
“您……您怎么了?”衡暝跟在他身边走着,小心翼翼地问道。
顾远洲没有理会他。
直到回了太子府,他也没有理会任何人。
待蝉鸣声渐渐歇下去,熔金的夕阳消失在水面上,雾蓝的夜色笼罩整座玉京城,枯坐窗前半日的顾远洲才终于抬头,怅然望向天边孤悬的明月。
“衡暝。”
衡暝正抱着剑打瞌睡,闻言一惊,险些怀里的剑都掉下去,他迷茫地“啊”了一声,“殿下,怎么了?”
顾远洲叹道:“你说,徒手摘月,是不是天方夜谭。”
不等衡暝回答,顾远洲已经知道了答案。
摘月已经是天方夜谭,试图让月亮坠落,更是异想天开。
他不想再做说梦的痴人,更不愿再自欺欺人。
“您说什么?”衡暝抹了把嘴,他正在半梦半醒间,有些没听清他家殿下的话。
顾远洲摇了摇头,向来冷冽的眉眼显现出几分温柔意味,他兀自笑道:“我说,明月照玉山,皎皎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