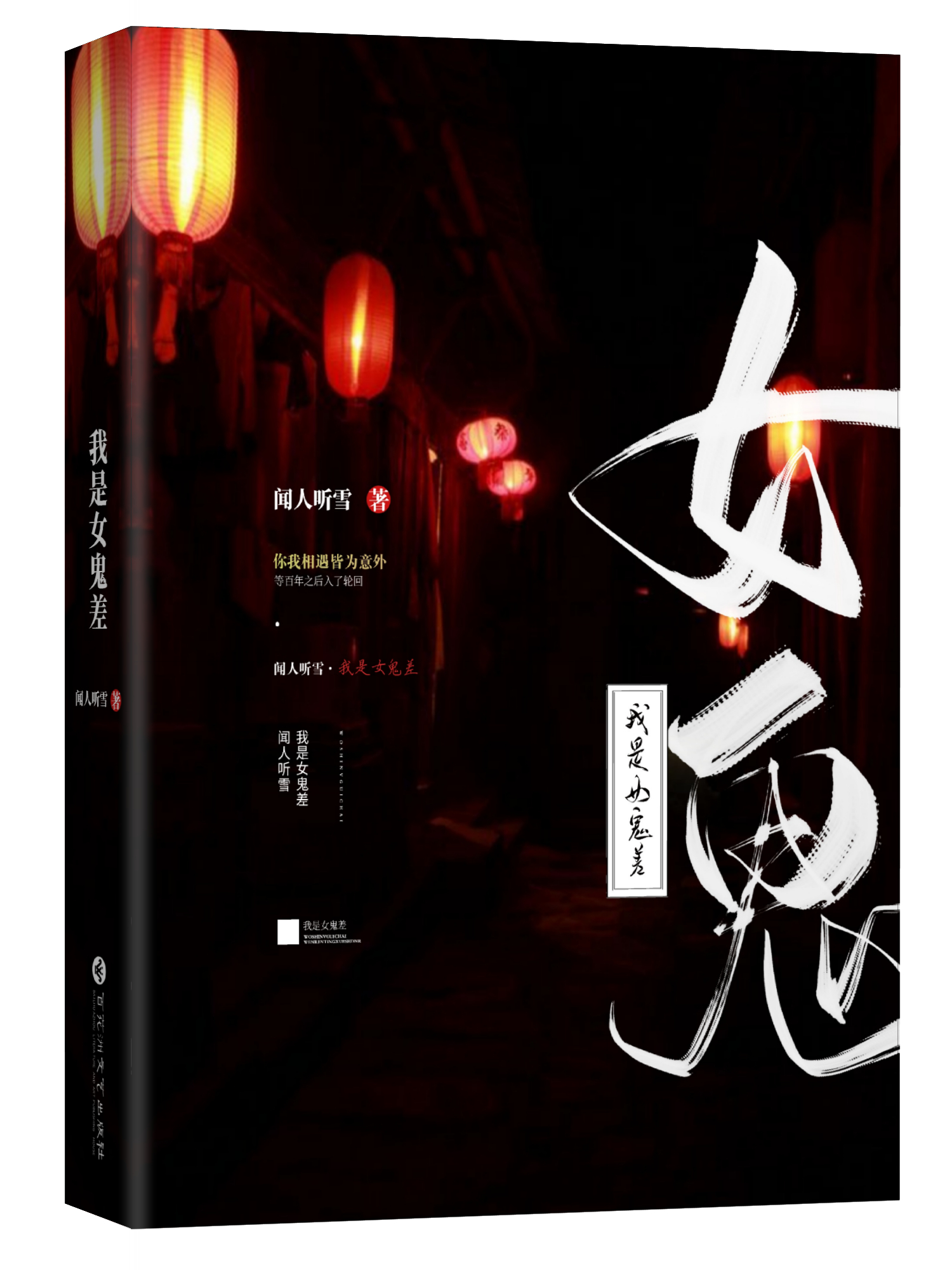摩托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路爬行。白泽把车停在山腰步行上山。
夜晚的星空,山顶别墅灯火阑珊,充斥着热闹的烟火气息,与一日前的空城霄壤之别。前院是乳白小洋楼,后院为简约中式小庭院,中间是片大花园,完美地由西式过渡到中式。
别墅正门大量士兵把守,戒备森严,后院却无人看守,他从后院翻墙溜进别墅,发现另一片奇怪的小花园。小花园土壤呈黑色,园中没有半根杂草;有规模地绽放琳琅满目的花。明明是夜里,这些花的姿态却异常绚烂,清楚。有的花呈喇叭形状自然垂下白的,紫的,红的,蓝的,其中白色最多;有的花姿异常挺拔,颜色绚烂夺目,外观似毛绒球,紧密地排列;还有的花呈妖娆的淡紫色,像千鸟在飞翔,花样繁多,实在令人应接不暇。
白泽靠近这群植株,一赏它醉人的芬芳。这片芬芳比酒还要浓烈,闻上两口,飘飘欲仙,使他彻底忘却手臂上的枪伤。
待会儿,若见到莫月,总不能空手。他信手拈来开得最艳丽的几支,拿着花往前院方向走去。他一路排查,搜寻莫月的房间。
前院一处小洋楼,整个二楼全灭着灯,底楼却灯火通明,有好几排士兵盯梢。要么二楼有重要的人,要么有重要东西。他把花揣在胸口,沿着窗户爬上二楼。
屋内很黑,伸手不见五指。
“白泽。”
寂静的房间里骤然响起他的名字,晶莹的冷汗挂在额间。
白泽硬着头皮摸黑开了台灯,莫月正躺在床上酣睡,她翻了个身,时间仿佛变慢了,莫月的动作开始拖长。
他把花放在床头柜上,摇醒她。
“阿月,阿月。”
莫月迷懵地张开一点点眼缝,看见白泽,惊地一下坐了起来。
他先亲了她的脸颊,替她理好鞋子。
“来把鞋穿上我带你走。”
“我不走,我要和阿岳一起住。”
“不准!你必须跟我在一起,陪在我的身边,跟我走。”白泽拉起莫月的手,要带她离开。
莫月赖在床上,不肯下来。
“我不走,你走吧,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白泽暴跳如雷抓着她的手腕质问道:“为什么不跟我走?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为什么刚刚扔下我跟他跑了?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你说!你说啊!”
莫月赶紧捂住他的嘴:“你小声点,大家都在休息。”
白泽推开她的手,闷闷不乐地把脸别在一边。
莫月尝试偷偷挣脱白泽握住的手腕。
白泽突然凶巴巴地瞪着她:“你变心变的好快。”
莫月黑着面雄辩道:“不是我变了,是你变了。”
白泽全身每一颗细胞开始沸腾,精神亢/奋,激昂,他的理智逐渐被滚烫的身体蒸发殆尽。他把莫月按在床上,豺狼一样疯狂啃食她的唇。
莫月竭力挣脱他,可是他倆实力悬殊,她被轻易地压在床上。慌乱中,她碰掉床头柜上的台灯。
屋内又是一片漆黑。
白泽把她压在身下,如破竹之势~~~~~。
莫月狠狠地给了白泽一巴掌,白泽怔了怔,盯着她一动不动。
张莲生闻声赶过来敲门:“阿月,心情不好别憋着,要不出来吃点水果。晓容很担心你。”
如此尴尬的境遇,莫月只想快点撵走张莲生:“不吃了,我很累,想休息。”
“这是你说的。待会儿,不准把我的房子拆了。”
幽暗中,莫月的眸子还是那样美,好像是有人把星星捏碎了,塞进她的眼睛。
她也看着他,两副曲/体/紧贴在一起,彼此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心跳。
他欲缩回身子,正在这时莫月纤细的手指无意间触到他脖子上的伤疤,以前的种种历历在目。她突然揽住他的脖子,往伤疤上亲了一口。
白泽盯着她盈盈的目光,邪魅一笑,继而放心大胆地攻城掠地。
阳光洒进房里,照耀在白泽的脸上。他睁开眼睛,盯着熟睡的莫月傻笑。他在她额间亲了一口,替她盖好被子,起床。
“都日上三竿了,还不起来晨练?”
张莲生拿着铜锣叫嚣,推开房门,撞见白泽正在扣扣子。张莲生愣在原地,看了眼白泽,看了眼床上熟睡的莫月,又看了眼遍地狼藉的衣服,一缕无名青烟自头顶升起。
白泽趾高气昂地瞥了他一眼,扔下一句话:“明天,我再来。”然后,名正言顺地从大门离开。
张莲生后知后觉才想明白,那股青烟的来历。莫月是以情人的身份住在别墅,现在白泽把她睡了,明摆着给他戴绿帽子,竟然还放言明天再来,太狂妄,太目中无人。
大清早,茶楼很清静。
白泽五折中枪的手臂出现在门口,小厮一见他便叫来了白先生。
李惜朝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消失的一晚做了什么。
“冲动了,惜朝,我昨晚好像冲动了。”
李惜朝更加好奇:“什么冲动了?你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话快到口中,白泽又难以启齿,他无力地瘫在藤椅上,望着房梁。
白映秋端来一个托盘,托盘里用酒精泡着手术器械。
白先生剪开染红的袖子,给白泽打了麻药,谨慎地取出子弹,老生常谈道:“有什么要紧事,不能先取了子弹再去。”
李惜朝挖苦道:“他害怕取了子弹,黄花菜就凉啰。”
李惜朝正色起来:“昨晚,警局来了消息。四名疑似杀害阿雨的凶手,被五花大绑吊在警局大门口。重点是这四个人的身份,他们都是孙天起的手下,就算是张莲生把薄山占了,都不敢对孙天起怎么样。你说是谁,敢动他的人?当铺老板的死和他也有关吗?还有,玉璜,矿洞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其丧命?”
折腾了三天两夜,白泽面无人色,眼眶深陷,周身写满倦意。他在茶楼稍作休息,又赶去警局上班处理阿雨的案子。
山顶别墅,已经晌午,莫月才醒。
她精心整理床头柜上的花。杨晓蓉一下跳进来,手里拿了两个大包子。
“小懒猪,饿了吧?中午饭都没吃呢。”
床上乱糟糟的,地上还有一些花的残枝。杨晓蓉把包子塞进莫月的嘴里,“你先吃东西,我帮你收拾。”
床单刚一拉开,被褥上全是血。
杨晓蓉以为是莫月的血,吓坏了,硬是推她去看唐廷枢。
“我忘了,他的枪伤。”
张莲生上来叫莫月吃饭,听到她娇滴滴的声音,气急败坏得不行。
“他好的很!今天走的时候活蹦乱跳的。还说,明天再来!”
莫月的嘴角甜滋滋地扬起。
张莲生指着她的鼻子,恨铁不成钢得骂道:“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一说到他,就这种表情。哎呀!女大不中留,女大不中留啊!”
张莲生非常讨厌白泽,讨厌他俊朗的相貌,讨厌他高傲的口气,讨厌他睥睨的眼神。同时,张莲生又很矛盾,莫月那么喜欢,元容也同意了,生米被煮成烂粥,由不得他接不接受。
张莲生破天荒主动提醒莫月洗了手,再吃饭。
莫月一上桌就埋头吃饭,一言不发。
“你怎么想的?”张莲生问。
莫月浅浅地回答道:“没有怎么想。”
“什么叫没有怎么想,你不是说他有爱人吗?可是他昨天晚上又来把你,哎呀!”张莲生羞红了脸,捶胸顿足了半天,“你说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昨天晚上我自愿的。”
张莲生坐不住了,站起来指着莫月,羞愧道:“女孩子家家,说这种话也不脸红。”
莫月很认真地看着张莲生。
“真的是我自愿的,不关他的事。睡火莲花期一到,我们就回迟木岛。”
“不行!碰了我的人就想跑,门儿都没有。”
“人家有主的,我承认我真的不想放手。我也想去争个头破血流,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是那样的人。应该说,是我自己懦弱,我没有勇气成为那样的人。都说,真正的情爱会让懦弱变得神勇,平庸变得出众,可能我和他根本就不是爱情吧。”
张莲生谈吐越发激动:“有老婆还来碰你!他可恶啊他!”
莫月加重语气强调:“我自己无能,不关别人的事。”
对话逐渐攀升,气氛白炽化。
“我不管!他必须娶你!要是在花期之前他没有八抬大轿来娶你过门,我要他全家陪葬!”
“你这是在给我压力!”
“我是为你好!”
“我不想逼他!我也不喜欢被人逼!”
张莲生一掌拍在桌上:“不行!我不管!我绝对不吃这个哑巴亏!”
“那如果我告诉你,雨夜那一枪是他开的,你还会这么撮合我跟他吗!”
张莲生狂躁地叫嚣道:“那他就该死!”,两个人的话音几乎同时落下。
莫月说岔了气,一直咳嗽。杨晓蓉赶紧为她倒了杯水,张莲生端起来一饮而尽,灭掉心头的熊熊烈火,酒杯往地上猛得一摔,离席去找唐廷枢抱怨。
午后,张莲生偷偷扔掉白泽送的花,又引发一场口角,两个人现在势如水火。张莲生命人在房间准备好一把步枪,守株待兔为的就是对付白泽的明日之约。
等不到第二天,一下班,白泽去市场买了一大束花,抱着走上盘山公路。上午才从别墅中光明正大地走出来,士兵以为有客到访,也没拦着。他抱着花,径直去了莫月住的那栋洋楼,在楼下一直叫喊:“阿月,阿月。”没有回应,就进了房间。
书桌正对着窗户,左边放着三针小闹钟,正中间简易的书架夹得满当当的书。莫月手里拿着钢笔,一边看书一边认真做笔记。
白泽把花放在书桌边上,翻了翻书名《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纯粹理性的批判)。
“什么时候会的英文?我怎么不知道?”
“那是德语。”
白泽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莫月一声不响,全神贯注地看书。白泽并没有打扰她,而是拖了跟凳子坐在旁边,静静地陪她看书。闹钟响了,整整两个小时,莫月简单收拾了一下才理会白泽。
白泽想了想:“孩子,怎么没了?”
“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就没了。对不起。”莫月眼眶噙着泪,视线望向窗外。
白泽愣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紧紧抱住莫月安慰道:“没事!孩子,以后会有的。”
尽管他的神态平静,心跳却骗不了人,他的心跳,一下比一下沉重地敲击在莫月的肩上。莫月推开他,道:“没有以后了,过阵子我就回火莲村。”
“什么!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你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面对白泽的苦苦哀求,莫月没有信心态度能一直决绝下去,只想尽快打发他走。哪知白泽不依不饶,不肯离开。张莲生步枪加持,所向披靡,冲到莫月房间。
“去死吧!”
铛!张莲生一脚踹开房门。
千钧一发之际,习武之人的条件反射,抬起枪干,临门一脚。子弹打在天花板上,张莲生连人带枪从阁楼的护栏飞了出去,狠狠摔在一楼地上,昏迷不醒。
白泽深知自己武功实力,刚刚一脚,全凭直觉几乎用尽全力。他相当心虚,战战兢兢地走到楼下确认张莲生是否已经身亡。
“唐叔!救命啊!唐叔!救命!”
莫月追到楼下,摇晃张莲生身体,想叫醒他。可是,他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没有动静。
过了两分钟,张莲生终于动了,捂着胸口叫苦连天。
他竟然没事!
白泽很是惊讶,没想到张莲生功夫这般高强,竟然能挡下自己一脚。
莫月担心地不得了,张莲生干脆顺水推舟,装得非常严重的样子,睡在地上六神无主道:“阿月,我看不见了。我好像失明了。”
莫月更慌了,急的语无伦次地又哭又闹,眼泪鼻涕大把大把滴在张莲生头上。
白泽无力地解释道:“他不可能失明,顶多就是内伤。”
莫月什么也听不进去,红着眼,冷冷地说:“你滚。”
白泽憋屈极了,不管他再怎么解释,莫月也不听,只好落寞地离开。快走到正门时,唐廷枢追出来,拍了下他的肩膀道:“莫月,更喜欢昨晚的花。”接着,意义深长地微笑。
白泽摸不着头脑,他不认识唐廷枢,而且作为山顶别墅的人,他没有立场帮自己。
白泽走后很久,张莲生还躺在地上装瞎。
唐廷枢滴了滴’眼药水’到张莲生眼里,马上药到病除,辣得他又蹦又跳。他瞧了瞧莫月的眼色,
赶紧脱下衣服,亮出胸口一团乌青,以证内伤,才松了莫月眼里的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