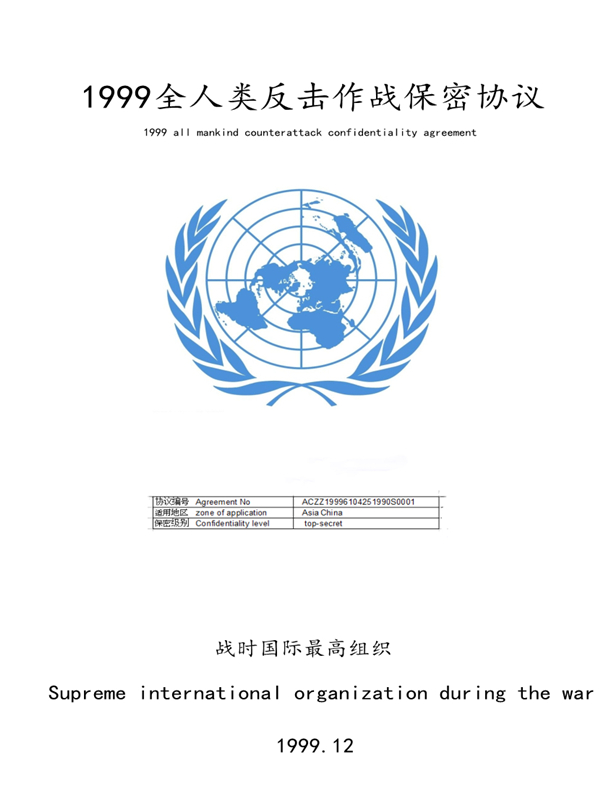众人驾车来到凤梧山脚下,行宫内的人工湖真是从山里引的活水。
下了马车,一行人顺着水源找到了湖水的源头,是一座高大十几米的瀑布,瀑布下面是一个深水潭。
邵一白让人沿途寻找,果然,在水潭附近发现了一处被踩踏过的痕迹。
水潭四周有几块巨大的石台,其中一块石台微微想潭水中央探去,石台上的青苔又踩踏的痕迹,还有一些杂乱的脚印。
“凶手应该是在此处抛尸的。”邵一白指着石台上的拖痕,“青苔被尸体拖拽之后,有一部分沾染到了刘大人的衣衫上,仵作在清理衣物的时候提取了一部分,确实与这里吻合。”
“可凶手为何要千里迢迢把刘大人弄到这里进行抛尸,而后又让它顺水冲进行宫?”程少卿晃了晃头,有些无趣地问,“这跟脱裤子放屁有什么区别?”
邵一白脸一黑,真想一脚将他踹下潭去。
不多时,撒出去的衙役们回报,林子里发现了一个木屋。
木屋不大,里间是卧房,外间摆着一张座椅,角落里摆着一只碗柜,里面还有两套餐具。
裴伷先绕过屏风看了看里间,简陋的木板床上铺着一床被子,显然是离开时并没有来得及带走。
孟鹤妘走到窗边的角柜前,打开柜子,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东西都被带走了,什么也没留……咦!”
“怎么了?”裴伷先扭头看她。
孟鹤妘从角柜的角落里找到一只干枯的野草编成的蚂蚱:“这东西可精致啊!怪好看的。”
裴伷先瞳孔微缩,抬手抢过草蚂蚱。
孟鹤妘不悦地皱眉,劈手去夺。
裴伷先连忙把蚂蚱收进袖兜:“我替你收着。”
“我没有手脚?”孟鹤妘嗤笑,整个人向前,一把扣住他的手腕,“还我。”
裴伷先拢着手不动如山,大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两个人在这儿闹着,门口传来一声轻咳,程少卿一脸暧昧地看过来,恨不能拿两个铜锣敲一敲。
“哎呀!哦,看来我进来的不是时候。”他装模作样往后退,推到门边,又探回身,“哎,裴伷先,你看出什么来了?”
裴伷先摇了摇头,孟鹤妘想说蜻蜓的事儿,被他暗暗掐了一下腰眼。
“裴伷先,你来看这个。”邵一白在外间喊,裴伷先连忙拎着孟鹤妘的领子将她拎到一边,出了里间去找邵一白。
邵一白正蹲在外间长桌下,目光沉沉地看着桌下爬来爬去的蚂蚁。
裴伷先示意程少卿把桌子搬开,便见许多蚂蚁从四周陆陆续续爬过来,然后转进颇为松软的土地里。
“是血。”
邵一白猛地抬头,狐疑地看向孟鹤妘:“你怎么知道?”
孟鹤妘双手环胸,面无表情地看着地面:“闻到的。刘伟达死了至少三天了,这么长时间了,地上还有蚂蚁聚集,说明当时他肯定留了很多血。”她一边呢喃着,一边夺过程少卿的金刀,不顾他的哇哇大叫,用力将金刀插入土中,用力向上一掘。
“噗!”的一声,地面被掘起一块,露出黄土下掩埋的黑红的泥土。
下面果真全是血。
“这里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凶手就是在这里杀的刘伟达,然后见尸体抛如不远处的深潭,之后再带着他的人头进入行宫,之后掩埋。”邵一白说完,扭头看裴伷先,“凶手应该是从出水口出入行宫的,若真如此,那嫌疑人的范围便扩大了许多。”
“也未必。”裴伷先打开角落里的碗柜,碗柜上下三层,第二层摆放了两幅碗筷。他伸手在第三层摸了摸,上面挤满了灰尘。
“行宫守备森严,外人想要进入,哪怕是从水下潜入,要想完全避开所有轮值的御林军去花园埋人头的可能都微乎及微。”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有同伙?”邵一白诧异道,“凶手的同伙在外面杀人,然后顺着湖水把尸体抛入深潭?”
裴伷先点了点头,关好角柜:“而且杀梁步仁和刘伟达的是同一人。”
“梁步仁不知病死的么?”程少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确切地说,是被人故意恐吓之后病发而亡,亦是谋杀的一种。”裴伷先淡淡地说,从木屋里出来,绕着小木屋走了两圈,然后在后面唯一的一扇窗户前停了下来。
窗户不大,窗棂从被从外面钉死,显然是凶手偶有离开时刻意钉上的。
窗棂下面是一片草地,裴伷先蹲下身子用后怕在被踩倒的草地上轻轻刮了几下,不多时,手帕上便染了许多青苔。
“凶手在杀人之前,应该先去深潭里试过多次。”裴伷先把帕子递给邵一白,“尸体能从这里顺利飘进行宫,应是经过周密计算的。”
孟鹤妘不解:“何须周密计算?直接抛尸有何不可?”
裴伷先摇了摇头:“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同,要先把尸体利用河水送到特定地点,其间不仅需要多次计算,否则很有可能在尸体没有进入行宫之前就浮出水面,半途被其他人看见,或是搁浅在某个河段。”
邵一白面无表情地收好手帕,“这也真是凶手一定要让刘伟达吞镔铁而亡的原因。”
“那何不绑石头?为何一定要逼他吞镔铁?”程少卿想了下刘伟达肚子里的那几坨镔铁,不由得一阵胃疼。
他的话瞬时引来三人鄙视的目光,好像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不知道一样。
“咳!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孟鹤妘嗤笑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搬石头那是沉河的,况且绑石头的绳子容易被谁冲开,可操作性太低,毕竟凶手是想把尸体送进行宫,以启……”她微微顿了下,扭头看裴伷先。
“如果我是邵大人,我会先勒令全城搜捕给刘伟达送信的那个孩子,不然的话,恐怕不出三日,凶手还会继续作案。”裴伷先笼着袖子,顺着来时的路下山。
邵一白面色微沉,连忙追了上去:“你是何意?”
“还记得那枚玉佩么?”裴伷先回头看他,“当初那枚玉佩便是我在益州赠与一个孩童的,此时它出现在此处,你不觉得奇怪?”
“你是说,你在益州的那个小孩就是给刘伟达送信的孩子?”邵一白皱眉。
“不止。”
裴伷先眉头微挑,突然停下步子等不远处的孟鹤妘。
邵一白看他:“你还发现了什么?”
“你可注意到刚才木屋的橱柜和椅子?”
邵一白一怔:“不过是正常的家具罢了。”
裴伷先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他:“橱柜一共三层,但碗筷都放在第二层,整个橱柜高不到三尺五寸,如果是正常身高的人,哪怕是个身高正常的女子,都会下意识把东西放在第三层,只有身高极矮的人才会把东西放在第二层,因为高度方便他取用。”
邵一白确实没想到这一方面,主要还是没想过一个孩子会是杀人凶手。
“就算如此,你为何不猜测是个个子娇小一些的女人?”邵一白犹豫道。
裴伷先拿出那只从柜子里找到的枯萎的草蚂蚱:“这是在里间衣柜里找到的,多半只有孩子喜欢这种东西。”
邵一白瞬时如同醍醐灌顶:“是我狭隘了。”
裴伷先微微敛眉,目光若有似无地看向身后不远处的孟鹤妘:“一叶障目罢了!”
邵一白抿唇不语,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便见孟鹤妘正紧紧蹙着眉头站在路边,目光戒备地看着一株垂柳。
细微的风吹动垂下的柳枝,一条碧绿的竹叶青正吐着信子与她对视。
邵一白轻笑出声:“孟姑娘似乎遇见了一点麻烦。”
裴伷先微微勾了勾唇角,姿态一下子松散下。
终于发觉到有人正在看着自己,孟鹤妘狠狠咽了口吐沫,僵硬地扭过头:“裴伷先,你过来背我。”
裴伷先微微一怔,便听一旁的程少卿发出一怔狂笑:“哈哈哈!孟鹤妘,你,哈哈哈,你竟然怕蛇,哈哈哈!”
孟鹤妘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来:“你闭嘴。”
程少卿抱着金刀好整以暇地看着她:“你来求我,我帮你把这孽畜砍成七段,你看怎么样?”
孟鹤妘隔着他看向裴伷先:“裴伷先你背我。”
“哈哈哈!孟鹤妘害不害臊?大庭观众之下让个男人背你?”程少卿一边说,一边偷偷拿眼睛看裴伷先,“喂,你不会真背她吧!这女的就是矫情,就是故意……”
“我故意怎么了?他不是我马奴么?不背我,难道背你?”孟鹤妘恶狠狠瞪他一眼,要不是她已经吓得腿软,她真想冲过去敲掉他满口牙。
程少卿脸“腾”地红了。
孟鹤妘见他脸红,连忙嗤笑道:“吼!你脸红了,你脸红什么?难不成你还觊觎裴伷先?”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邵一白臊得老脸通红,连忙紧走几步,招呼衙役们下山。
程少卿被怼得脸红脖子粗,还想回嘴,只觉得身边一阵清风刮过,素白的衣袂翻飞,裴伷先已经站在七步之外,微微朝着孟鹤妘弯下腰肢。
艹!
我特么眼瞎了吧!
这是个假裴伷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