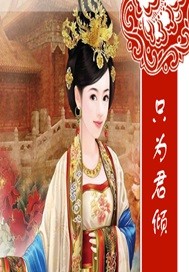库乐从宫里铩羽而归,天后并没有即刻派兵支援瓦特平叛的打算,俨然是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他磋磨不错大盛这边的态度,但从玄武门外加了三倍的羽林军可以看出,大盛皇帝的情况并不乐观。
从昨日开始,京都城里关于罗刹的传闻已经越演越烈,各个坊间不仅加强了巡城司的密度,城外的京畿大营也有所动作。十几年来,京都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动静,想来……
“主子。”
门外传来阿瞳布的声音,库乐连忙收好伤药,拉紧衣襟:“进来吧!”
阿瞳布推门进来,脸色略微有些难看:“整个驿站里里外外都是琅琊王的人,大盛这位天后似乎对我们并不放心。”
库乐端起茶杯倒了杯水:“斑布和木樨呢?”
“斑布刚被送了回来,木樨留在宫中,听说天后已经下旨册封郡王了。”他反手关上门,“还有一事。”
库乐抿了口水,低头摆弄桌上的瓶瓶罐罐。
“京中凡三品以上的官员均在今晚进宫了,裴伷先坐着张平的马车也从玄武门进了永寿宫。”阿瞳布偷偷用余光看他,拿不准他到底怎么想的,“远在冀州和陇洲的魁王,长安王于昨日进了淮州境地,不出三日便会抵达京都。”
库乐忽而一笑,仰面靠着椅背,用手挡住眼睛。夕阳的余辉从洞开的窗棂洒下来,在他脸上留下一片斑驳:“大盛如此的大的动作,恐怕京都要有大动作了。”
“所以公子,我们该回去了。如果大盛皇帝真的有了什么不妥,新帝对瓦特态度不明,我们再想出城,就难了。”
库乐突然放下手,目光幽幽地透过虚掩的窗棂看向窗外迤逦的夕阳,许久才淡淡道:“是呀,该回去了。”
————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防火防盗……”
更夫敲响了二更的棒子,拎着铜锣走出巷子,两只野猫“咻”地一声从角落里窜了出来,几个起落,消失在巷口。
长乐坊的坊墙外,数道黑影消无声息地潜入了铜雀街。
黑影快速地穿梭在院落之间,熟门熟路地来到铜雀街尽头的一处二进院落门前。
院子里没有灯,但胜在今日月光正好,借着清冷的月光,黑影们摸到了西厢房的窗前。
为首的黑衣人带着一副精致的面具,他轻轻抬了抬手,身后的黑衣人忙从怀里掏出一根吹管,点开窗纸,小心翼翼地将吹管穿入窗纸,吹入迷烟。
过了大概有一盏茶的功夫,迷烟生效后,黑衣人伸手轻轻推开窗棂,一翻身跳了进去。后面的人见同伴已经进去,扭头看了眼显然是首领的鬼面,得到他的首肯后,自动向左右散开,把整个房间围住。
房间的门从里面被打开,是刚刚翻进去的黑衣人。
夜莺发出凄厉的叫声,但这并不能影响他们的行动。
鬼面慢悠悠走进房间,视线若有似无地朝床上看去。
孟鹤妘面色微白地躺在床上,即便屋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也没有丝毫醒来的迹象。
鬼面冷哼一声,踱步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看向她。
其他人开始紧锣密鼓的搜东西,唯有鬼面一直站在床边看着孟鹤妘,并缓缓抽出腰间的弯刀。
“你真的要杀我?”
孟鹤妘紧闭的双眼猛地挣开,袖里刀抵在鬼面的腹部。
鬼面微怔,握着弯刀的手一顿。
这时,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火把的光亮把整个院子照得亮如白昼,三千虎贲军几乎把整个院子团团围住。。
裴伷先分开人群,看着屋子里晃动的人影,面色阴沉地道:“出来吧!这里已经被包围了。”
相较于院子里的喧嚣,屋子里安静得落针可闻。
一名狼卫突然冲到床边:“我们上当了,外面全是虎贲军。”
鬼面握着弯刀的手紧了紧,目光阴鸷地看着床上的孟鹤妘:“把七星锁交出来。”
“凭什么?”孟鹤妘冷笑一声,手里的袖里刀往前松了松,尖锐的刀剑划破衣料,刺破他的皮肤。
空气中一点点弥漫开淡淡的血腥味,他微微皱眉:“怎么?你就甘心被裴伷先利用?”
孟鹤妘嘴角一抽,强作镇定地道:“你怎知我不是跟他合谋?”
鬼面冷哼,身子微微向后,孟鹤妘连忙顺势从床上起来,屋外的火光把屋里照得透亮,衬得她脸上的笑容越发的妖冶:“就算我不跟他合作,也有办法抓住你,不是么?”她似笑非笑,“你看,你现在不就是上钩了么?”
裴伷先有他的大事,她可以做她的小事,这些饿狼从瓦特一直跟到了大盛,她已经没有耐心陪他们玩儿了。
“所以你是故意搬出来的?”
孟鹤妘勾了勾唇,眼角余光扫了眼窗外:“只是不想牵连他人罢了。”
鬼面微微一怔,想要抬手挥刀,结果手抬到一半,弯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把青石板的地面砸出几点火花。
鬼面瞳孔微缩,不敢置信地看着孟鹤妘。
孟鹤妘咧嘴一笑,抬手指了指床头柜上摆着的八角香炉:“下药这种事,都是姑奶奶玩剩下的。”仿佛是印证她的话一般,屋子里的狼卫纷纷倒地。
鬼面身子一晃,靠着梳妆台稳住身形:“呵!是我疏忽了。”
“你疏忽的事还多着呢,就比如白虫……”她冷哼一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你们知道大盛皇帝喜食鹿血,便把得了白虫病的牦牛混入贡品之中,鼓吹牦牛血的奇效,诱使皇帝食用。那位新安皮货行的老板就是当初在益州卖皮影师鬼雾草的人,离开益州之后,他便在京都布局,提前把患病的牦牛混入西市之中,一手炮制了夜行罗刹,以便你入京之后另做图谋。”这一场局做了这么久,不可谓不精密,只是他大概没想到自己会搅和进来,更没想到裴伷先会和高宗皇帝联手破局。
鬼面苦笑出声,身体顺着梳妆台向下滑落,“哈哈哈哈!是啊,除了你,怕是也不会有人知道白虫一事。”
“不,你最不该疏忽的,是裴伷先。”她下意识侧头看了眼映在窗纸上晃动的人影,不知为何,她就是知道,那个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人是裴伷先,“裴伷先一家蒙难,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手,可偏偏他是裴伷先。一门三代为相的人,绝不会置天下安慰于不顾。错就错在,你不了解他。”她脸上的表情一暗,猛地伸手,一把扯下他脸上的面具,露出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
库乐下意识扭过脸。
孟鹤妘面无表情地丢下面具,转身往外走。
“滚滚。”库乐突然出声,“你是什么时候,怀疑我的?”
孟鹤妘脚步一顿,回头看他:“长风亭。”
库乐微怔,孟鹤妘的目光落在他耷拉在腿边的双手,掌心已经被指甲抠的血肉模糊。
“从始至终,鬼面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她眼神微暗,咬了咬牙,“而我认识的鬼面是个话唠。”事出反常必有妖,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库乐勾了勾唇:“可你怎会觉得是我?”
孟鹤妘并不急着回答他的话,从怀里掏出手帕丢在他手边:“别祸害你的手了,我下了了半日醉,没睡半日,你动不了的。”
被识破了心思,库乐反而扯唇一笑:“被你识破了啊!”
“对,识破了。”孟鹤妘抿了抿唇,“一开始我也没怀疑过你,直到我确定是白虫作祟后,我便猜测,你个胡禅之间或许有些关系。这世上,能想到用白虫害大盛皇帝的人,也就只有你了。”
库乐眼神微暗:“所以你就没想过,我为何要背叛葛丹?”
是啊,一个温柔少年,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个工于心计,为达目的不折手段的人?
“我以为你并不在意那些。”她以前是真的这么以为的,只是她似乎从来不曾真正的了解过他。
库乐的眼神已经开始涣散,他拼命地攥紧了手里的帕子:“如果我说,我从未想过杀你,你信么?”
孟鹤妘身子一僵,抿唇不语。
库乐突然轻咳两声,苦笑道:“其实我也不信。”
孟鹤妘眼角一抽,差点被他气乐了:“哦,感情着,我还要感谢你的不杀之恩?”
库乐无辜地眨了眨眼,神情格外的温柔。他微微勾了下唇,用力勾了勾手指,轻轻点了五下。
孟鹤妘微微一怔,这是他们少时说悄悄话的小暗号。
这个时候,他还想跟自己说什么?
她抿了抿唇,甩出袖里刀压住他的脖子:“你想说什么?”
库乐忽而一笑,突然用尽全身的力气,抬手勾住她的脖子,温热的薄唇轻轻贴在她的耳朵上:“你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七星锁里藏着燕云十二州的布防图和宝藏的么?”
孟鹤妘猛地推开他。
库乐咧嘴一笑,微微扭头看向窗棂。
“裴伷先,是裴伷先在益州放出的风声。至于他到底要做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
裴伷先面无表情地看着窗棂上一个个倒下的人影,垂在身侧的手紧了又紧。木石担心地上前一步,目光扫过窗棂:“公子,现在怎么办?”狐狸就在里面,如果贸然攻进去,狐狸肯定会受伤,可如果不攻进去,迟则生变,以后未必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将胡禅安插在京都的钉子全部拔除。
裴伷先知道他的担忧,抿了抿唇:“再等等。”
“裴公子,不能再等了。”虎贲军中郎将刘奎走上前来,面无表情地看着裴伷先,“迟则生变,若是出了什么叉子,裴公子恐怕担不起。”
“我说了,再等等。”
“可是……”
眼前一道寒光闪过,刘奎只觉得脖颈一凉,一把软剑已经虚虚的缠在他的脖子上,剑的另一端,是裴伷先阴鸷的眸子,他狠狠咽了口吐沫:“裴伷先,你想抗旨不成?”
裴伷先讥讽地勾了勾唇角:“我说过,再等等。”
刘奎脸一黑:“你特么的疯了?你要谋杀朝廷命官?”
裴伷先抖了下手,缠在刘奎脖子上的软剑骤然收紧,在他最脆弱的皮肤上留下一道红痕。
刘奎面无表情地咬着牙,目光阴郁地看着他:“好,我再等一刻钟,一刻钟之后,他们要是不出来,就算你杀了我,我身后的三千虎贲军也一定会冲进去。”
裴伷先抖手收回软剑,看也没看刘奎一眼。
刘奎抿了抿唇,抬手摸了一下脖子上的伤口,毫不怀疑,如果刚才他真的带人冲进去,裴伷先能绞了他的脖子。
他拧眉看着面前的裴伷先,试图从他脸上找到当年名满京都的少年天才的影子,但令他失望的是,面前的男人似乎决绝地与过去做了彻底的切割,再也不少以前的裴家公子了。
他是一柄藏在暗处的疯刀,一旦出鞘,便是血流成河,势不可挡。
这时,虚掩的房门突然从里面打开,烈烈的火光中,孟鹤妘面无表情地从里面走出来,目光落在裴伷先脸上时不自觉地闪躲了一下。
“狐狸!”木石连忙冲过去,“你……”
孟鹤妘懒懒地撩了下眼皮,打了个哈气:“哦,原来我的院子这么热闹啊!”
木石嘴角一抽,偷偷看了一眼身后的裴伷先,莫名的,总有种要完的感觉。
虎贲军一窝蜂地冲进屋里,偌大的院子里一下子空荡下来,孟鹤妘下意识搓了搓手臂,这才意识到,原来已经快入秋了啊!
“走吧!”裴伷先伸出手,孟鹤妘连忙侧身避开,脸上带着笑,“我累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裴伷先低敛着眉看向停在半空的手,喉咙里莫名一阵发堵。
孟鹤妘突然有些讪讪地,回头看了眼人影攒动的窗棂:“你们大盛人,是不是都喜欢下棋,且自允为棋艺高手。”所以但凡行事,总喜欢把别人都算计其中?
后半句话她没说,只低头看着鞋面上的花纹,心里有些发笑。
裴伷先捏紧拳头看她:“君子六艺是启蒙必修的课程。”
孟鹤妘险些被他气笑。
她是问他什么狗屁倒灶的君子六艺么?
她拧眉看他,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然而让她失望的是,这个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坦荡如斯,呵!真是见了鬼的坦荡。
裴伷先不喜欢此刻她脸上的表情,有些薄凉、有些失望、更多的是一种冷漠的疏离,他莫名有些心慌,想要伸手去拎她的领子,督促她回家。
孟鹤妘再次避开他的手:“我累了,想睡觉了。”
他微怔,眼中露出一丝迷茫,讷讷地说了声“好”,转身往外走,结果走了几步发现她并没有跟上。
孟鹤妘看着他回头,两个人明明隔着不远的距离,却好像隔了天涯海角,她越不过去,他也不愿停下脚步。
“哎呀,困顿这玩意儿来得猝不及防的,你……”她咧嘴一笑,玩世不恭自朝他挑眉,“自便吧!”说着,一溜烟进了旁边的厢房。
裴伷先怔怔地看向黑漆漆没有意思光亮的厢房,心底里说不出的窒闷。
“公子。”木石同情地看了一眼裴伷先,讪讪地摸了下鼻尖,“你说,狐狸这是不是生气了?不打算回去了?”
裴伷先扭头看他:“你很闲么?”
木*殃及池鱼*石脸一垮:“我这就去帮刘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