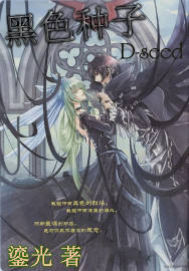益州这地方吧,虽然是边城,但是随着多年前云霞郡主和亲,瓦特与大盛的关系得到缓和,两国也开始贸易往来,作为两国交界地的益州颇得了一些好处,近几年更是富得有些流油。
但凡是富得流油的地方,要么是天子脚下,治安良好,夜不闭户;要么就是天高皇帝远,三教九里窝里斗,你砍我来我吃你。
益州先后换了几任县令,效绩奇差,要说整治谈不上,搅屎棍倒是都做得不错,大牢里乱七八糟关了一堆人,有罪的没罪的,谁也说不清。
孟鹤妘被五花大绑地丢进大牢里,同行的还有裴伷先和木石这俩王八蛋。
领路的小丫鬟和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关在隔壁,从一进来就痴痴傻傻地喊着:“夫人死了,夫人死了。”
孟鹤妘一个人背靠着草垛子坐着,一边偷偷用袖里刀割绳子,一边恶狠狠地瞪着对面的裴伷先。
牢房里的环境比瓦特的马厩还不如,猫崽子大小的耗子跟遛弯似的在里面到处晃,看中哪个了,还能胆大包天地窜过去闻一闻,好像下一刻就能咬一口。
她愤愤地冷哼一声,用脚尖挑开晃过来的耗子。耗子“吱吱”叫了两声,身不由己地朝着裴伷先脑门飞过去。
孟鹤妘巴不得能命中目标,可是这狗男人运气好,耗子飞到一半翻了个身,硕大的身体扭转出霓裳舞的优美弧度,安全落地后,呲溜一声穿进角落里的耗子洞里。
绑人的绳子大概是假冒伪劣产品,孟鹤妘蹭了几下就给割断了。
她偷偷看了眼牢房外,趁着无人注意,偷偷活动了一下双手,然后一点点往裴伷先那边蹭。
木石一直注视着她,发现她往这边蹭,瞬时紧绷了神经,一脸戒备地瞪着她。
孟鹤妘翻了个白眼:“你瞪着我干什么?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团结,团结懂不?”
木石冷哼,朝她伸出手:“那你先把我家公子身上的毒解了。”
小忠犬还不傻。
她讪讪地笑了下:“不巧,解药我没带在身上啊,要想解毒,恐怕要先出去才行。”说着,目光落在一直面无表情的裴伷先身上,“喂,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啊?你那情人真叫人杀了啊?”
裴伷先低垂的眼睑懂了懂,看傻子一样地看着她。
孟鹤妘感觉到了深深的恶意,不过她不怕,她千里迢迢从瓦特到大盛,死里逃生了多少次了,这点程度还不能把她怎么样。
她蹭蹭蹭,终于蹭到了裴伷先旁边,挨着他靠墙坐着:“按理说你一直跟我在一起,杀人是不可能杀人的,所以,是有人陷害你?情敌?”她想了一路,觉得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
裴伷先扭头看她。
“你别光看我,说话呀!”
“说什么?”裴伷先终于开了尊口,但等于没开,跟放了个屁一样。
孟鹤妘有点不太乐意,用肩膀顶了顶他的胳膊:“你人都偷了,这个时候还是痛快点,找到凶手才能洗刷冤屈。”
裴伷先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来,那双微敛的眸子如同淬了墨,就那么阴沉沉地看着她,好像一条正在吐信子的毒蛇。
旁边牢房里的小丫鬟大概看不下去了,突然咬着牙滚到铁栏边,义正言辞地指责孟鹤妘:“姑娘,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表哥呢?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崔夫人也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两个清清白白,夫人是,是因为有事儿求他才让我请公子来的。”
小丫鬟大概不知道,有些事儿吧,它总是愈描愈黑,但孟鹤妘现在不想教她做人,挪着屁股又一点点蹭到小丫鬟身边,背着双手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既然你说我表哥跟你们夫人没关系,那她为什么要让表哥大晚上来江府?”
小丫鬟脸色微红,瞄了一眼裴伷先,讷讷道:“我叫采薇,是崔夫人身边的大丫鬟,那个是翠花,也是夫人身边的丫鬟。”她用嘴指了指旁边挨了木石一手刀,现在更痴痴傻傻的女人,“我们夫人其实根本连裴公子都没见过,是因为府中最近不太平,锦绣阁里总闹鬼,夫人吓得经常梦魇,我听人说朱雀街的裴公子能抓鬼,治癔症,便跟夫人建议,让她请裴公子来府中看看。可是没想到,没想到……”
孟鹤妘安慰了哭哭啼啼的采薇两句,又挪着屁股蹭到裴伷先身边:“哎,她说的都是真的啊!”
裴伷先目光向下移动,落在她的挨着地面的屁股上。
孟鹤妘愣了下,顺着他的视线往下,脸“腾”地红了。
“你看什么呢?登徒子。”
裴伷先抿唇不语,挪开视线。
孟鹤妘本来没觉得怎么样,结果刚才他这么一看,她倒是反应过来,屁股经她这么来回几蹭,竟然火烧火燎地疼。
裤子不会破了吧!
她深深地忧伤了一下,悄悄把手探到屁股下面摸了摸,幸好没破,差点晚节不保。
裴伷先拧眉看着她兀自在哪儿折腾,实在没眼看,索性扭头看向隔壁牢房里痴痴傻傻的女人。她的嘴里还在嘀咕着:崔夫人死了,好多血,好多血。
孟鹤妘也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这才注意到,她襦裙下摆一团血迹。
“喂,这个崔夫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啊?”她用胳膊撞了下裴伷先。
裴伷先淡淡乜了她一眼,双手拢进袖子里,靠在墙上假眠,俨然一副不想说话的样子。
孟鹤妘是个闲不下来的性子,扭头又看木石,算了,这小忠犬就是根木头,能懂个屁啊!
————
监狱里没有时间可言,孟鹤妘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正昏昏欲睡的时候,感觉身边的人动了一下,猛地睁开眼,这才发现裴伷先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昏暗的走廊尽头。
莫名的,她就是感觉到了一种紧张,扭头问他:“怎么了?”
裴伷先低头看了她腰腹一眼,孟鹤妘一怔,顺着他的视线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自己竟然坐到了他的长衫下摆,原本顺滑的苏锦已经被她的屁股蹂躏成一坨。
她干巴巴一笑,连忙挪开屁股:“哈哈,你这衣衫的料子好像不太好啊,不禁坐啊!”
裴伷先嘴角微抽,几不可查地拉回自己的衣摆,并用手轻轻铺开了皱成一坨的地方,可惜效果不太好,怎么看都是一坨。
孟鹤妘觉得这人有点强迫症,想告诉他皱了就皱了,你现在是在坐牢,不是在逛花楼,还讲究衣衫工整。
可惜话到嘴边还没说出来,走廊两边突然躁动起来,原本或趴、或坐、或趟着的犯人瞬间如同打了鸡血一样全部冲到牢门前,扯着嗓子不要命的喊:“冤枉啊!”
“放我出去,老子没杀人。”
“冤枉啊!”
……
此起彼伏的嚎叫声成功地打消了孟鹤妘喊冤的热情。
走廊墙壁上挂着的人鱼灯忽明忽暗,牢头用力甩了一把鞭子,牢房瞬时安静如鸡,那一瞬间,孟鹤妘想到了科尔曼草原上的羊群。
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孟鹤妘不自觉地跟着紧张起来,探头往走廊里看。
不一会儿,几个穿着衙役服的捕快簇拥着一个年青人走进地牢。走廊里的光线有点暗,但架不住这位爷自带光芒,那把挎在腰间的金刀亮得能闪瞎人眼。
“这是谁啊?”孟鹤妘扭头看裴伷先。
裴伷先撩起眼皮看了眼已经走到牢房门前的人,懒洋洋地吐出三个字:“不认识。”
这狗男人竟然说不认识我?
气场两米八的金刀男瞬间如同炸了毛的猫,抽出腰间的金刀,大手一挥。
“咔吧!”
小孩儿拳头大小的铜锁被从中间一分为二,“啪啪”两声掉在地上,牢房里顿时爆出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孟鹤妘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的铜锁,又看了看金刀男那一脸“你欠我八百万贯”的表情,连忙双手撑着地面,再次挪动小屁股。
这哪里是不认识啊!这分明就是有深仇大恨的!
我挪,我挪,我挪挪挪,屁股磨得直发疼,愣是没移动半寸。
“你去哪儿?”
孟鹤妘不敢置信地回头,果然,这狗男人正面无表情地抓着她的后衣领子。
“裴伷先,真没想到啊,你也有今天。”淬了毒一样的嘲讽声从头顶传来,孟鹤妘低头看着映入眼帘的黑色皂角靴,不知道这个时候跟裴伷先撇清关系是否还来得及。
裴伷先用力将她往后拽了下,把她拽到身边。
“你放手。”
“不放。”
“你放手。”再不放她就发飙了。
裴伷先撩了下眼皮子,拽着她脖领子的手更用力了:“表妹。”
靠!这个时候,谁是你表妹?
“大人,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他表妹。”孟鹤妘连忙抬头,一脸委屈地看着程少卿,目光在他身上松垮垮的官服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到那把牛逼轰轰的金刀上,“大人,我是冤枉的,我就是个良家民女,是他把我绑来的。”
程少卿握着金刀的手“嘎巴嘎巴”直响,孟鹤妘都怕他一不留神把刀给捏断了。
“大人?”孟鹤妘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结果程少卿突然就跟抽了羊癫疯一样,把金刀往地上一拄,原地转了两圈,指着裴伷先一阵大笑。
“哈哈,裴伷先,裴伷先,你说你,你怎么就混到这种地步了?连你表妹都急忙跟你撇清关系。”
“大人,我真不是他表妹。”孟鹤妘连忙澄清。
程少卿大手一挥:“不,你是。”
“不,我不是。”可是无论孟鹤妘再说什么,程少卿就是一心认定她是裴伷先的表妹,为了苟活,可以出卖青梅竹马的表哥。
孟鹤妘觉得和傻子说话实在是太费劲,索性一扭头,再也不说话了。
大概是笑够了,程少卿把金刀挎回腰间,回头扫了一眼身后乌压压一片的衙役,轻咳一声:“行了,你们都先下去吧,我有事儿要问这几个犯人。”
顺利清走了吃瓜群众,原本热热闹闹的牢房再次安静下来。程少卿让人给他自己拿了把太师椅,大刀阔斧地坐在牢房里,看起来威风凛凛。
木石黑着脸蹭了过来,挡在程少卿和裴伷先中间。
程少卿翻了个白眼,用金刀把他扒拉到一边:“你个小屁孩,哪儿有事都有你呢?怎么?我还能把他吃了不成?”
木石瞪圆了眼睛,贝齿咬着薄唇,看得孟鹤妘莫名有点……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