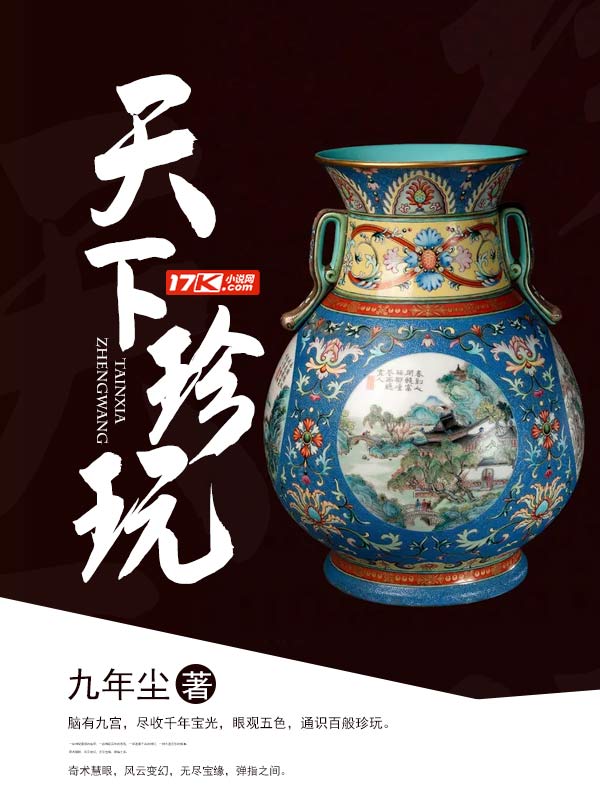民间近来口口相传一个故事:新科状元考取功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名落孙山,心灰意冷时又怕无颜见父老,行至江边,便生出一死了之的念头,幸好被一名女子所救。
经这名女子苦苦相劝、悉心陪伴,状元郎才重整旗鼓,继续科考之路,临行时两人跪拜天地私定了终生。
岂料,金榜题名时,圣上将其赐婚于长公主,状元郎不愿辜负糟糠,长跪于午门外。那名忠义的女子正是姜淑妃身边的女官虞氏。
故事渐渐传开后,百姓们皆为虞氏的深情动容,为状元郎的不离不弃感动。
人人称颂:世人都爱攀龙附凤,唯状元郎飞黄腾达之时还记得相逢于微时的那个她。请愿之声渐起。
圣上却不肯舍弃如此优秀的妹婿,毕竟长公主的婚嫁问题一直都是他的一块心病。
几经思忖,圣上最终同意让虞氏作为平妻同一日嫁入状元府邸……
傍晚时分,状元府中,金桂飘香,张灯结彩,宾朋满座。
“皇上、淑妃娘娘、贤妃娘娘驾到……”有人朗声诵道。
众宾客跪下山呼万岁,状元郎的父母更是跪伏在人前,不敢抬起头来。
皇帝亲自将老人家扶起,笑道:“静和自小与朕亲厚,她的婚礼朕就不请自来了。”
“陛下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老夫得见圣颜喜不自禁。”袁父连忙拱手道。
皇帝爽朗地笑了两声,被状元郎迎至主位落座。
皇帝坐席旁各有两张椅子,良贤妃已经踱步往右边走,采苓却站着没动。
陛下落座后见左边的位置空空如也,目光一瞥,提醒她该入座了,否则众宾客也不敢入座。
“请问袁大人,虞府娘家可有人来?”采苓问。
“臣妻漫云乃孤女。”状元郎回答。
“不知袁大人可方便在那边设立一桌虞府娘家的席位?”
“娘娘这是?”
“本宫便是漫云的亲人。”
“娘娘相赠的十里红妆,臣感恩不尽,实在不敢再劳烦娘娘。”状元郎拱手道。
“本宫相赠之物那是给妹妹的嫁妆,与袁大人并无多大关系。”采苓道,说罢自顾自找了大堂内的席位坐下。
状元郎立刻派人去安排坐席,其后,又躬身相迎,使其落座于皇帝的席位下方,与袁家父母同席。
典礼上,状元郎捧着一个绸缎绣球,绣球的两侧以丝缎相连,身旁的两名女子以红盖头覆面,各自拽着丝缎的一头缓缓走向高堂。
堂上手臂粗的红烛内火光跳跃,人群中有人窃窃私语:“状元郎可真是好福气,左拥右抱,从此享尽齐人之福。”
与皇帝、良贤妃同坐于一侧的姜淑妃只露出一抹苦笑,姻缘之路上,两个人携手仍是曲折,三个人未免也太拥挤了。
转目一瞧,良贤妃正含笑望着皇帝,皇帝的目光却在静和长公主身上。
片刻后,“静和!”皇帝怒喝。
采苓连忙转过头去,瞧见堂前的红烛不知何故落下来,砸在漫云的脚边,顷刻间已将她百褶裙的裙边点燃。
“漫云!”采苓连忙提醒。
功夫身手都在普通人之上的漫云,今日似乎入了魔障,出宫时心不在焉,此时竟然躲不了一根落下的红烛。采苓倏得站起身,却被皇帝拽住手腕,她挣了挣,未果,便转过头来狠狠盯着他。
此时,袁府的家丁已端了盆水来将漫云裙上的火浇灭。
那条红裙上的山茶花和蝴蝶,是漫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那些个翠微宫里无眠的长夜,采苓就躲在灯影里看她绣花,并笑她恨嫁,如今那些着火的山茶被水一浇便都荼靡成灰。
“你是什么东西?敢与本殿争男人。”静和声音虽小,却被采苓听得一清二楚。
“放手!”她已是极为冷静。
“大好的日子,姐姐怎敢如此顶撞陛下?”良贤妃责道。
皇帝手一松,采苓跨步而上,推了状元郎一把,自己站到两名女子的中间,她深看了眼漫云破损的百褶裙,转过身子,一巴掌拍在静和长公主脸上。红盖之下的长公主忽然懵了,竟揭开盖头来,扬手要还击,采苓没动,袁杰遗挡在她跟前,替她挨了一掌。满座皆惊,随后一片哗然。
“你让她在大婚之夜受辱,本宫尤其失望。这一掌……”众人皆以为事情就此作罢了。
熟料,姜淑妃再次扬起手臂,重重赏了一个巴掌在静和长公主的脸上,“无论何时何地,本宫的人都不许你碰丝毫!”
“皇兄!”静和捂住脸哭求。
皇帝冷声吩咐左右,“起驾回宫。”
回程的马车内,采苓坐于极远处,将皇帝身边的位置留给良贤妃。贤妃讨巧,沿路上一直在聊沧凌公主的趣事。
“静和是朕的亲妹妹,让她嫁给袁杰遗,朕以为是下嫁,本已对她心怀愧疚,你为何非得当众给她难堪?”皇帝冷声问。
采苓勾着一抹冷笑,借着月光和窗外的灯火见他正凝视着自己,便回答: “让漫云与静和同侍一夫,臣妾也很愧疚。”
“你!”皇帝气极,冷静了片刻后,才语重心长道,“静和她不过是要在袁家立威,漫云知道,袁杰遗也知道,你那么聪明的人为何就不懂呢?”
“臣妾向来愚笨,还望陛下见谅。”
“你!”皇帝压低了声音,“果然是恃宠而骄。”
良久无声。
“怎么?不顶嘴了?知道自己理亏?”片刻后,皇帝问。
良贤妃连忙转过头来查看,片刻后惊呼:“陛下,姐姐她晕倒了。”
次日,翠微宫中,韩医正亲自送来一碗深棕色的药,苦口婆心道:“师父听闻娘娘您再次晕倒,又仔细研究了微臣所述的脉象和症状,开了这个安胎的方子。”
“师父为何不肯亲自过来?”采苓问。
韩医正叹了口气,“娘娘当初在太医局里与师父朝夕相处,陛下到底是介怀的。虽然师父并不在意,当徒儿的自然是要为他考虑周全,往后娘娘有什么话同微臣说便是,微臣自当转告师父。”
“我也没什么要同师父说的。既然他一切都好,便是最好了。”采苓笑道。
“娘娘快喝药吧。”韩医正将药碗放至她跟前,“娘娘可是想要亲自看一眼药方?”
“不用了。我相信你。”采苓端起药碗一饮而尽。
韩医正走后,采苓望着空落落大殿,心生惆怅。昨夜皇帝守在床边,待她醒来,只说了一句话便头也没回地离开。
他说:“朕虽答应过你即使是你恃宠而骄,朕也不杀你,可若是朕的孩儿有半点差池,朕永生都不会原谅你!”
那也是我的孩儿,我又怎会不全力相护?采苓心道。
不过十日,便出了差错。
中秋节的晚上,紫微宫中设了家宴,后宫诸妃陪太皇太后赏圆月,静和长公主携驸马列席,歌舞不休,丝乐未断。
采苓照例坐在杨贵妃下首,良贤妃以上。皇帝与太皇太后并坐于堂中主位上。驸马行礼时,太皇太后笑道:“果真是个标志体面的人儿,怪不得哀家的孙女非嫁不可。“
“老祖宗……”静后娇嗔,“孙女哪有?”说完后双手捂住发烫的脸颊。
众人皆笑,唯独采苓面无表情。
“姐姐近来兴致不高,是否身体不适?”良贤妃故作关切,“姐姐肚里的小皇子,陛下可是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着呢。”说完后,瞥视杨贵妃。
采苓也侧过头看了眼杨贵妃,见其很快收起笑容,只垂首漫不经心捋了捋裙上的褶皱,似并不愿意置身事中。
采苓心中有了几分思量,转头瞧了眼皇帝,见他正漫不经心喝着宋美人亲自斟的酒。采苓将目光移到对面,跳过正喋喋不休讲述新婚趣事的静和,与袁杰遗四目相对。
那目光依旧温和,一双眼睛仿佛带着笑,依旧是多年前东喜楼里的锦衣公子,哪里会是朝堂上的工部要员,后宫中的长公主驸马?
她薄唇勾出一丝苦笑,举杯对着他,这一杯敬逝去年华仿佛指缝间的流沙。
她跟前的席案上放着的酒壶里只是一些清茶,她刚落座时便闻到了清淡茶香,所以才敢喝了数杯。袁杰遗却不知,只端着酒杯怔怔望着她。
“啪!”一声脆响,一只夜光杯落在她脚边,碎成了渣渣。
抬眼瞧去,皇帝正朝着此处冷然睥睨,而他身侧的宋美人早吓得花容失色,握着酒壶的手微微打颤。
采苓也受了一惊,却仍然将杯中的清茶一饮而尽。宫人们连忙来收拾碎渣。
“谁让你们给她上酒的!”皇帝责问。
“启禀陛下,淑妃娘娘案前的酒壶里只装着清茶。”玉德垂头丧气,“用酒壶装茶水是奴自作主张,奴有罪,求陛下责罚。”
殿内鸦雀无声。片刻后,皇帝面色未变,只冷声道,“下去领罚。”
“等等。”采苓忽然站起身,大腿触碰到小案使得案上的茶壶左右摇晃,她又弓身将之扶稳。可就在直起腰之时,腹中一阵剧痛,她故作无异,坐回席位上。
“姐姐可是想为玉德公公求情?”良贤妃问。
采苓的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脸色逐渐苍白,笑容却洋溢在脸上,努力提了口气:“玉德好大的胆子,竟敢用清茶唬弄本宫,应当罚。”
“姐姐果真这样想?”良贤妃一再找话。采苓只点了点头。
恰此时,一股热流滑过两腿内侧,她明白,见血了,腹中胎儿怕是保不住了。
可是她却不敢动,皇帝还端坐于大殿之上,太皇太后慈眉善目地望着众人,杨贵妃正端详着一块桂花糕,良贤妃拨弄古筝准备亲自献曲一首,赵昭仪托腮望着皇帝,宋美人跪坐在皇帝跟前,含笑为他再倒了一杯清酒,其余说不上名字的嫔妃们坐在一处,互相低语。
太热闹了,热闹到她不愿去打扰。在这月圆的中秋夜,她第一次生出了害怕的念头。
目光移向对面,袁杰遗也正焦急地回望她。到底是陪过她朝夕的朋友,她细微的动作又如何能逃得了他的眼睛?眼看他撑着小案就要站起身来,采苓狠狠瞪他一眼,示意他不可轻举妄动。
目光再回到皇帝身上,见他正饮着宋美人递来的一杯酒,微眯着眼睛看着莲步轻移走入殿中央的良贤妃。曲子悠远绵长,醉心其中令人仿佛身处空山幽谷。一曲终了,皇帝含笑拍了拍手。
采苓一只手抚着腹部,一只手拽过长而厚重的裙摆垫在臀部之下,深怕血浸透了中裤,无心听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