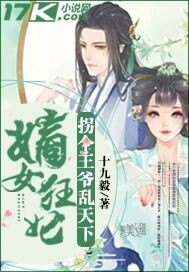站在雨花阁城楼的顶部,可以将长安城尽收眼底。
还是内廷女官之时,她寻得空闲便爱攀着石阶往上走,凭栏眺望东边,那是墨渊阁和东喜楼的方向。
今日到底是贪心了些,跟在一众宫人身后将吴姑姑送出华清门,本就该老实回去太医局,可是却鬼使神差走上这雨花阁。
傍晚时分,云霞将靛蓝色的天空晕染出红橙相间的绚丽,宫中一排排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开得正好,极目远眺,长安城中华灯初上,车水马龙。
她小心翼翼看了眼紫微宫的方向,确定宫道上并无郁墨言的身影,暗自决定再站一柱香的时间就回去太医局。
一年前,郁墨言在她额头上刻出一朵嫣红的曼珠沙华。
“彼岸花。”她对镜自照,尤是满意,“为何偏偏是此黄泉之花?”
他的目光极柔和:“为了覆盖那个字,我只能选了这花。“
“嗯。我挺喜欢的。”她笑道,“只要你不同我生死两隔,永不相见。”
不过是随口一句笑谈。
“苓儿。这朵花在你额头之上很美。”他正色,“我会想法子送你出宫,从此别再回来了。”
她收起笑容:“要送我走?能去哪里呢?天地虽大,已没我容身之处。”
“北国可好?”他问。
“沈泰与我素来水火不容,父亲更是从来不管我的死活。”
“云南想去吗?”他再问。
“殿下有十八位姬妾,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怕死。”
“隐居乡野,从此不问世事?”他没有放弃。
“这么说来,你果真是要与我永不相见?”采苓笑着打趣。
“苓儿……”他蹙眉。
“能留下来吗?留在你身边。”她问。
“我会换掉所有认识你的人。”不过一瞬,郁墨言回答。
她摇了摇头,顺手拿起一张绢布遮住半张脸,“我甘愿再不以真面目示人。只要我不说话,没人会认出的。”
一个月之后,她跪在他身前敬了三杯茶,从此成了他唯一的爱徒。
时至今日,太医局内的学业和事务都相当繁杂,不比东喜楼中恣意潇洒,也没有垂拱殿内的游刃有余。昨日解剖一头母羊差点要了她半条命,师父还说让她做好心理准备,不久后便会让她解剖新鲜的尸体。人的尸体。
即便如此,近日心中总能生出四个字——“未来可期”。
她已经在幻想自己行走江湖,被人称为神医的模样,那时候她一定是一身白衣若雪,手握一把玉折扇,姿容绝代。
凭栏眺望时,忽然就笑出了声,还好那轻轻的笑声快速地掩盖在北风猎猎的呼啸声中。
“小四……“
这天籁之声又是打哪儿来的?是梦里,还是幻觉?
她两只手拍在石栏上,哀声叹口气。
“你是何人?”无比熟悉的声音再次从身后响起。
随后是玉德气喘吁吁的声音:“城楼上风大,陛下可要当心龙体啊。”隔了一瞬,才惊恐道,“来着何人?见了圣上却不知回避。”
采苓心中一凉,埋头转身,屈膝行礼,一气呵成。
她的腿已经很酸了,沈牧迟却仍一声不响站在原处。
玉德上前来仔细瞧了她一眼,问身旁的侍卫:“这位可是太医局郁大人的关门弟子?”
守卫弓身回答:“正是宋医女。可惜是个哑女,听不见公公的斥责。”
“启禀陛下,此人不过哑女一名。奴这就将之打发走。”玉德拉了拉她的胳膊,下巴指向出口,示意她速速离开。
她转身要走,可是偏偏贼心不死,临走之前没忍住,偷瞥了沈牧迟一眼。
听说,陛下如今正是盛年,连师父也只能每隔半个月去请个平安脉而已,其余人更是从未有见到龙颜的时候,她便很少听说他的近况。
真是可笑啊,既是要杀自己的人,她竟有心思关心他的近况。
面纱之下,她唇角轻轻勾起,露出一抹心酸的笑容。
四目相对后,她的心扑通跳个不停,连忙转过眼去,出口就在十步之外,她一定可以落荒而逃。
“别走。”倏忽间,皇帝已经抓紧了她的左手腕,如若是往常,她会挣一挣,可如今扮作哑女,自然应该唯唯诺诺,不能轻举妄动。她僵在原处。
“启禀陛下……宋医女她听不见。”玉德连忙再提醒一次。
“让朕看看你。”九五至尊,说出这话时满腔皆是请求。
她心中五味杂陈,却依旧一动不动。
皇帝阔步走到她跟前,咫尺的距离,他俯下身子,双目炯炯盯在她的眼睛之上,骨节分明的一只手缓缓抬起来,指腹轻柔地在她额间那朵彼岸花上摩挲。
“这又是什么?”皇帝问。
“启禀陛下……此乃黄泉之花曼珠沙华。”玉德环顾四周后,硬着头皮回答。
皇帝深不见底的眸子半垂,冷声道:“滚!”
玉德再次环顾四周,让侍卫们先退下,自己也灰溜溜避往一旁。
周遭忽然安静下来,只听见呼啸的北风吹得两人衣袍猎猎作响。
皇帝的手已经落在她的面纱一角上,她闭上了眼睛,倘若面纱掉落,他知道她未死,会否大发雷霆呢?她忽然也想知道。
可是师父又该如何?窝藏囚犯的罪名可不小。届时她一定会咬死说是自己胁迫郁大人,将他撇清得一干二净。
那只手却停在了面纱外,她耳根处,那温暖的指腹只触摸到她的耳根,淡淡的龙涎香气透过面纱传入鼻中,她摒住呼吸,生怕会情不自禁去深吸一口气。
皇帝的目光似浸满氤氲,顷刻间,却已又是一渊深不见底的寒潭:“是朕认错人了。你走吧。”
反倒是她愣了,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以为必死无疑,可是却轻而易举便逃开了。是应该暗自庆幸的吧,可是为何她心里似被掏空了,无比怅然呢?
“陛下……”莺声燕语,又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石阶门口传来。
她垂着目,并不想去看。可是几声奶娃的哭声,倒是勾起她的兴致。
良贤妃怀里抱着的婴儿,刚过半岁,正是当朝第一位公主。沈牧迟的长女。
“城楼上风大,抱她上来做甚?”皇帝负手而立。
玉德见良贤妃上来了,宋医女却赖着不走,连忙上前来赶人。
“陛下有所不知,沧凌哭个不停,应是想念父皇了。”她怀中的婴孩,果真朝着皇帝的方向挣了挣,一双小小的藕臂努力伸向皇帝,小嘴瘪着,不住抽泣。
采苓刚走了两步,忽顿住步子。原来他的孩子叫沈沧凌,真是个好名字。
“过来吧。让父皇抱抱。”皇帝的声音极为温和。
“您嘞,快走吧。别仗着自己又聋又哑就在此以下犯上。”玉德连忙给她指路。
采苓游走回了太医局的内院,见郁墨言和小川正坐在大堂内吃饭。她安静地走到平时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小川连忙给她夹了块肉:“姑姑,我爹有点生气。”
她吐了吐舌头,确定四下无人后,凑到小川耳旁:“我知道。”
全程无话,连小川都觉得气氛不好,只乖乖扒完了饭到屋外玩耍。
采苓收拾完餐具,试探性问:“师父。您要喝普洱还是龙井?”郁墨言没有理她,起身往前殿而去。
次日,郁墨言将人体解剖课提前,采苓一点心理建设没有,跟在韩医正身后唯唯诺诺。屋子外却围了许多学徒和医女,统统巴望着能进去大开眼界。
刚步入屋中,便感到一阵肃杀的凉意迎面袭来。一具微胖的妇人尸体挺直地躺在案板上,一袭月白长衫面无表情的郁墨言,就负手站在尸体的一侧。唯一庆幸的是尸体的面容被一张白色的绢布遮住了。
“我嘞个去!”韩医正也打了个寒噤,自语道:“虽是罪妇却也下不去手啊。还是让这丫头划第一刀吧。”
采苓站在他身后,故意踩住他的靴子,他一个趔趄,差点跌进尸体的怀抱,被吓得当即哇哇大叫。直到郁墨言冷冷瞥他一眼,才站直身体,摆出一派虚心求教的模样。
“小韩你划开胸口,让宋儿划开腹部。”郁墨言指了指两处位置。
韩医正用唇语跟采苓解释了一番,她两只手不断发抖,只敷衍地点了点头。
一切都是血淋淋的,即便是许久后想起来,也会浑身不舒服,可是师父却说他十岁便见惯了人的身体构造。她感觉自己对师父的崇拜又增加了无数多。
可是这次解剖却让她清楚认识到胞宫和其它妇人器官,这些都是书册上画不出来的。学习结束后,郁墨言又让他们将各个器官缝回原位,连胸口和腹部上的开口都小心翼翼缝了,三人对尸体鞠了躬,才先后步出小屋。
围在屋外的人群立即将韩医正包围住,纷纷询问解剖的经过,采苓只觉头昏目眩很不舒服,可看韩医正却意气风发、滔滔不绝与人讲着,仿佛这次经历多么值得炫耀。转过头去,见郁墨言也看着韩医正,嘴角勾着一抹欣赏的笑容。她有些沮丧。不对比还好,如此看来,谁是学医的谁是来混日子的一目了然。
中午,韩医正端了碟菜到后院来,她一点也没食欲,所以连面纱也没取下来,就静静坐在案子前。韩医正将那碟菜凑到她面前:“宋儿,来尝尝这碗猪大肠。”
脑海中顷刻间满是卷成一团血淋淋的肠子,她冲出屋外,蹲在檐下,胃里翻江倒海,连连吐着。
屋内,韩医正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郁大人,下官可不是故意的。”说完后,搁下猪大肠又来给采苓顺背,窃笑道,“看你今后还敢不敢绊我。”
她很沮丧,并非是被韩医正给摆了一道,更多的是郁墨言居然没来关怀几句。
别人学艺困惑时,师父总会语气温和地谆谆善诱:别灰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她的师父还是不理她,甚至没抬眼看她一下。
傍晚时分,下起了小雨,她裹着被子蹲在屋子里背《黄帝内经》,膳房的阿嬷来敲门, 连说带比划,意思是她养在的膳房后院里的羊快生了,胎水流出,小羊却久久无法娩出。
她速速跑去羊圈,见母羊拱腰伸腿,不时痛苦哀叫。她伸手探入产道,只摸到小羊的屁股,无法将其拉出,正不知如何是好,郁墨言拿着医药箱就站在跟前,他递给她用于麻醉的曼陀罗草,一把小刀和剪刀。
母羊的剖腹产很成功。看着小羊从胎膜里挣出来,伸了伸腿,睁开眼睛,她忽然开心到留下泪来,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让她在羊圈里不住蹦跶,吓得旁边圈里的小羊们嗷嗷直叫。
“师父。多谢你教我医术。”两人并行穿过大殿后的庭院,她附在他的耳旁低声道。
他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提着木制的药箱,低垂眼睫来看她。她连忙乖巧地双手接过药箱,抱在怀中,“伞还是您自己撑着吧,我够不着。”
他空出一只手,刚好能将她往伞下一带,她便稳稳当当靠在他的肩头,他唇角勾起一抹笑,语气极为温和:“是你天资聪颖。”
师父终于肯搭理我了,师父还夸我天资聪颖呢?
她心道。面纱下的小脸上早就开出了一朵花,眉眼弯弯似今夜的月牙,举头望着郁墨言:“师父,我答应你,从今往后再不会偷跑出去。”
“嗯。”郁墨言垂下眼来深深看着她。
又过了两日,垂拱殿的小太监匆匆来请太医,说陛下抱病不起。
韩医正多问了几句,小太监道:“前日落雨起风的天气,陛下站在雨花阁顶久久不愿下来,怕是那时候染了风寒。”
采苓正在分拣药物,忽顿住,小太监看了她一眼,试探性问韩医正:“这位宋医女不是哑女么?如何像是能听见咱们说话似的。”
“公公多虑了。”韩医正连忙道,“我这就去通知郁大人。”
采苓再无心拣药材,站起身朝门口走去,却不小心撞在桌案的一角上,力道有些大,榆木的大桌案抖了几抖,她却一声未吭,甚至没有看一眼受伤的大腿,只默默离开。
“啧啧……果真是名哑女。”公公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