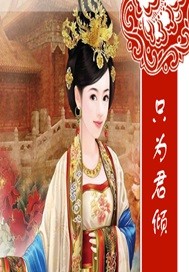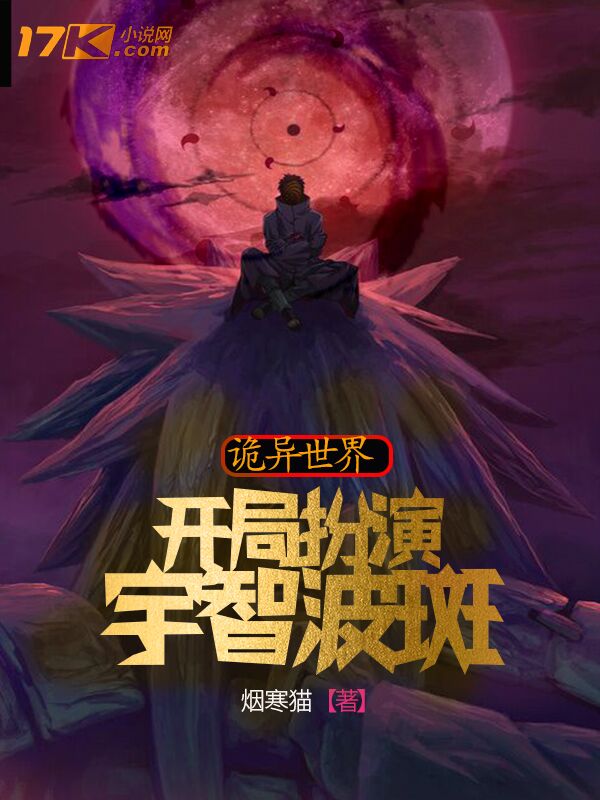仿佛是一晃之间,春去秋来,冬去春又回,一载的时光匆匆流过。
太医局外殿院子里一颗百年的梨树开满了雪白的花,微风过处,花瓣纷纷扬扬散落。
梨花树下,一张竹几并数条小凳,两名宫女并排坐在竹几对面,正等着宋医女开方子。
宫女甲盯着周身雪白的宋医女一撇一捺正写字,忽打了个哈欠,转目四看后,对身旁之人道:“自陛下一月前去了云南,垂拱殿内也安静得很,正好得空来瞧瞧这顽疾。”
“姐姐在万岁跟前伺候,可知晓万岁为何要突然离宫去云南?”宫女乙瞧了一眼宋医女后才笑道:“姐姐别担心,宋医女虽是太医令大人的首席爱徒,却是个又聋又哑之人,所以她才会只用纸笔同咱们交谈。”
“听说是为了那位姑姑。”
“那位姑姑?无诏不得回京的那位吗?听说是患了重病。”
“本来陛下是要将其接回的,可是滇王殿下加急送了折子,称几经调查,才知那人并非原来那人。”
“不是那位姑姑吗,又是何人呢? 当初可是刑部侍郎亲自押解的犯人。”
宫女甲环顾四周,又对正抬头思索的宋医女报以礼貌性的一笑,才凑到宫女乙的耳畔道:“正是掖庭宫的珩儿。听说此事与魏美人脱不了干系。”
“魏美人吗?倒是个可怜人,如今碧霄宫内之人个个发着疹子,听说周身奇痒无比,宫女淞荷上月不忍其苦自缢而亡呢。嫔妃自缢那是关系到举族性命之事,魏美人自是再大的痛苦也只能干忍着。若是真有干系倒是个好事,总算是能让她得个解脱吧。”
“倒是没错,碧霄宫如今可真是比冷宫还阴冷,连打更的都要绕着走呢。”
“不过姐姐,既然万岁已经知晓云南的并非那位姑姑,为何还要亲自去一趟呢?”
“谁知道呢。或许是谁说的都不信,非得自己走一趟亲自瞧瞧吧。”宫女甲接过宋医女递过来的药方,满面笑意的点头,又道:“不过,这宋医女虽蒙着面纱,仔细瞧着倒有几分那位姑姑的轮廓呢。”
“姐姐怕是眼花了,那位姑姑皮肤白皙性子又活泼,与宋医女的沉静可是天壤之别,听说姜医女满面的红斑,所以才会蒙着面呢。不过,她额间的这胎记倒是别致,像是一朵花。”
“曼珠沙华……”两人异口同声。
“对,就是黄泉之花。”宫女甲补充道,“妙法莲华经上有此花的注解,听说意味着生死两隔,永不相见。到底是个不祥之兆,难怪会成日蒙着面。”
“谁说不是呢。”宫女乙一边说一边朝宋医女露出笑容,将手腕放在她的手指之下。
宫女们离开后,自有人端来一盏新茶,打着哑语道:“医女请休息片刻。”
她露出笑颜,搬了把小凳坐在太医局门口等人。
太阳西斜之时,那人才从殿门口跨步进来,她连忙站起身,拉着他的袖子,笑意盈满双目。
“不去仔细研读医书,守在此处做甚?”郁墨言垂眼看着她,又让随行的医正先离开。
隔了片刻,那薄纱之后的嘴唇快速翻动,却是压低了声音:“今日可算是憋死我啦。”
原来如今的宋医女便是当初的姜采苓。
“师父可知晓碧霄宫之事?”
“嗯。”郁墨言唇角轻轻勾起,“怎样?师父没骗你吧。动不动就杀人那多粗俗啊,这世间自有让人生不如死之法。”
“哦。”采苓点头,将郁墨言拽到内院,环顾四周确定无人后又问:“珩儿为何也死了呢?难道师父还有千里投毒的本事?”
“珩儿?”郁墨言眉毛一抬,“何人?为师不认识。”
“哦。那应该是她命不好。”采苓撇了撇嘴,“师父是去给太皇太后瞧平安脉了吧。她老人家一切都好吗?”
“脉象虚浮,仍需调整饮食。”郁墨言回答,片刻后已是半眯着眼睛看她:“《神农本草经》背熟了吗?才刚学了点皮毛竟敢给人看诊了。”
“师父有所不知,徒儿专功妇人之症,只需了解胞宫,熟背《妇人婴儿方》和《千金药方》便可,不必背完《神农本草经》。”
“胡言乱语。知道何为‘有毒无毒,斟酌其宜’吗?”
采苓答不上来。
“‘七情和合’又是什么?”
“七情六欲都要合在一起?”采苓想了一想,勉强回答。
郁墨言被她气笑了, 戳着她的额头道:“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
“原来如此啊。”她连忙附和道。
“真的理解了吗?那你说说看到底是何意?”郁墨言一脸的严肃。
采苓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墨言道:“背不了《神农百草经》今晚别吃饭了。”
“是。师父。”她垂头丧气走了。
回屋后对着典籍挑灯夜战,过了亥时才将之背完。
她欢喜地敲开郁墨言的房门:“师父,原来“有毒无毒,斟酌其宜”的意思是有毒之药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其毒性之大小也能斟酌用药,而‘七情和合’指的是药物配伍的关系,比如两味或者两味以上的药配在一个方子中,相互之间会产生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反应。”
郁墨言仔细听着,慢慢露出欣赏之色,又问:“那么应该如何配药呢?”
“此七情,应该合而视之。单行的,不用臣佐之药。相须相使者能用,相恶相反者勿用,如果要减轻某种药的毒性,可酌情用相畏相杀的。”
“相恶之药可知晓?”郁墨言又问。
“元参恶干姜,巴戟恶雷丸,狗脊恶败酱。”采苓信心十足。
“很好。孺子可教也。”郁墨言俊朗的脸上挂着春风般和煦的笑容。
“师父,夜深了。您这是要去哪儿?”采苓问。
“你肚子咕咕叫了。为师去给你端包子来。”郁墨言快步消失在长廊的尽头。
采苓抱膝坐在檐下,望着夜空中一伦圆饼似的明月,露出久违的笑容。
早前两位宫女的言谈不经意间又来扰乱了平静的思绪,让她倏忽一下便想到了滇王。
是两月前的除夕,太医局里的医官们早早归了乡,偌大的殿宇中除了郁墨言和她便只有几位家住长安的医正。
午后,郁墨言应邀出席宫内的庆祝活动,她百无聊赖下,便戴好了面纱到前厅去与韩医正下棋。
赢了两局,第三局时她去倒了杯茶,再回来瞧见棋局有变。
她深知是韩医正输不起背着她调整了棋局,她很想嚷他两句,可是如今扮着哑女,到底不敢轻举妄动,只暗自下定决心就算是一局死棋,她也要想尽办法让它起死回生。
滇王独自进入主殿内,两人都紧紧盯着棋盘,未注意到有人闯入。
直到她走了一步妙棋,滇王拍手道:“好!”
两人错愕地抬起头来,见到穿着朝服的锦衣王爷正注视着棋盘,笑道:“你们继续啊。”
“参见殿下。”韩医正已机敏的单膝跪地拱手行礼。
她却当场愣住,直到韩医正替她解释:“这位是太医令郁大人的徒弟,自幼跟在郁大人身边,大人进宫后念其孤苦无依,又是聋哑之人便将她也带进宫。她脑子不太好,失了礼数,请殿下恕罪。”情急之下,他朝采苓使了个眼色。
你脑子才不好!采苓心道,却是屈膝行礼如仪。
“都起来吧。”滇王笑道,“宴席之中,本王忽觉头晕,又怕传太医惊扰了太皇太后,便到此处来走一趟。”
“下官这就为殿下把脉。”韩医正连忙摆出一副专业的姿态。
滇**炯的目光却只留在她身上:“既是郁墨言的爱徒,自得了几分她师父的真传。就让她提本王看看吧。”滇王如是回复韩医正。
“可是……”韩医正欲言又止。
“有何可是?”滇王有些不耐。
“殿下有所不知,这宋医女只能看……妇人之症。”韩医正嗫嚅。
“无妨。”滇往倒是笑了,“本王的身体与妇人也无多大的区别。”
韩医正抚着胸口,差点喷出一口血来。
采苓躲在面纱之下,也是稳了许久才保持住不笑。
韩医正无奈之下又给她使了个眼色,正此时,滇王已经挽起袖子,将光洁的手腕放在她跟前桌案上。
她悄悄按了按微微颤抖的一只手,才将之抬起来,手指轻柔地覆在他脉搏跳动的地方,她虽紧紧盯着他的手腕,眼角余光却能清晰看见他的目光是一刻也没离开过她,情急之下,她忍不住咳了一声,瞥眼看他,剑眉星目,目光炯炯。
她连忙瞥过眼来,这时候,他也将目光移向她的手指,看了片刻。
她感觉手抖个不停,连忙停了诊脉,拿过纸笔正要胡乱开个强身健体的方子。
“哈哈哈……”滇王朗声道:“本王出来走了一趟,忽觉头清目明,不治而愈了。”
说罢,起身便走,她还来不及反应,他便只给她留了个清俊的背影。
当初不敢相认,连半个字也未说。
今夜月华如练,满目星辰,她抱膝坐在一地清冷里,举头轻声道:“王爷。多谢你……”
千里之外,云南滇王府内,春风拂面,桃花杏花开了满树。
“皇叔恐怕早就知晓此人并非是她,竟瞒到最后?”主位上,皇帝眼神冰冷。
“当初可是刑部侍郎亲自押解的人,连陛下的心腹都看不出来,臣愚昧,自然也被蒙在了鼓里。”滇王悠闲地喝了口茶。
皇帝薄唇轻轻勾起,笑意却不抵眼中:“明明一开始就知道,偏偏等了一年。皇叔留给她的时间果然充分,如今即便是朕布下天罗地网怕是也难将之找到。”
“原来陛下也明白事到如今已是一年的光阴。”滇王收起笑容,“一年之中,陛下可来过一封书函?千秋节、太皇太后的寿辰、中秋、除夕,陛下可有过半点赦免她的意思? 若非听说人病重将死,陛下还会想起这世间还有一个她吗?”
大殿之中,两人剑拔弩张,两两向望,静默无声。
片刻后,皇帝问:“皇叔可知她如今身在何处?”
“臣不知。”
“皇叔竟决意至此?”皇帝面色一凛。
“臣犹记得几年前东喜楼中,圆嘟嘟的女孩子手持一把折扇,坐在小桌边,听曲子吃花生米,一杯接一杯饮酒。臣问她身为女子为何不守妇道要当众醉酒,她拍了拍桌案,朗声道:喝不喝?要喝就坐下,不喝就请便。”
“这样的人,陛下让她委身为奴,向嫔妃们端茶送水,磕头如仪,陛下可曾心疼过她半分?”
皇帝双眉蹙在一处,久久不语。
滇王劝道:“放她走吧。她那样的人应该策马红尘里,本就不属于深宫之中。”
皇帝冷然瞧了他片刻,倏得起身,从其身旁掠过,只留下一句:“朕绝不会放手。”
许多日后,未央宫中,又有一批宫女到岁数了,将会被放出去。
采苓穿了浅蓝的襦裙,以同色面纱覆面,一年以来首次踏出了太医局的殿门。
郁墨言去紫微宫陪太皇太后下棋,一个时辰内是不会回来的,她便寻得机会偷偷跑出去。
因为前几日她无意间得知,浣衣局的吴姑姑也将在今日被放出宫去,她只想悄悄去掖庭看她最后一眼。
那一日晴朗无云,杏花露在宫墙之外,桃花开了满树,承影湖中偶见白鹭低飞,各种熟悉的景致许久不曾见过,倒是有些想念,她又贪心地在亭子里坐了一会儿,直到无意间想到了碧落,而如今的自己在沈牧迟的心中恐怕还不如碧落,心情忽然很低落,便只垂着头朝掖庭宫行去。
她躲在浣衣局内晾晒的层层衣物后,见到拿着小包袱的吴姑姑正与众人道别。
吴姑姑虽然已过二十六岁,却还是身姿绰约,面容娇美,即便是在长安城中也能嫁入积善之家从此相夫教子吧。
她目光一转,瞧了眼水池边那块大石头,曾经两人都爱坐在上面。吴姑姑说:“色衰而爱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她埋头轻笑,就算命苦如吴姑姑至少还有滇王倾心以待。
而她虚活了二十年,深爱之人即是要杀她之人,又有什么资格来怜悯别人呢。
此生还很长,只愿吴姑姑从此安稳无忧。
却不知,便是在这草长莺飞的春日,在那高高的城楼之上,那人站在身后,冷声问她:“你是何人?”
一年之后,得以再次见到沈牧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