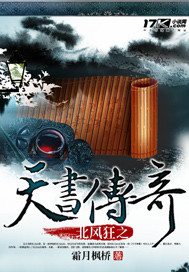次日醒来,已是天光大亮。采苓做内廷女官的时日虽然不长,当值时一定是寅时末起身,赶在卯时伺候陛下更衣,今日却是个例外。
玉安在外间小声问云鹤,“是否呈报彤史女官记录在册。”云鹤应允。
采苓睁开双眼望着满目的水色幔帐,彤史女官掌记宫闱起居及内庭燕褻之事,从今往后她便是沈牧迟名正言顺的……姬妾,史册上一名被他偶然临幸的宫人,或许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出现在史书上,除非生下皇子后母凭子贵。
昨夜与他靠得那样近,仿佛是情深甚笃,可是双方都在置气,更多的是怒目以对,并不完美。
去年八月就在心中反复酝酿的一件事,忽然水到渠成变成了现实,却仿佛是在梦中。她狠狠掐了自己的大腿,果然是疼,还好不是一场梦。
起床时,见水色床单上沈牧迟躺过的地方有一抹鲜红,她惊恐地检查一遍,月事并为至,忽然想起成婚前两日,阿娘专程找了位老嬷嬷来教,说女子初夜落红,良人尤爱之,洞房花烛夜的喜床上也会铺上落红帕,以备长辈检查。
她的洞房花烛夜是在天牢里度过的;她的“喜床”没有花生、红枣,是一串的水色,更没有什么素白的落红帕。
穿戴整齐后,她从里间的柜子里拿出另一套水色的被套床单,快速地将染了血的给换掉,丢在一旁,若是能洗掉最好,洗不掉就只能扔了。
这便是她的初夜,与旁人的多有不同,更比不上良明月的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可是她有什么可计较的,去年九月初三就将自己嫁了出去,纵使来拜堂的只是一缕空气,她也不可能再二嫁一次。世间之事变幻莫测,有多少能遂心愿,又有多少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可沈牧迟却反而少了她的这份恣意洒脱。午膳时分仍不见其回内殿,采苓守着满桌的饭菜,等了一柱香的时间,玉安匆匆来报:陛下独自一人留在垂拱外殿,不思饮食。
采苓将饭菜装入食盒中,自家的“小娘子“还是需要自己来哄的。
翩然行至垂拱外殿,见一众宫女侍立在廊上,玉德守在殿门口,见了她来,连忙招呼,“陛下吩咐谁都不能前去打扰。”
采苓扬声道:“那我就先走了。”
玉德一个噤声的手势还来不及做出,皇上浑厚的声音自殿内响起:“小四……”
玉德一惊,让出道来,采苓提着食盒趾高气扬从玉德身边走过,他连忙帮着推开了殿门。
本端坐于帝坐上的沈牧迟忽然站起身来,表情复杂,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渊儿无意打破她的青花瓷瓶时便是这样的表情,她怜爱尚且来不及,怎会怪他?
“这些都是陛下爱吃的菜,趁热吃吧。“跪坐在他身前,将一碟碟佳肴摆在他面前的小案上,微笑着看他一眼。
“朕昨日多喝了两杯,听信谗言,伤害了你,你可还怪朕?“沈牧迟问。
“听信谗言?“他如此快就将事实调查清楚了?
“浣衣局的吴监作今日一大早就跪在垂拱殿外。“他扬了扬眉,似揶揄,”洒扫太监也回禀说在小山后面发现了一地的瓜子壳。“
她将鳜鱼烩往他手边推了一推,“既然查明了真相为何还是不高兴?”
“朕昨日对你……太粗鲁了些。”目光刚触及她的裙摆,红霞登时染上面颊,他埋着头扒了一口饭,不敢抬起眼睛看她。
她噗嗤一笑,片刻后,拉着他的衣袖:“奴婢有个请求。”
他怔怔看一眼衣袖,又连忙抬头看着她的眼睛,期待她继续说的话。
采苓微微一笑:“彤史女官那里,可不可以不要记录?”
皇上举筷的一只手半悬在空中,原本闪着星辰的眸子慢慢黯淡无光。
“都依你。”片刻后,才冷声道。
正此时,殿门再次被推开,玉德匆匆禀奏:“太皇太后忽然晕厥,恐病危。“
话音未落,沈牧迟已经大步流星朝着紫微宫的方向疾走。
紫微宫寝殿内,鹤发白须的太医刚为老祖宗诊治完,支支吾吾只说情况不容小觑,万幸下醒来也会留下病根,届时更是难以根除。
采苓心中七上八下,抬眼看着沈牧迟,他平静如常的脸上隐现焦虑,问老太医是否有所隐瞒,老太医才道,普天之下唯有一人能医治此症,可他常年隐居,恐怕无从寻找。
“可知姓名?“沈牧迟问。
“郁墨言。”老太医拱手道。
天下名医竟然和隐世画仙同名同姓,采苓正侧耳倾听。良贤妃行至跟前,将她拉至一旁,问:“苓姐姐可知太皇太后她老人家为何忽然晕厥?”
采苓摇了摇头,良贤妃道: “正是滇王的侧妃向太皇太后告密说姐姐昨日私会滇王。那名叫“小虫子“的王妃看起来虽单纯无害,却是阴险之人,姐姐要多加提防。”
“多谢娘娘提醒。“采苓点头。她想过琮知会告密,没料到的是太皇太后会因此事气到晕厥,这可如何是好?好不容易才让她老人家喝了一杯赔罪的茶,如今又是功亏一篑。采苓即懊恼又内疚。
“你先回吧。“陛下吩咐,她又如何能留,如果太皇太后醒来瞧见了她保不准又会气到再晕一次,还是先走为妙。
“陛下不必太担忧。臣妾会守在太皇太后床前半步不离的。”良贤妃走到陛下跟前,极是乖巧。
“嗯。”陛下回答。
采苓这时刚跨过寝殿的门槛,初冬的日头温和,她却觉得尤是刺眼。
采苓绕道去了掖庭,还是坐在那块大石头上,让了一半的位置给吴姑姑,看着宫女们忙前忙后,正在浆洗的绛紫色衣裙,质地精良与旁的多有不同,一看便是良惠妃的新装。
她抬眼瞧过去,看宫女悉心地浆洗完再一遍一遍过清水,似乎很认真地盯着却是目光空洞。
“昨夜受苦了?”吴姑姑忽然问。
“我能受什么苦。”她扬眉轻笑,“倒是你跪在殿外到底几个时辰?膝盖可可还无碍?”
“无妨。”吴姑姑轻轻移了移腿,避开她的视线。
她便继续看向前方,“是否怪我多事?”昨夜滇王往后走时撞见还留于亭中的吴姑姑,追问之下,只好将此事叙述给她听,姑姑便连夜跪在垂拱殿外,此番情谊,让采苓很是内疚。
“你一心为我,我又如何会怪你。”极为真诚的言语,“况且一早我便猜到了你的目的,一心前往也是要遂了自己的心愿。”
“那就再多嘴问一句,你同殿下到底如何?”她自察多事,禁不住笑了。
吴姑姑也将目光瞧向远方,微不可察叹了口气,缓缓道:“我只祝贺他佳偶天成。“
“殿下就丝毫未表明心意?“采苓连忙追问,十八位侍妾伴在身侧的人怎会忽然成了不开窍的木头?
“他问:将来可有何打算,不如……”采苓听得正起劲,“话音刚到这儿,我便打断了他,说待明年放出宫去,洛阳有位表哥还在等着。”
“洛阳的表哥?”
吴姑姑释怀一笑,“自然是骗他的。”
“姑姑何必如此?”采苓气急。
此后,她听到了一席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却又似醍醐灌顶的话。余下的许多年里,偶然还是会想起,总是似一团消不散的阴云笼罩在头顶。
“我明年就二十六了,最好的年华皆留在了这深深的内廷。许多年来,我不知长安城有什么变化,更不知道宫外的生活是怎样的,伺候过的男子唯独滇王一人,不谙男女相处之事。“
“虽一心只在他身上,可色衰而爱驰,比不过年轻貌美的,更不知该如何同他的姬妾们相处。他既开口问了一句’将来有何打算,不如‘这就够了。我既不敢抛开所有跟随在他身边,又何必非要听到那些蜜语。“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如若再年轻五岁,估计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不如’后面是什么不听也罢。”
宫女们此时已经洗好了衣衫,五颜六色的锦衣挂在一根根竹竿上,随着初冬的微风徐徐摆动。采苓目光投在一众彩衣上,忽觉天旋地转,垂下眼来问:“放出宫后可还会想着嫁人?”
“运气好遇到合适的自然会嫁,遇不到也就算了。“吴姑姑故作轻松,拍了拍采苓腿,”你又如何?“
采苓并未立即回答,起身穿过池畔绚丽的彩衣,朝着浣衣局的院门而去,清冷的声音从远方传回来:“你一定不会嫁的!“
相遇、相知、相爱都在最美的年华里,又如何再倾心于他人?即便运气好也不过是将就一场。老天让你碰见这世间最好的男儿,却只给了个情深缘浅,清深永远藏在心间,缘浅就让余生来弥补。
太皇太后在昏迷两日后终于转醒,滇王回藩,皇上也恢复了早朝,一切都仿佛回到了从前。
采苓依旧尽心伺候于帝前,只是皇上已渐渐同她疏远,凡是在紫微宫用膳皆是由云鹤亲自伺候饮食。
而良贤妃依旧是深得帝宠,许多晚上陛下皆留宿于长乐殿,听闻良贤妃近来越发肤若凝脂、明目善睐,不过这些采苓都看不见,陛下免了她早朝前的更衣之职,另换了他人。
懿旨是今晨收到的,虽只是口谕,春姑姑一字一句却似印在她的心间。
“老祖宗只怪你太随心所欲,不是真的厌你。此番出宫,一定要将功补罪,将来时日还长。“
出宫寻名医郁墨言,如此重要的工作不派给高手如云的兵部,也不派给消息灵通的廷尉局,怎么就交给了她?
正百思不解,一筹莫展之时,春姑姑提醒:”提防身边小人。“
更是令她一头的雾水,便索性不再去想。
听闻郁墨言隐居于南北两国边境旁的山林间,此去千里,食宿全包,正是欣赏大好河山的良好时机。
她又何乐而不为。
是夜,小屋内,她正在紧张地收拾着小包袱。
听闻北国是冰封之地,多带几件厚衫准不会错,幸好漫云新做了两件冬袄,她善女红,绣的两朵蔷薇两只蝴蝶栩栩如生,一只手刚抚过衣领,心中就有了主意,连忙将其放下,转身要出门。
小门被人嘎吱推开,皇帝就站在跟前。
“陛下为何在此?奴婢正要去找您。”她转忧为喜。
“在收拾行装?”本面带薄怒的皇帝见了她已是极力克制,“果真是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采苓心存疑问,迫不及待的应该是他们沈家人,她虽也担心着太后,但是还不至于迫不及待,“陛下前来就是要数落奴婢?”
“朕……”竟被她一句话噎住。
“陛下,奴婢明早就要出行,此去千里也不知几时能归,你非要这样怒目相对、没有一句好话吗?”她叹了一口气,将他让进屋来,已是态度很好。
“小四……“他忽然长臂一揽,将她紧紧拥住,然后埋下头来,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之上,颓然极了,“莫不说是永州,即便是你逃去天涯海角,朕也能将你找到。”
“逃去天涯海角做什么?那里是有金银珠宝还是美酒佳肴?”采苓垂在身侧的双臂也抬起来,放在他结实的腰背上。
自年初入宫,便同住在这深深的宫廷中,此去经年,许久不能再见面,难免不舍。
“竟还有心思说笑。“他半是责备半是揶揄,一把将她拦腰抱起,走到小床前。
她忽然脸红,连忙挣脱,密密匝匝的吻已落在脸上,脖间,”小四……别推开朕。“
窗外忽然下起了绵绵细雨,帐内两抹身影合二为一。
“陛下今夜要睡在这里?”许久后,采苓推推身边的人。
“有何不可?”慵懒的语气,一双手将她搂得更紧。
“到底有失身份。“采苓怯怯提醒。
“整个未央都是朕的,朕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他翻身向外。
“那明日睡睡掖庭宫如何?“她忽然想到浣衣局里不避风雨的茅草房,忍住未笑。
“你……”忍住薄怒,“休再气朕。”
“那奴婢求陛下一件事,可好?“她顺势问。
“说来听听。”已清醒大半。
“明日出宫,求陛下恩准让漫云也同行。”
片刻无言,采苓心中忐忑不定,正要再求,皇帝缓缓道:“朕正有此意。”
“谢陛下。”她连忙要起身行礼,他长臂一伸将之按倒,“早些睡吧。”
可是睡至半夜,他还是起身离开,垂拱殿的灯光骤然大亮,云鹤已经指派了另外的女官从此伺候他起居。她翻身向内,却久久无法入眠,只以为是为明日出宫之事欣喜难耐。
次日清晨,两辆车與停在安德门外,采苓与漫云拿着小包袱快步走近时,见到从马车前闪身而出的陶陶,其喜不自禁,一把接过采苓手中衣物:“怎就带了这些?无妨!待抵达永州,本少给你买裘皮。”
怎么?前几日还穷苦潦倒,现在又富裕了,朝廷分配给此行的预算到底多少?来不及问,萋萋温婉招呼她:“苓姐姐。“
原来杨家兄妹也同行,果真是好,她虽是为了赎罪,杨家兄妹却是为了立功,若是成功迎回郁墨言,萋萋封后的路途就更加坦荡了吧?而陶陶,和平年代,也没有战功可立,若是此行顺利也能授封为正五品的定远将军吧?
采苓心中稍安,毕竟有杨家兄妹在,此行的凶险系数直线下降,遂展露笑颜,跨步要上车。
“姑姑等等……“回眸处,玉安公公匆匆奔至。
心潮难免起伏,她只极力克制着,待到玉安走近,才问:“有圣旨?“
玉安踟蹰半刻,“陛下让贤妃娘娘前来相送,娘娘步撵缓,让洒家先来同姑姑通报一声。“
御前太监玉安如今也得听命于良贤妃,果真是恩宠有佳。陶陶上前一步正要说点什么,采苓将他一把拉回,两人斜靠在车辕处,等了两柱香的时间。
步撵珊珊来迟,撵上身着华服的女子连声催促,宫人们跑得满头大汗,摇摇晃晃跪伏在宫道上,玉安亲自前去将之扶下来。
“奴婢(臣、臣女)参见贤妃娘娘。”众人免不了要行礼。
“姐姐快快请起。”贤妃笑容如和煦的春风,一把将采苓扶起,“此去千里,北国冬日天寒地冻,妹妹特意给姐姐带了件玄狐裘衣,希望姐姐别嫌弃。”
语罢,自有宫女捧着件红狐狸毛的大氅前来,嘴里嘀咕:“这可以陛下新赏给娘娘的。”
“休的多嘴。”明月轻叱。
陶陶走近,又要打抱不平,采苓将其一把拉回,双手去接盛大氅的托盘,“多谢娘娘。“再次屈膝行礼。
贤妃来这一趟,他们见时行礼,临别时还要行礼,陶陶只拱手作揖已面色难看,采苓一双腿微曲数次却仍是笑容不减。
“本少如今才知,你在内廷里过得也不好。“起行的马车内,陶陶忍不住抱怨。
“笑话!本少官品比你还大两阶,不知多逍遥自在。”采苓不以为意。
“是!姜大人!”陶陶连忙拱手作揖,良久后盯着目光瞧向窗外的采苓,“那良贤妃额上的花钿别致精巧,本少总觉得似在哪里见过。”
“鱼膘贴的翠钿。”采苓打帘继续瞧着繁华的长安城,“本少贴过半年,后来跟风的人渐多,便弃了。再说,实是罪过,不知伤了多少翠鸟。”
“这裘氅又如何?”陶陶厌弃地瞥一眼一旁的红狐裘皮。
“留着。”采苓淡淡一笑,“北国冰封,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