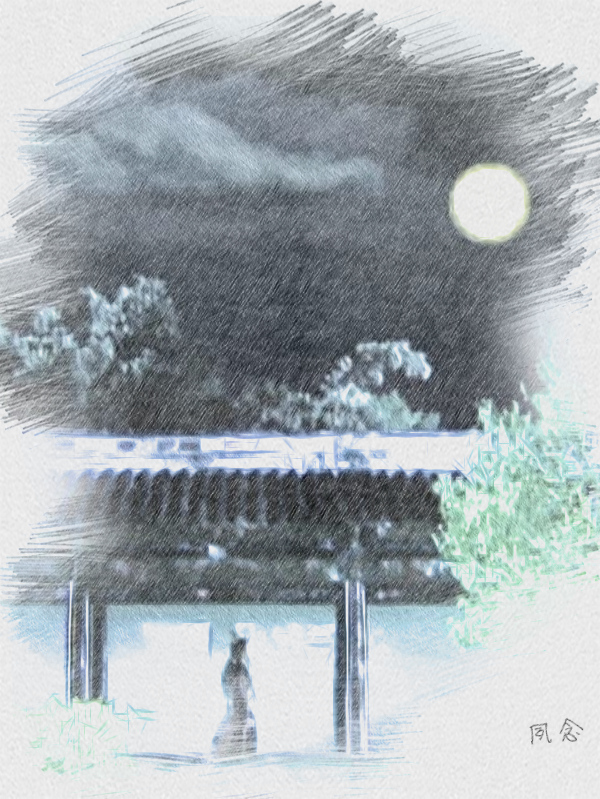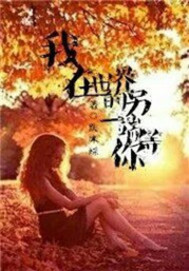池畔另一处较敞亮的屋子里,漫云跪在地上,采苓站在她身边,其余人皆怒气冲冲瞪着她们。
“漫云。你动不动出手伤人,莽撞至此,你可知罪?”吴姑姑厉喝。
“是她俩犯错在先。”漫云极力解释。
“我们不过是不小心撞翻了晾衣杆,正要去扶,漫云就怒不可遏像要杀了我们似的。太可怕!掖庭里有这样的人,姐妹们如何能安心哇。”珞雪如泣如诉。
“明明是你们先伤人。”漫云争辩。
“不要吵!”吴姑姑低喝一声,“姜采苓,你也是当事人,还不快快说出事情始末?”
采苓站在原处,身子一僵,漫云当初在秦王府被碧落找麻烦,打得皮开肉绽未吭一声隐藏得极好,如今不过是道行尚浅的两名丫头就让她爆怒至此,果真是关心则乱。
“是我出钱让漫云收拾这两名贱婢。”采苓昂首道,“谁让她们故意撞翻了晾衣杆。”
“姐姐!”漫云双目圆瞪,不可置信。
“漫云,我如今也没多余的银子,你还是离我远点比较好。”采苓恳求。
“大胆。竟然仗着有几个钱就胡作非为。”吴姑姑怒不可遏,“姜采苓将所有衣物再洗一遍,漫云罚跪一晚,明日搬去东屋,你两个从此不准相见。”
漫云已是满眼泪光,抱着采苓的腿不肯放手。采苓狠心踹了她一脚,头也没回前去涣衣池。如今她站在风口浪尖上,多少人盼着她坠入深渊,她可不想拉漫云来垫背。既然保护不了的人,离得远远的,反倒是好。
浣衣,晾晒,换两个池子的水,事情好不容易做完,天已经微微露白,漫云所在的那间小屋还燃着微弱的烛火,她遥遥看了一眼,在袍衫上擦干泡到发白的双手,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小破屋躺下。多多少少睡一个时辰,也好。
床板很硬,月光从破了许多洞的窗户纸里透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翻身朝屋内,沉沉睡去。
次日早晨需扫干净池畔的落叶,中午之前收起昨天洗的衣物,用烧烫的铁壶熨烫,小心翼翼折叠,按样式和颜色分成小包袱,由专人送去各宫各院。
第三日又是蹲在池边洗堆积如山的衣物。接下里数日如一。唯一的好消息,是漫云调去洒扫,可以拿着扫帚走在宫道上,虽仍是苦力,却并不枯燥。
以此往复,统统繁琐而枯燥,却皆为序章。
真正的悲剧出现在半月以后,正是她来月信之时。因近来身体劳累非常,她向上级告了假,早早回屋子里歇息。那间破屋,经过这几日的修葺整理已算是个温暖的居所。采苓躺在硬邦邦却干净的木板床上,一动不动,只等癸水顺畅流通,小腹部的坠痛感方能减轻。
迷迷糊糊的梦里,奶娘端着红糖水来给她喝:“月信来时,各方面尤其应该注意,万不可疲劳受凉。”她本应该咕噜一口气喝干红糖水,却不知为何开始啃桌角,并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她总说自己啥都不怕,其实怕走夜路也怕蛇,最怕的还是那老鼠。如今吓得惊醒过来,耳边还是吱吱吱的声响。按说粮仓在掖庭宫内,这里最见不得老鼠,应该是绝无鼠患的。采苓正想壮着胆子去将油灯点亮,再将那老鼠打死。可是肚痛难忍,她已是极力撑着,还是不敢去点灯,只能蜷缩在墙角,静盼着天光大亮。
没多久,天还没大亮,便有人来拍门,她才刚打开门,小宫女忧心忡忡道:“采苓,你昨日交给我的衣服里可有尚宫大人的披帛。”
“有啊。”采苓不明所以。
“今日司制房派人来领尚宫大人的披帛,要倚着款式、大小再给大人做一件,却怎么也找不到。”小宫女急得额头的冒汗。
采苓安慰道,“我这就去浣洗池边再仔细找找。”
“啊!”小宫女圆眼惊恐地瞪着,手指着采苓屋里除了床以外的唯一家具,破了脚的圆凳,此时圆凳上放着的水绿色衣物已被咬得支离破碎,圆凳另一个角落,一碗打翻了的红糖水浸染着已经残败不堪的衣物,水滴黏黏乎乎往下滴,角落里两只贪婪的大耗子,正意犹未尽品尝着糖水,听到宫女的惊呼,这才一股脑跑了个没影。
“那是尚宫大人的披帛!”宫女惊惧非常,死死盯着采苓。
还是池畔那间平日里浣洗宫女们休息的屋子,高堂上坐着的人却换成了尚宫局的韩司制,冷眼瞧着她:“你入宫多久了?竟然不知糖水是主子们的饮食,宫女也能偷喝吗?”
“糖水为何在我屋中我也并不知情。”采苓面色苍白,极力辩解,“昨日我早早告了假……”
“依本司制看绝非首次,不然何以招致鼠患?”韩司制对一旁的吴姑姑道。吴姑姑近来多有关注采苓,知道她踏实肯干,对那些吃食和衣料更是毫不关心,应该不会躲起来喝糖水,更不会私藏尚宫大人的披帛,正要解释两句。韩司制又道,“吴监作对掖庭的罪妇是越来越仁慈了。以本司制看,此事万不能轻饶。宫女采苓,拖下去杖毙如何?”
“万万不可!”吴姑姑连忙跪下求道。
“本司制试探你而已。”韩司制讪笑道,“吴监作到底心软。本司制自当禀明尚宫大人,或许应该请她同掖庭令商量,再指定监作人选。”
“来人!将采苓拖出去,杖责。”吴姑姑咬唇。
“杖责?还未说数量,吴姑姑这也算惩罚。可惜了尚宫大人的披帛,那可是太皇太后恩赐的料子。”韩司制不依不挠。
“请大人示下。”吴姑姑从牙缝里挤出这些字。
“浣衣局的内务本也不该本司制管,既然吴监作开口求,那本司制就大胆说一句,听闻浣衣局是有水刑的。这宫女犯了如此大错,难道不应该尝尝水刑吗?“韩司制细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阴险。
采苓心中凉了半截,想不到北国奸细想加注于她身上的刑罚在自己的国家、在无比熟悉的未央宫中就要“享受”到了!
如今却不是悲叹的时候,她极力想着脱身的法子,却已被几名壮妇压着捆了手脚,扔进其中一个水较深的浣洗池里。池水及胸,虽是初夏,只觉下半身冰凉刺骨。
迷迷糊糊的意识里,见到一名纤瘦的女子跪伏在浣衣池畔,采苓横眉冷对,怒道:“来做什么?看我笑话。”
“姐姐,别这样!”漫云哭求,“我知道你是故意同我划清界限。”
采苓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颓然道:“既然知道,还不快走。”
“我不会走的。从此都不走。”漫云忍着泪水,“虽然浣衣局里劳务繁重,但能跟姐姐在一起,我心足矣,什么都不怕。”
采苓忍着心痛,脸上一抹苦笑映在水面上,她顿觉头很重,就要栽入水中。
漫云惊呼着涉水而来,一使劲就要将她抬起来,采苓用最后一丝力气道:“我撑得住,此劫过后浣衣局里才总算有我们的位置。你让我撑着……”
起先在小屋内,吴姑姑怜悯的神色不掩,近日以来她勤勤恳恳做工,老老实实做人,无非是要吴姑姑摒弃偏见,要是能受下这水刑,吴姑姑便再不会认为她只是个锦衣玉食什么都不会做的娇小姐。
意志虽强,身体却不允许,晕倒在水池里,漫云连忙将她拖到池畔石板旁:“姐姐等等,我这就去求人。”
记忆从此断片,以为会在昏迷里见到燃着炭火的相府院落,奶娘坐在炉边将棉花塞进丝绸布条里,责她:姑娘家即来月事躺在床上最好,为何要到处跑?全都看不见了,头脑一片空白,应该这便是快要死去了吧。可她还有许多心愿未遂,比如去江南再开一家东喜楼;比如把饼铺的生意在全国各地开上百家分店,那些酥饼可都是照着司膳房的精品制做的;再比如说抚养渊儿长大,那孩子软襦可爱,拉着她的手左右摇摆:姑姑怎么会老?就算是老了,渊儿也会驾着大马车带姑姑周游全国,或许我们还能去北国看看。
……她如何能死!意志尤其坚毅,便只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再醒时,是次日清晨,破旧的小屋内挤满了人,一名穿着翠色襦裙的老妇人坐于床边,见她转醒过来,连忙握着她的手道:“既然醒了,其他都不要想,只需多休息。”
此人正是尚宫局韩尚宫大人,从前在紫微宫里见过数面,从未有深交。采苓意识尚不清晰,只不解其意地看着她。韩尚宫温柔道:“不过是一件披帛,何至于此?”
采苓极力撑坐起来:“可是披帛并非我拿的,那碗红糖水为何会在房中我也毫不知情。”极端的肚痛袭来,额间汗珠滚滚而落。
“吴监作,此事交给你彻查。务必查出事情的真相。”韩尚宫严肃道。
“属下领命。”吴姑姑犹豫,“韩司制还跪在屋外。”
“让她跪着。手伸得还挺长,竟然管到浣衣局来,让她好好反省正好!”又拍着采苓的手道,“你多休息几日。待身体大好了,再出门未晚。”
待到众人离开,漫云将采苓身下的厚棉布移出,只见上面鲜血淋漓,竟已是乌血成块,漫云忍着心痛,如自言自语:“这要是落下病根可如何是好?”见才苓也正看着那一滩乌血块,连忙安慰,“太医局遣人来过,虽只是个学徒,却也跟着医正学医数载,他说姐姐只是感染了妇人之症,一日三次准时喝药,一月后即可无恙。”
“你找了尚宫大人?”采苓只问。
“姐姐好好将养身体,其他的别想太多。”漫云小心翼翼将另一张棉布垫在床板上,见采苓紧紧盯着自己,才嗫嚅道,“是去找了玉安。玉安来后,惊动了内侍局,这才通知了尚宫大人。”
采苓刚听到这里,立即忍着肚痛要下床来,被漫云紧紧按住:“别担心。别担心。我求过玉安了,此事千万不可张扬,不会让陛下知晓的。”
采苓这才躺下,翻身向内,片刻后对漫云道:“谢谢你,再救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