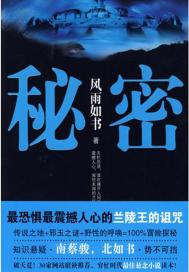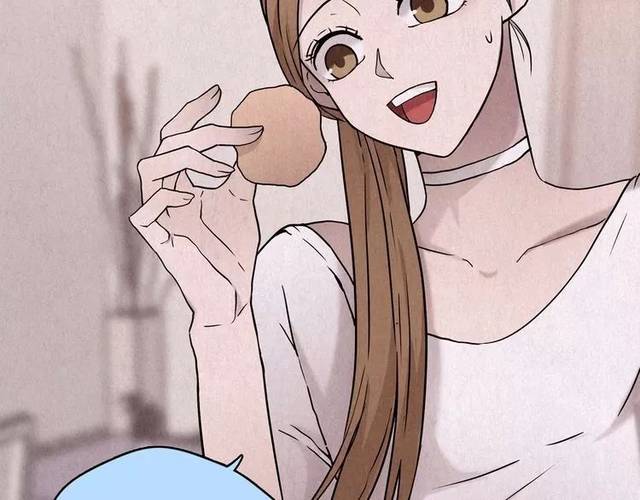这是一个与冲突说密切相关但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问题。黑格尔不是说理想的悲剧冲突的双方都应追求和体现“普遍伦理力量”、“永恒正义”的一个方面吗?相对于理念总体来说,两方执持的东西都有片面性,但这些东西本身还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的,或者说,是受普遍性的力量推动和决定的。对上,它们是“绝对理念的儿子”;对下,它们又是“普遍人类的旨趣”。黑格尔对于戏剧作品是否与这种普遍人类的旨趣有关联的问题相当重视,既然它们都是理念派生出来的,那么众星托月,只有深切地表现了它们,才能把理念烘托出来。一个民族的广大观众取舍戏剧的标准在哪里?许多古典名剧成功的关键在何处?黑格尔都企图在这里找到答案。他所谓的那种推动决定戏剧的普遍旨趣和普遍力量,有家庭、祖国、名誉、友谊、爱情等等。不管哪个时代,哪个民族,人们都关心和追求这些问题,戏剧作品越是抓住它们不放,就越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黑格尔指出:“在戏剧动作情节中互相冲突斗争而达到解决的那些目的一定要是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或是要有在本民族中广泛流行的一种有实体性的情致做基础”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黑格尔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与印度古典剧本以及卡尔德隆的剧本作了比较。婆罗门的宗教生活和僵化的天主教义使那些表现它们的剧本无法为更多的观众长久地欣赏,但莎士比亚剧作的观众却日益增广,“因为它们尽管具有民族的特点,其中占很大优势的却是普遍人类的旨趣”。世界上不欢迎莎士比亚的地方也有,但那不是出于观众心理的抵拒,而是狭隘而特殊的清规戒律在某些民族的艺术领域里作祟。可以与莎士比亚比拟的是古希腊戏剧,它们在题材方面也是任何时代都不会丧失其效果的。反之,如果戏剧只写那些“只是由某一民族的时代风尚所决定的非常特殊的人物性格和情欲”,那么,黑格尔指出:“不管它有多少其他优点,它也就愈易消逝。”
但是,要让观众感受到这种自己身上也有的普遍旨趣,戏剧艺术的特殊使命是要把它们化为一种“有生命的实际存在”,它们是普遍旨趣和普遍力量的个别化和具体化。基本方式是删略无关宏旨的外在因素,把戏剧人物的性格写得生动具体。正是活生生的戏剧人物,给了普遍旨趣以可感的生命。黑格尔把性格看成是理想艺术表现的中心,戏剧当然更是如此。
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问题,黑格尔也曾不止一次地发表意见。这些意见主要可以分为性格所应有的特点和性格塑造方法两个部分。
人物性格应该具有哪些特点呢?黑格尔分三个层次进行论述。一是把性格看做具有各种属性的整体,写出各个个别人物性格本身的丰富内容。在这里他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但是≯性格的这种丰富而又完整的特点,史诗表现起来要比戏剧更便利。二是把上述丰富的整体显现为某种特殊形式,突出一点,作为对性格多方面性的“一个统治的定性”。这种性格特点就表现为明确性,例如莎士比亚创造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两个性格,就是以爱的感情作为他们的“统治的定性”的,因此使人感到丰富中的明确。这种性格特点就适宜于戏剧来表现了,戏剧中的主角大半比史诗中的主角较为简单。三是把上述明确性显现为一种一贯的行动,始终如一,决绝不易,可名之日坚定性。普遍力量的展现需要有一个过程,而性格的坚定性正是保证了这一点。为此,罴格尔反对主角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反复无常,反对让他受制于人,更反对把他写成忧伤抑郁、悲观失望的人物。这样,他就排斥了近代文学和近代戏剧中的许多性格刻画。
在戏剧性格的塑造方法上,黑格尔主张具体,反对抽象;主张内在化,反对表面化;主张有机融合,反对特征凑合;主张在冲突中刻画出生动性,反对在宁静中作平面描绘。他虽然着眼于普遍旨趣,却又深深懂得如果人物性格“只是一些抽象旨趣的人格化”,那就“简直不会产生效果”。具体了,但却是表面的,那就会成为寓言式人物,不成其为戏剧性格。抽象化、表面化的戏剧创作的共同特点是把许多不同的特征和活动生硬地串在一起,特征来自演绎,串联仅止表象。黑格尔认为这是塑造不出一个有生气的人物性格来的。他说,
戏剧人物必须显得浑身有生气,必须是心情和性格与动作和目的都互相协调的定型的整体。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特殊性格特征的广度,而在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实际上这个整体就是个性本身,而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泉源,从这个泉源派生出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把许多不同的特征和活动串在一起,尽管也形成一个排建成的整体,却不能显出一个有生气的人物性格。
这段话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说到性格必须在冲突中展现,这便牵涉到黑格尔对于“戏剧方式”的理解了。尽管他承认在许多艺术上人物是中心,但他又认为,单纯的人物描写不能直接体现目的,也未必符合每门艺术的特殊方式。戏剧的根本方式还是由冲突组成的戏剧动作和戏剧情节。人们不会仅仅为了表现性格而去动作、去冲突的,相反,往往是在动作和冲突中很自然地把性格显露出来的,戏剧在表现这两者关系时也是如此。这是亚里斯多德谈到过的,黑格尔表示赞同。
黑格尔关于赋普遍人类的旨趣以具体生命的论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戏剧创作的实际指导价值。将具体的戏剧人物与重大的社会意义接通血脉,既使人物在更大的空间范畴和时间范畴中发生影响,又使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化作具体、可感的生命体,这是让两方面都得益的好见解。其中对于“生命体”的结胎,亦即人物性格的塑造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也显得切实可观。缺憾之处是未能对那种所谓“普遍旨趣”和“普遍力量”作理论上的个别化、具体化的定性,结果它们尽管被设想了在戏剧作品中的实际体现,但在设想者自己的理论中却始终没有成为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况相联系的“有生命的实际存在”,始终是一个虚缥空泛的概念。当然,从理念出发的黑格尔也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