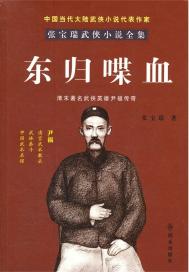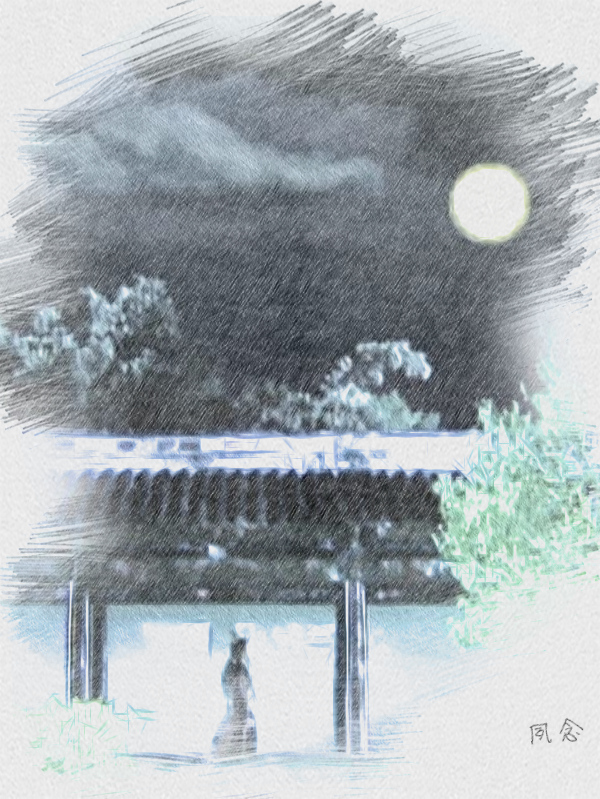除了对结构和布局的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外,李渔戏剧理论中另一个比较具有贯串性的思想是求新。
李渔一谈及这个问题就以戏剧的特殊性作为出发点。他说,“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至于填词一道,较之诗、赋、古文,又加倍焉。”这是他对自己的美学思想所作的极有层次的袒示。他不赞成食古不化的行径,反对在艺术上因循守旧,把一个“新”字放在自己整个美学思想领域的触目地位上。在他看来,“新”与“美”这两个概念颇为接近,对天下事物均是如此,而于文艺尤甚;在文艺之中,戏剧还应比其他艺术样式加倍地求新。理由何在?对于文艺的总体来说,如若一味因循守旧、不脱窠臼,再有才华也只是机械模拟,“徒作效颦之妇”,“遂蒙千古之诮”;戏剧之所以要特别求新,李渔认为是它的特殊观赏方式决定的:“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戏剧面对观众,演出频繁,因而“尤是新人耳目之事,与玩花赏月,同一致也。使今日看此花、明日复看此花,昨夜对此月、今夜复对此月,则不特我厌其旧,而花与月亦自愧其不新矣。故桃陈则李代、月满即哉生。”这就十分紧密地联系着戏剧特殊的艺术特点来为新张目了。依据近代艺术分类学和艺术特征论,戏剧的欣赏与诗、画、小说的欣赏很不相同,欣赏者与欣赏对象的依赖、吸附关系特别紧密,而当欣赏过程一开始,欣赏者大多就失去了挑选或搁置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反复地看同一出戏,要比反复地看墙上的同一幅画难于忍受得多;但无论从剧团还是从观众的角度,演出都应该是经常的,那么戏剧内容本身的新就特别显得重要了。李渔是在自己长期的戏剧活动生涯中感受到这种特殊的重要性的。李渔同意“无传不奇,无奇不传”这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把“新”和“奇”相等同,甚至直言“新,即奇之别名也”。毋庸讳言,他把“新”的概念定得过于狭窄了。他曾说,不仅前人写的一概不能称之为新,而且自己前些日子编演的也不是新,简直一句话,被看见过的就不是新,“知未见之为新,即知已见之为旧矣。”这种浮浅而绝对的见解使“新”的地盘越来越小,只好和“奇”合并为一了。我们在考察日本世阿弥的戏剧观时曾看到这位能乐大师在戏剧新鲜感的问题上存在着无原则地迎合观众的倾向,这在李渔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对戏剧的过于商业化的理解使他难脱炫奇趋时的偏好。同是一句“惟陈言之务去”,韩愈意在特立独行,“能自树立不因循”(《韩昌黎集·答刘正夫书》),李渔则意在观众口味,并不想“自树”什么。他说写一个戏之前先得问一问过去有没有人写过这种情节,“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不多去过问其他。
但是,李渔毕竟也在急急追求新奇的艺术跑道上树了一块禁戒牌:“戒荒唐”。所谓荒唐,他主要是指魑魅魍魉,见闻之外、不合人情的怪异事件。他说,“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无论词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这样,“戒荒唐”这一否定性主张引出了“说人情物理”这一建设性见解,新奇也就有了一个限制。李渔有不少地方讲到人情和情理,如“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传奇妙在人情”之类,概念的内涵并不稳定如一,但却反复地表明了他是把戏剧题材的重点安置在合情合理的现实人生之中的。人情物理,他重在人情;写景言情,他重在言情;外貌内情,他重在内情。有这么一个重砣悬挂在里面,李渔所谓的追求新奇,便主要表现为在“家常日用之事”中挖掘追索。他把戏剧与人世间比较稳定、比较普遍的情感因素和理性因素的联系程度,看做戏剧艺术生命长短的关键,这是深刻的。他说历史上不少关乎人情物理的典籍长期流传、家喻户晓,而某些荒唐怪诞的志怪之书却只存其名,未能传下。他又说,之所以还会有不少人热衷于这种“当日即朽”的荒唐,是因为“画鬼魅易,画狗马难”,自知自己无力刻画那些人人习见、人人可以指摘评论的内容,只好一头钻在谁也没有见过的鬼域之中借以“藏拙”。当然,对于文艺作品中的鬼魅世界也不可一概而论,比李渔小三十岁的蒲松龄将以自己的《聊斋志异》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但李渔这些意见的基本精神还是可取的。在日常生活中找出艺术矿藏,在平凡习常中挖出新奇内容,这确实是一条广阔的艺术道路。
既然李渔对自己提出的新奇作了如许制约,那么很自然,他就不能不论述如何在平常的人情物理中追求新奇了。他指出有两种情况,一是同样性质的事情,由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和深邃,做起来会愈出愈奇,所谓“物理易尽,人情难尽”,“尽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后人”。因此在每个看来极为平常的领域里都会“有日异月新之事”,李渔以他的时代最为习见的家庭闺阃题材为例,证明像“贞女守节”、“妒妇制夫”这样的常事范围内,生活中已发生许多耸人听闻、前所未有的奇事;二是前人已经写’过的事情,也“尽有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即也有施展才华的余地,也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可能,结果“使人但赏极新极艳之词,而竟忘其为极腐极陈之事者。”这当然很难,李渔说他自己也没有做到,但他在理论上充分地肯定了这种可能。概括起来,李渔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新奇之事是挖不尽的,被人早挖过了的还能进一步挖掘出新奇的内容来。这样,他就把题材限制和新奇统一起来了。
作为一个需要不断演出的戏班子的主人,李渔也懂得不能完全依赖新创作的剧目,因为这总是供不应求的。那么,演旧剧又怎么和追求新奇的观点统一起来呢?李渔提出了“变旧成新”的主张。他反对有的戏班子“演到旧剧,则千人一辙,万人一辙,不求稍异。观者如听蒙童背书,但赏其熟,求一换耳换目之字而不得。”旧剧新演,必须有所改易,但又不得超过限度,致使失却基本面目,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李渔以美人作比,说可变其“丰姿”,不可动其“体质”。具体说来,戏曲中的曲文和大段关目就像美人的体质,不应去动它,一则因为这是原作者的心血所在,应让它常留天地之间而不应由我之手使它埋没;二则因为一般人们往往认为古代的作品不会比今天差,你改来改去反而招人嘲笑。“仍其大体,既慰作者之心,且杜时人之口”,这是李渔在旧剧新演的问题上申述的第一个原则。戏曲中有一些内容如“科诨”和“细微说白”之类则像美人的姿态衣饰,那就不可不改,原因是“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李渔不是一再强调戏剧要“人情”吗?台上演的戏如已完全违逆了今日之情态,观众就难于动情不易接受。因此他说,如果原作者还活着,他自己也会改的,说不定当年他活着的时候,多看自己的几遍演出就想改了呢!李渔还自信地说,如果“我能易以新词、透人世情三昧,虽观旧剧,如阅新篇”,作者如地下有灵是会感激的。至于旧剧中有的还留有不少漏洞,那就更有必要“靠后人泥补”了。然而总的说来,增、改之间须持谨慎态度,“但须点铁成金,勿令画虎类犬。”
在李渔关于改动旧剧的论述中,我们又看到了一朵熟悉的火苗:“透人世情三昧。”可以说,他整个关于新奇问题的论述,也正因为“透人世情三昧”而增加了不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