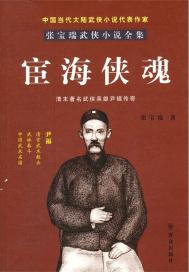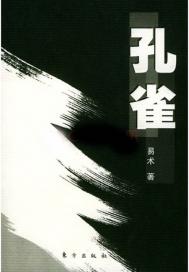李渔生前没有能够见到清代戏剧创作的高峰,他跋涉在由前代高峰通向新的高峰的山坡上。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指出:
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其最相异之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异《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
梁启超还论述了诗、散文、小说等领域的情况,不能说没有鸟瞰式的宽广见识,但也不乏不够公正持平之处。上引他对清代戏剧的看法,确实是劈头就把握住了一代峤岳,但判定出现了孔尚任、洪异的时代为“不发达”,多少显得有些武断,这与他在小说领域只承认一部《红楼梦》,而又把出现了《红楼梦》的清代文学界说成“不发达”是一样的。
以汤显祖为最高代表的明代浪漫主义戏剧创作潮流,到明末社会大变动时期已渐渐减弱,及至清初,更不成气候了。这与急剧变化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清代的满族统治者和元代的蒙古统治者是不同的,他们在汉族人民的血泊中夺取南方、稳定政权之后不再盲目、愚蠢地继续虐杀汉人,更不与汉人的传统文化对立,而是以远比蒙古人高超的统治才能和文化修养实行威柔并济的文化统制。被明代的许多思想家、文学家摇撼过、批斥过的程朱理学,在康熙等人的竭力倡导下又神气起来,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戏剧创作的敌人。反清的杰出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主张通过研究经史来复兴民族、改革社会、启迪天下,但他们在提倡严正的学术风气的同时也抨击了明代反道统的进步思想家,甚至还抨击了小说和戏曲。结果,尽管梁启超把清代的学术发展比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上却反而出现了那些近似文艺复兴的因素一时被压抑的情况。这主要表现于上层抗正统、违古典的文学思潮的被贬抑,直抒性灵的文艺方式的被遗弃,以及下层市民文艺的被轻视。难怪梁启超要把文艺置之于“复兴”之外了。
但是,尽管创作思想有所变易,戏剧的繁荣局面倒一时没有变化。康熙等人并不厌弃戏剧,官绅地主更以私养戏班作为奢侈生活的重要标志,据记载,康熙年间北京“养优班者极多,每班约二十余人,曲多自谱,谱成则演之,主人以为不工,或座客指疵,均修改再演。”(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于此可见一时之风。有一些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不愿与清王朝合作,蔑弃科举,或以剧遣怀,或借剧泄忿,也使剧坛保持了不少生气。清初比较有影响的是李玉、朱素臣等吴门戏剧家,他们的成功之作是歌颂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和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暴政的剧本《清忠谱》,这个剧本以发生在一六二六年的实事为依据,与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为中国戏曲史上所罕见,艺术上也条理清晰、气氛浓郁、真实动人。李玉还写过《干钟禄》、《万里缘》等一些不错的剧本,朱素臣则有《十五贯》、《翡翠园》祭当时还有几个以写杂剧为主的剧作家如尤桐、吴伟业等,把戏当做诗歌来写,人称“案头之曲”,寄寓个人感伤,很难付诸演出。李渔就出现在这样的境域之中。
李渔(一六一一~一六七九年),晚年号湖上笠翁,原籍浙江兰溪,出生于江苏如皋。早年好象受明“公安”、“竟陵”派文学的影响较深,神颖任侠,不拘古礼,游历四方,曾到过苏、皖、赣、闽、鄂、鲁、豫、陕、甘、晋、北京等地。十七世纪中期清兵入浙前后家道衰败于战乱,面对满目凄伤,他思想变化很大。尤其是著述和藏书被焚,使他不能不感慨于学术文化在离乱之世的空虚和软弱。就此,他从沉迷于文章意气,变得孜孜于应世干禄。入清以后他移居杭州、南京,曾开设过有名的“芥子园”书铺,出过不少带有明显商业性目的的工具书,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
李渔酷爱戏剧,他一生最主要的行迹是戏剧活动。他曾这样自述:
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
他家里设有戏班子,经常奔走于达官贵人门下以博取馈赠。家庭戏班中的女旦,多半是他的小妾,此时他已无田产支撑这么一个庞大而腐化的家庭,不能不在许多方面仰仗权贵:负笈四方,托钵终年,往吸清风,归餐明月。
莫作人间韵事夸,
立锥无地始浮家。
制成小曲惭巴蜀,
折得微红异舜华。
檀扳接来随按谱,
艳妆洗去即沤麻;
当筵枉拜缠头赐,
难使飞蓬缀六珈。
(《次韵和娄镜湖使君顾曲》)
这是一种热闹、繁忙而又不无心酸的卖艺生活。他自己除了训练演员、导演剧目外也登台演戏,同时又写了不少戏供自己的戏班演出,有时只写完一半就先拿去付排了。总之,他是一个戏剧全才,一个精通这门综合艺术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戏剧实践家。他的剧作以《笠翁十种曲》较为著名,内包《怜香伴》、《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这十种传奇,总的说来,无甚精彩。其中除了《比目鱼》、《蜃中楼》有一些比较正当的意蕴外,大多轻薄不德、趣味低下,钻在偷情纳妾之类的圈子里,甚至还有阿谀豪富的内容。艺术上也过于追求巧合、噱头,格调不高。较可取者,是在编制情节、铺排场面的技巧上比较熟练,结构上针线较密,容易付诸演出。但这无改于梁启超所说的“浅薄寡味”。
李渔这个人,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特殊的生活领域里的复杂存在。他既有附炎趋势的一面,又有违世逆俗的一面,而无论哪一方面都根据自己的独特才能采取着独特的方式。
首先,尽管作帮闲文人是明末清初知识界的一种风习,但作为一个出身并不低微的知识分子而踞身于优伶行列,还是需要下点决心的;而公然洗去高雅之色,直示谋生营利的本相,则在当时的戏剧家中也未免显得过于袒露无状了,与他同时的戏曲作家袁于令说他“善逢迎,游缙乡间”,“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也”,这就显示了李渔与时尚的知识分子处世立身观念的距离。在清廷复兴理学的时代,李渔并不是一个反理学的斗士,但他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格调显然是不能见容于理学和道统观念的,或者说,他至少需要有一些消极反抗的勇气才能如此行事。据说李渔针对人们的贱视反而额其寓庐日“贱者居”,可为一证。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把李渔与元代关汉卿等人等量齐观,他只是在职业方式上,而不是在戏剧活动的实际内容上与上层社会的正统观念保持着距离。在演剧的实际内容上,他是力求缩小这种距离的。这就是他品格上的既矛盾又统一之处。既不是长年劳顿于科举途上渴求一官半职的正统文士,也不是仇视豪强、厌恶道统而啸傲于山林的叛逆者;以权势者所不屑之技艺而取悦于权势者,自己则从中施才、谋利、取乐,这就是李渔。
其次,李渔的逢迎谋利是以自己颇为丰厚的艺术修养为基础的,这使他具有非一般文化商人和戏曲班主可比的功力和魅力。他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偏重于生活趣味和现实享乐,广泛、实用、散杂,间或还能窥见明代“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遗风,与拟古复古、皓首穷经、端严方正的道学家又一次拉开了距离。中国现代文学家林语堂曾这样赞叹李渔艺术修养的广博和独特:
他是一个心裁独出,思想卓越的人,所以他对每个论题,都贡献了一些新的观念。他所独创的东西有一部分已经成为今日中国人的传统了。最杰出的贡献是他的信笺(当时出售,名为“芥子园名笺”),和他的窗户设计及墙壁设计。他的《闲情偶记》一书虽然知者不多,可是他的《芥子园画谱》(中国初学画者最常用的范本)及《十种曲》却是很有名的。他是一个戏曲家,音乐家,美食家,服装设计家,美容家和业余发明家。
(《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出于自己的生活和艺术追求对李渔有着明显的偏爱,但李渔的才学确实是不可抹煞的。思想家鲁迅曾深刻地指出李渔是一个有才能的“帮闲文人”:“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而且把他与袁枚相提并论(《从帮忙到扯淡》)。有的文学史家甚至直接把李渔与袁枚、金圣叹一起列为晚明反拟古、主性灵、攻道学的思想余波在清代的主要代表:“金圣叹尽力于鼓吹小说,李渔尽力于戏曲,袁枚则尽力于诗歌”,并说李渔“对于人生与文学的态度,都与公安一派人相近。他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在他的著作里,留下许多描写生活趣味和山水花草虫鱼的小品文,这些都是清新流丽趣味丰富的文字”(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五八年版)。这个论述多少也有溢美之嫌,但通过李渔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能和文化心理结构,把他从封建卫道派及其庸庸碌碌的扯淡清客的营垒中划分出来,则是公平的。带有明显的迎合性质和博利目的的传奇创作不能完全代表他的艺术情怀,反映他的落拓本性。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他的另一层矛盾,即在各方面都自愿地蜷曲于时尚习俗之下的所作所为与他在青年时期被开拓、激扬得颇为自由的内心的矛盾。这比起上述敢于坚守正统文人所不屑的职业,但又不得不服务于权贵的矛盾来,思想意义更为深刻了。李渔在重重复杂的矛盾中,有的地方让外力消蚀了自己,而且消蚀得十分厉害;有的地方则也隐隐地存守着本性,款款地抵拒了外力的吞食。正是这个原因,他既不能以光华夺目的品格受时人和后人的景仰,又不会平庸到不留任何印痕于历史;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留在历史上的印痕本身也常常发生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如他杰出的戏剧理论和并不见佳的戏剧创作的矛盾,便是一例。为演出匆匆赶写的剧本有着比较直接的迎合和谋利目的,质量自然就差;反之,与这些目的远一点的理论著述、散文小品,因能直抒胸襟,倒可以见出一些真功夫和真情趣。
李渔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较大反响的,正是林语堂所说的“知者不多”的《闲情偶寄》,尤其是其中的戏剧理论。
李渔的戏剧理论比他的戏剧创作更能体现到他为止戏剧经验积累和戏剧思想发展的成果。李渔去世之后八九年,洪异就写出了《长生殿》,再过十年,孔尚任写出了《桃花扇》。与李渔剧作相比,这两部杰作无异是拔地而起;但考之于李渔的戏剧理论,则可发现新的戏剧高峰的出现确已具备了足够的艺术条件,当然,这并非是就洪、孔与《闲情偶记》的直接关系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