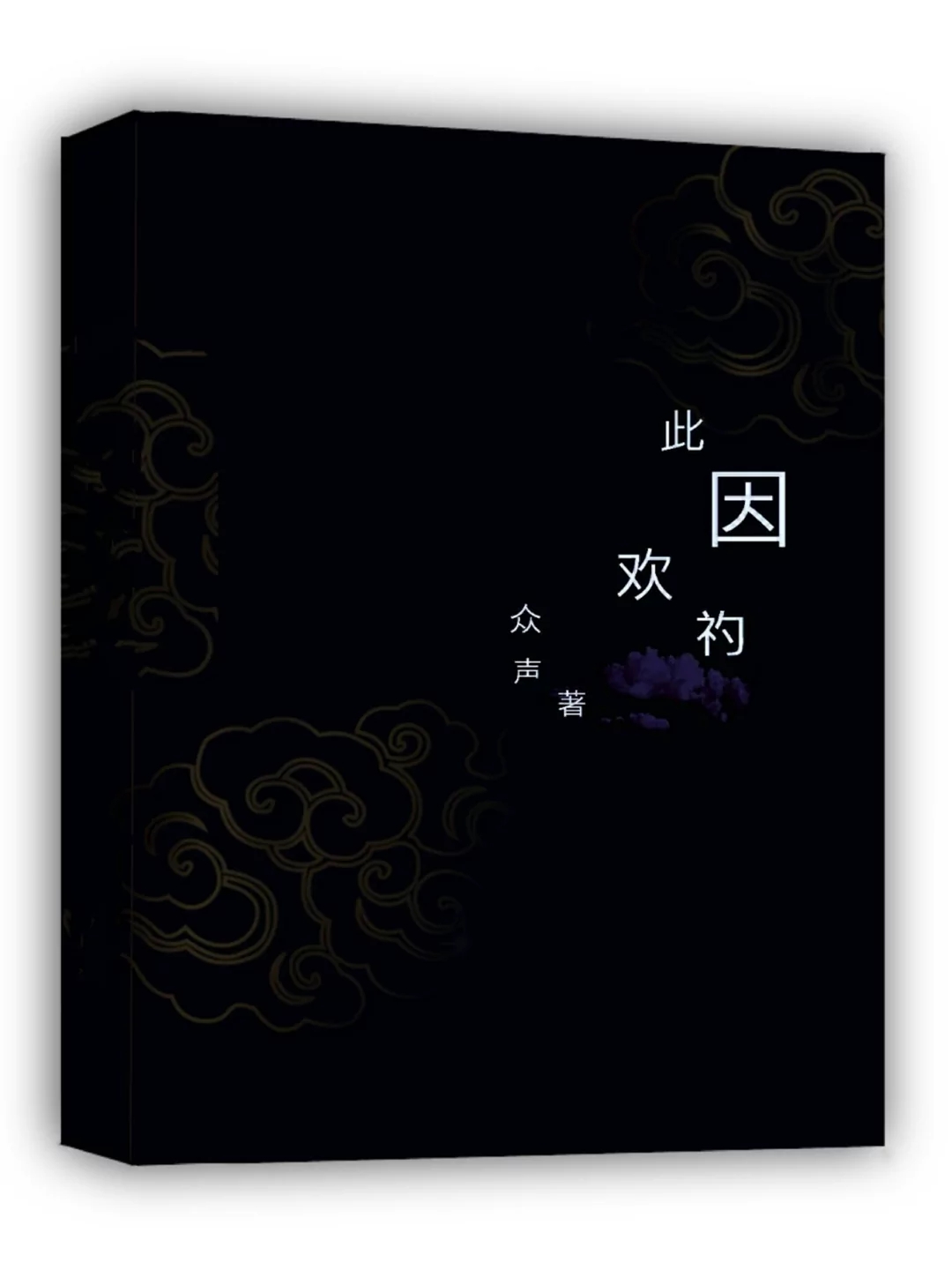天造其势,人造其果。
二十多年前,因为一场四人的感情纠纷,引来多年以后的恩怨。
只是,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复仇,然蔓延伸展到今日,已经并非简简单单的恩怨情仇了。
那是,早已一发不可收拾、无法回头的贪得无厌。
这么多年来,她心中心心念念的复仇,是颠覆武林。而今过了这么久,颠覆武林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复仇。
贪心不足蛇吞象!
听七楼中尸横满地,却全都是一些无辜的家丁下人。
“公子出游时,楼中的弟子奉了你的命令,不允许接手关于无痕组织的任务,更不允许乱造杀虐,是以很多人在楼里待了许久,乏腻之后便离开,外出闯荡去了。”
七角楼前,聂涯儿努力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尽力平稳地向洛夜白解释着。
“我前往寻找公子的时候,尚有两位长老留在楼中,所以我想,这一次来的人一定不是泛泛之辈……”他说着看了看地上二位长老的伤口,全都是一招毙命。
听着他的话,洛夜白神色镇定得有些异于寻常,看得聂涯儿心里直寒。
每次公子露出这样的表情,都不会有好事情。
“发出白色令,通知楼中弟子即刻赶回。”冷冽清越是嗓音中带着冰濯的寒意,直逼人的心脏,他说着看了看地上的尸体,眼神蓦地一寒,“将所有人都好生安葬。”
“公子——”聂涯儿抬眼看了看楼上,欲言又止。
“去吧。”洛夜白并没有回答,只是淡淡说了两个字,背过身去。
楼上,阿难陀站在窗前,将一切都尽收眼底,心中不免有些压抑,骤然胸口一同。姜儿见了,连忙将她扶到桌旁坐下。
“阿难陀,为何整个听七楼都被毁了,却唯独这座七角楼尚完好无损?”姜儿递给她一杯茶,不解地问道。
“七角楼周围都布有阵法,待在这里,你最好老老实实地不要乱走动,万一触动了阵法,我不由得救得了你。”阿难陀接过水杯,却并没有立刻喝下,而是四周环视了一圈。
“阿难陀,你在找什么?”
“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曾经在这里照顾过我的人……”话音未落,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她没有回身,只是淡淡地问道:“为何不见寒之姑娘?”
“陆府有事,她回去了一趟。”洛夜白声音低沉,却还是对阿难陀的问题有问必答。
“哦?是什么事竟然能让她离开听七楼?”
“她的好姐妹,陆府的管事夏亦姑娘出事了。”他说着淡淡地看了阿难陀一眼,目光锁紧她风轻云淡的眼眸,似乎想要从中看出一些什么,“她受伤了。”
“就是那个精明能干的丫头?”
呵!近来江湖上还真是不太平,只因为有人不想让它安稳太平下来。她的怨恨究竟有多深,又要杀多少人,她才能罢手?
也许,她根本就不会罢手。她已经停不下来了。
有些事情,在你能控制它的时候不把它牢牢控制好了,待到它逐渐膨胀之后,你再想要控制住它时,就已经是无能无力了、身不由己。
比如说,野心、贪念。
“没错,陆少遇袭,她替陆少挡了一剑。”看她的眼底除了惋惜和平淡,就再也没有多余的情绪。洛夜白心底终是忍不住划过一丝黯然,继而被敛去不见。
“看来,有些人已经无法悬崖勒马了。”她低下头,端起杯盏呷了一小口茶水,润了润有些干燥的喉咙。
“什么人?”
“造孽之人。”
“听你的语气,似乎有能制住她的办法。”洛夜白冷眸一沉,定定地看着阿难陀,“你究竟知道多少东西?”
“呵呵……我知道那么多事情,有何奇怪的吗?”凤眸一挑,淡然地迎上洛夜白探究的目光,“难道七公子就没有想过,为何这么多年来江湖能一直这般泰然安详,没有太大的是非风波?真的,真是因为你们三大组织的三足鼎立相持而来的?”
洛夜白的眼神咻然一顿。
“当然,三足鼎立维护了整个武林的和平,是一个不可争论的事实,只是,有没有人想过,为何这毫不相干的三方会如此识时务,顾大局,又为何会配合得如此完美,天衣无缝?难道,在这三方的背后,就没有另一个组织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陆府、听七楼和冰凝山庄实则是受命于同一个人,或组织,是这个组织让他们这么做,也维护为了和平?”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随口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七公子听听便是,不必放在心上。”
洛夜白微微侧身,睨了她一眼,看见她低头敛目,轻轻蹙了蹙眉,想必是身体不适,心中又不由得一紧。
“连着赶了两天的路,怕是你身体难以吃得消,还是先歇着吧,药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他说着看了阿难陀一眼,见她微微点头,便转身出了房间,下了楼。
不拖沓,不勉强,不纠缠。
这是当初他答应过莫娘的,他为人处事一向说到做到,所以现在他不会纠缠于那些不该纠缠的事情。蛊毒尚未解,安全尚且不能确保,其他的一切都只是妄谈。
至少如今,他可以守在她身边,可以整天见到她。
这本是一种奢求,而今奢求达成,便是他最大的庆幸。
身后,阿难陀走到后窗前,看着后院里那座凄凄凉凉的无名荒冢,眼神一点点暗淡下去,继而转身吩咐道:“姜儿,备些酒来。”
记得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还是三个月前。
那时的听七楼威武严紧,别说有人能随意进出杀人,便是一只鸟儿都别想来去自如。而今的听七楼,满是凄凉与沉寂,若非得令赶回来的那些弟子,多一个人影都难以见到。
也是啊,那时有洛夜白在,苏焕、聂涯儿和寒之都跟随左右,自然不可能有人能动得了听七楼分毫。
而现在——
微微一声太息,手中酒壶里的酒全都洒在荒冢前。
好久不见了,苏焕。转眼一别已数月,这些时日来,我却没能为你做任何事。我姑息养奸,我纵容凶手,任她肆意伤人。你说,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只是,佛语有云,善恶终有报,我知道我终究拦不住她,也救不了她。
那个人已经生气了,他发怒了,他已经追查到了我这里。我比谁都清楚,即便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告诉他,他一样可以很快就查到真相,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没有能瞒得住他的事情。
远远地看着她低头倾酒的模样,洛夜白有些许的恍神。他缓缓走上前,替她披上手中的披风。
“这里夜间有风,天冷,注意身体。”他说着自然地接过她手中的酒壶,对着荒冢洒下一片酒水,眼中的深深的沉恸和愧疚。
“他一个人待在这里未免孤寂,弗如将他同其他弟子一起葬了吧。”
她知他心中伤心,也知他是想保护她,所以才隐瞒了苏焕的死,甚至墓碑上连一个名字都不能留。然而,将苏焕葬在这里,终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就像她站在后窗便可看到苏焕的坟墓一样,他会每天睁眼闭眼都可以看到,而每一次看到,终会免不了一场心伤。
可是,她不想看到他伤心,尤其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她。
若不是她现在一点武功都没有,又何须苏焕为了她受那三剑?
“我会替他报仇,用那人的鲜血来祭他的墓碑。”淡然轻缓的语气,静淡无奇的神情,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心中惊寒。
侧身看着他平静无波的眼底,极力压抑着的愤怒,那种隐忍已然就要到了极限,他却还在努力忍着,幽深的眼眸中是种种情绪的交杂,在看透他深深隐藏的心事之后,所有的情感都一目了然——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在他最困惑无助的那段日子里,是苏焕和聂涯儿陪着他走过来,他们就像他的两只左右手,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不是主仆之情。如今苏焕死了,无异于等于硬生生地砍下了他的一只胳膊。
“对不起——”短短的三个字,她却憋在喉咙里许久,才说了出来。
尽管早已说过这句话,可是看到他这样的神情,她的心又一次隐隐作痛。
突然,那阵冷热交替的气流突然在全身又不安分地窜动起来,冷不防地从手脚窜上心头,阿难陀只觉眼前一阵暗淡,接下来便是铺天盖地的晕眩。
看着她摇摇欲坠的身体,洛夜白一转身将她拦腰扶住。
“怎么回事?”眼看阿难陀的脸色逐渐变得难看,不多会儿,竟与刚开始中毒时那样,一阵红一阵白,看得他心底一阵阵不安,“毒不是已经快解了吗?”
不由分说,将她抱起,连正门楼梯都不走,直接跃身上了二楼的窗户,从窗户进了二楼。
正在里面收拾东西的姜儿被吓得一愣,再看洛夜白怀里越来越虚弱的阿难陀,顿然变了脸色,战战兢兢地看着洛夜白将阿难陀放下,把脉,一句话也不敢多问。
但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洛夜白神色越来越难看,蓦然握紧了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