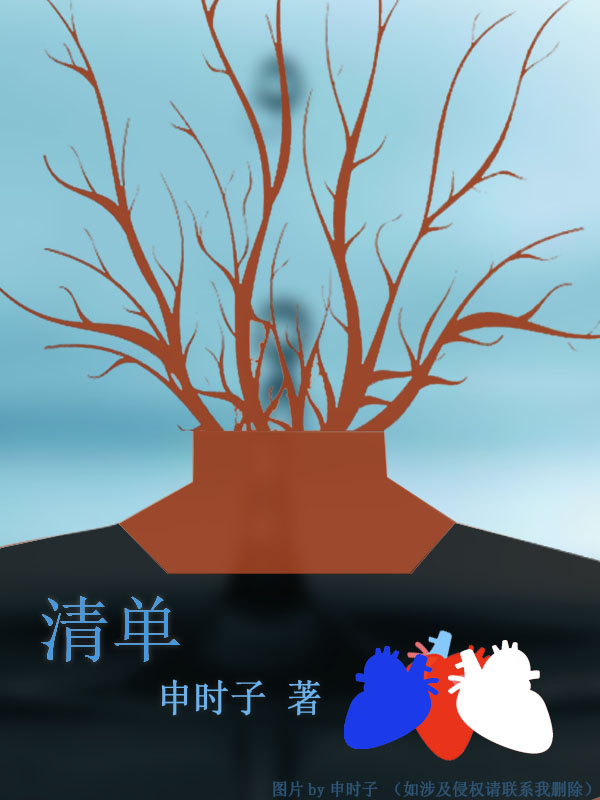我终于理智起来。
如果说西区没人,我信,如果说周Sir两口子不是人,那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相信。我们一起进入404的这些人都见过他们两口子,而且是光天化日,还在他家吃了饭,还在他家睡了觉,他们怎么可能不存在?
我只是被老姜这个梗给吓着了——两个守墓人给自己的尸体守墓。
我对他说:“你跟他们两口子打过交道吗?”
老姜说:“我长年累月在西区等人,多寂寞啊,我跟他们是邻居,当然要交往了。那两口子人挺好的,总照顾我。”
我又有点糊涂了,如果他们不是活人,怎么照顾老姜?
我必须得走了,我说:“嗯,我走了。”然后又加了一句:“如果你实在等不来就回老家去吧,廊坊现在发展得挺好的。”
老姜没有接话,我走出很远之后,听见背后的浓雾中传来了他的声音:“你留心一点,晌午12点你保准看不见他们。”
追着我吓是吧?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浓雾似乎凝固了,一直不肯散去,我听到西区的大喇叭响起来,正是那条通缉我们的广播。
我一路摸索着,终于走进了西区,隐约能看到房屋,却不见一个人,真的有一股墓地的肃杀之气。我正在辨别着周Sir家在哪儿,浓雾中突然闪过一个人影,直觉告诉我那是个女的。
我又生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李红?
这个人迅速不见了,我都没听见脚步声。
我绕过葵花杆夹成的小园子,来到了周Sir家门口。我很不希望我是第一个赶到的,虽然老姜说的话不可信,但被他一渲染,我的心里还是虚虚的。
周Sir家的门上贴着两个门神,那是神荼和郁垒,都褪色了。里面有人在说话,我听到了四爷的声音。
我赶紧敲了敲门。
有人走过来给我打开了门,正是周sir,他看到我之后什么都没说,而是警惕地探头看了看,这才说:“赶紧进来。”
其他人都到了,他们正坐在东屋的炕上说着话,我一下就放松了。几部手机都在充电,把房间里所有的插座都占用了。
四爷说:“你腿脚有毛病?”
我说:“半路遇到了一个人,聊了会儿。”
四爷说:“谁啊?”
我说:“西区的那个老姜。”
说到这儿我看了一眼周Sir,他并不关注我们在谈什么:“你们还没吃饭吧,我去叫我媳妇给你们做饭。”说完就要往外走。
我说:“你等一下。”
他就停下了。
我审视了他一会儿,突然说:“西区有人吗?”
他愣了愣:“你放心,没人知道你们在这儿。”
我说:“我问你,除了你和你老婆,西区还有别人吗?”
周Sir说:“有人啊。”
我说:“你能给我叫来一个吗?”
周Sir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你想找谁?”
我说:“随便,是个人就行。”
四爷说:“小赵,你怎么了?”
我说:“你别管。”
周Sir马上对着西屋喊道:“媳妇,你把隔壁老李叫过来。”
接着就听见了大波浪的声音:“干啥啊?”
周Sir说:“有点事儿。”
大波浪说:“他不在。”
周Sir看了看我,又说:“他干啥去了?”
大波浪说:“都去办公大楼领衣服了。”
我说:“都去了?”
周Sir说:“都去了?”
大波浪说:“都去了。”
我说:“就是说,除了你们两口子,其他人都不在?”
周Sir说:“这些人干活儿没力气,只要免费发东西,个个都跑在最前头。”
有这么巧的事吗?
天色太昏暗了,棚顶的灯泡亮着,不超过50瓦。我看着眼前的周Sir,忽然有些恐惧。
小差、四爷、Asa、小马哥都察觉到情况有点不对,但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听。
我说:“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周Sir就像传声筒一样朝着西屋问:“他们啥时候回来?”
大波浪说:“那可说不准了,他们每次都去食堂蹭饭,说不定明天才能回来。”
周Sir对我耸耸肩:“这些人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
我突然换了个问题:“你和你老婆为什么不要小孩儿?”
周Sir有些不好意思,他朝西屋指了指,低声说:“检查过,你嫂子/宫颈粘连。”
我说:“是吗?”
周Sir马上说:“我没问题。后来一想不要就不要吧,咱也丁克一把。”
Asa说话了:“小赵,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能说吗?我要说的是——周sir,你和你老婆是不是都被烧死了?
我没理Asa,接着对周Sir说:“西区这些人为什么不搬走?”
周Sir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我没有接话,继续说:“你们两口子跟老姜的关系怎么样?”
周Sir说:“唉,他媳妇不是在‘919事故’中死了吗,他受了刺激,脑子就不好使了,挺可怜的,每年过年我们都请他来我家吃饺子。”
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关键问题:“你家西屋老少间里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周Sir眨巴了两下眼睛,流露出了无赖的眼神,冷冷地说:“我可以不说吗?”
我说:“不可以。”
然后,我转头看了看小马哥,开始请求后援。没想到小马哥说:“你咋管那么宽呢?周Sir,你把他撵出去。”
周Sir说:“算了,我也不瞒你们了,那里面有人。”
我马上绷紧了神经:“谁?”
周Sir说:“我媳妇他老爷们。”
我蒙了,转头看了看那几位,他们也瞪大了眼睛。周Sir说老少间里藏着大波浪的老公!
我大脑里马上闪过了一系列的猜测——他和大波浪是情人关系,他们两个人合伙把大波浪的老公囚禁在老少间里了,这里天高皇帝远,两个人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过上日子了
小马哥已经从炕上跳下来,惊讶地说:“大哥,你玩的有点大啊!”
周Sir说:“你们知道‘拉帮套’吗?”
我蒙了一下,马上就明白了。
“拉帮套”是东北农村早年间的一种风俗——家里男人得了重病,生活无法自理,更不能养家糊口,于是经夫妻双方协商同意,招个年轻的壮男人一起生活,就像一辆马车走不动了,再牵来一匹马帮忙拉套,晚上三个人睡在一铺炕上,形成一妻二夫的格局
没想到我竟然404真的碰到了这种事!
周Sir接着说:“他瘫了,常年躺在炕上起不来,吃饭喝水都要有人伺候。你们来了之后,我怕你们笑话,就让大波浪把老少间的门锁上了。我带你们去看看。”
我说:“不用了。”
Asa却走了过来:“不,要去看看。”
周Sir看了看他,马上解释说:“我们从来没有虐待过他,真的。”
Asa说:“看看就知道了。”
四爷很八卦地跳下炕来:“去看看去看看!”
我们跟随周Sir来到西屋,大波浪正在看电视,我看了下左上角的台标,奇形怪状的,竟然不认识。播的应该是个武侠剧,有个男的正挟着个女的在天上飞,整个画面又是磨皮又是柔光又是滤镜,整的跟假人似的,作为从业者我真的有点脸红。
周Sir说:“媳妇,我带他们见见他。”
大波浪一下有些紧张,她把电视关了,站了起来。
周Sir说:“钥匙。”
大波浪这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了周Sir,周Sir把门打开,那股香灰和中药混合的味道一下就变得呛鼻子了。
老少间的光线很暗,我勉强看清有铺小炕,炕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被子盖到了脖子下,只露出脑袋来,他的头发和胡子理得很干净,只是脸色白得吓人。我还注意到,他的枕头是个长方体,深色的,说不清是黑色还是深蓝色还是藏青色,总之很大,很高。枕头边上堆着很多药瓶,还有个玻璃杯子,里面是空的,不过杯子很干净。炕边有个桌子,上面供奉着一尊花花绿绿的神像,身体像水瓶那么大,还有个香炉,里面插着几根残香,香炉旁边放着一只很小的收音机。
这个人看到进来人了,把脑袋转了转,朝向了我们。
Asa先说话了:“你好。”
病人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些拘谨地说了声:“嗯”
Asa说:“我们是来串门的。”
病人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又说了声:“嗯。”然后就看周Sir。
周Sir大声说:“他们来看看你!”
病人说:“嗯,嗯哪。”
Asa站在了炕前,问:“你怎么样?”
病人“齁喽”了一声:“我挺好的。”
Asa说:“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可以跟我们说。”
病人艰难地摇摇头:“都挺好的。”
大波浪走进来,有些不耐烦地说:“老聂,你说话你大点声儿,别跟蚊子似的。”
我用余光注意到,周Sir瞪了她一眼。
那个老聂赶紧说:“我挺好的,谢谢领导关心”
说完还是看周Sir。
我觉得他不好,他说“挺好的”,“都挺好的”,“我挺好的”,越是这么说越可疑。
首先,他被锁在了老少间,说明他在这个家庭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就像我们来了客人,把一堆脏衣服胡乱塞进衣柜里。而且,他肯定被命令不许说话,不然我们不可能始终没发现他的存在,他要上厕所怎么办?
其次,他叫我们领导,说明他没见过404的领导,就是说没人来看望过他,他的一切都被周Sir和大波浪捏在手中。周Sir跟他甚至是一种特殊的情敌关系,不可能对他有多好,只能指望大波浪念及旧情来保护他了,但是,就算当着我们的面,大波浪对他的态度都这么粗暴,我们离开之后就更不好说了。
Asa突然凑近老聂说:“需要我们报警吗?”
这句话如同一枚炸弹,所有人都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