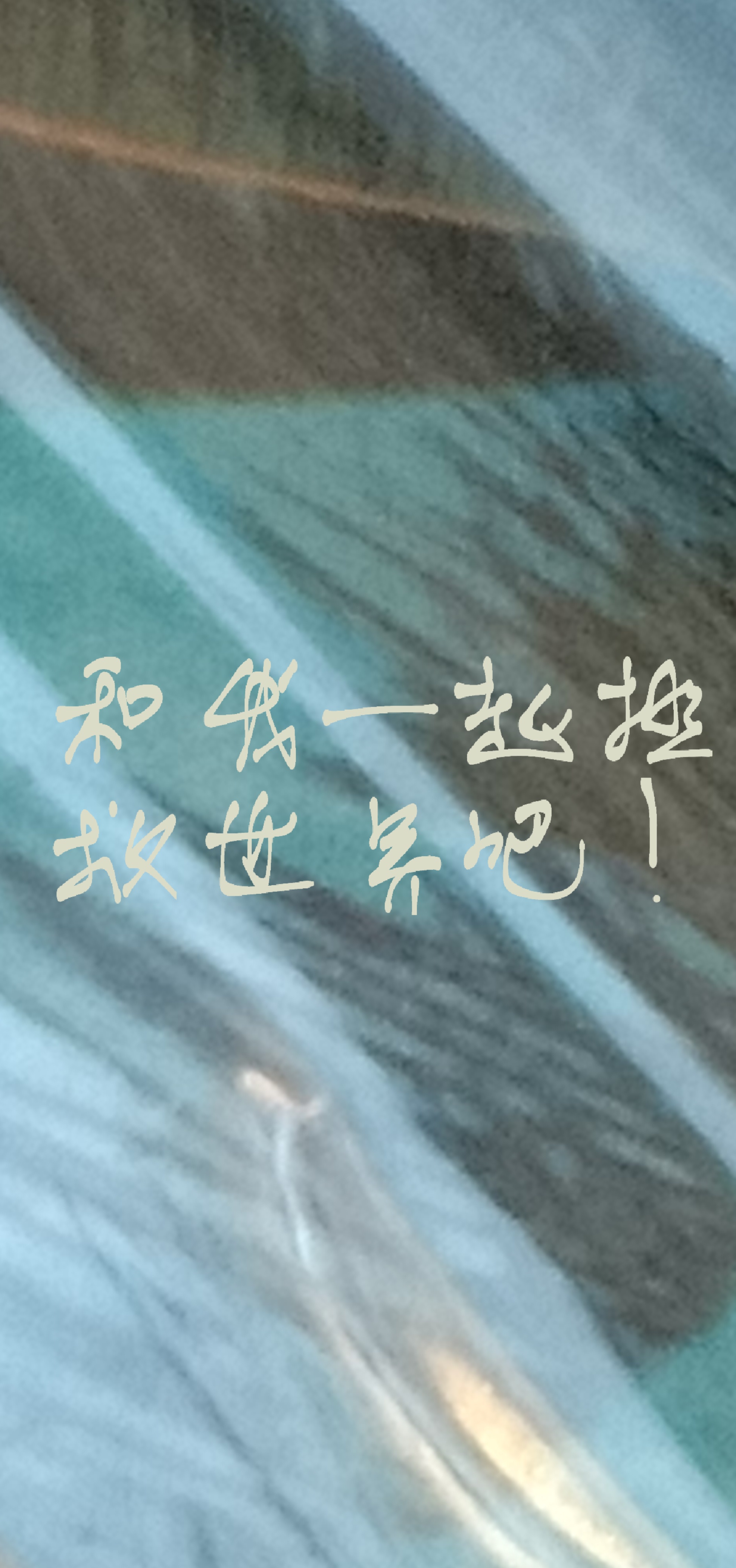我一下就爬了起来:“怎么了?”
Asa说:“他们来抓我们了!”
我愣愣地看着他:“谁?”
Asa说:“留守人员!”
我说:“你怎么知道?”
Asa急切地说:“我听见了无线电里的声音,我们属于非法闯入,办公大楼的人刚刚接到通知,正要过来抓我们!”
我还是不相信:“你每次听见的不都是过去的声音吗?”
Asa说:“这次是现在的!”
我说:“你确定?”
他转身回到他的床前,手忙脚乱地收拾起了行李:“你再废话我们就走不了了!”
我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把睡袋塞进旅行包,然后就跟着Asa跑了出去。我们刚刚来到走廊里,就听见楼下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上楼梯的时候,他们突然把脚步放轻了。
声控灯亮了,我和Asa只能躲进对面的厕所。
我从门缝儿朝外看了一眼,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正是那个光头,还有两个虎背熊腰的胖子,看上去有点像日本的相扑选手。
光头打了个手势,倒计时三二一,三个人一股脑地冲进了我们的房间。
一个声音传出来:“这俩小犊子蹽了!”
另一个声音说:“赶紧去撵!”
三个人又快步离开了。
世界一下变得魔幻起来。我睡着之前,世界一片祥和,一觉醒来之后,剧情突然变成了悬疑片
几分钟之后,Asa小声说:“赶紧下楼。”
当我们踉踉跄跄来到一楼的时候,却发现楼梯口那个金属收缩门被锁上了。
Asa靠在楼梯扶手上喃喃自语起来:“这可怎么办”
我盯着这个金属门,也没了主意,就算有管钳也不可能剪断它。
突然,收缩门外出现了一张脸,我和Asa同时朝后退了一步,此人正是邢开,他抓着栏杆,看着我们笑了:“你们梦游了?”
我赶紧揉了揉太阳穴,装作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我怎么会在这里?”
Asa马上东施效颦:“对啊,我怎么也在这里?”
谁梦游还成双成对的?
谁梦游还拎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
邢开又笑了:“可能是白天太累了,没事儿,回去接着睡吧。”
三个人就这么半真半假地对着话,谁都没有戳穿谁,我悄悄拽了Asa一下,然后返身朝楼上走去。走上几级台阶之后,我回头看了一眼,邢开站在栏杆外,还在对着我们微笑。
我们匆匆回到房间,用那个拖布顶住了门,然后关上灯,藏在了黑暗中。走廊里的光从门缝透进来,我的眼睛下意识地盯住了那里。
还没等我和Asa商量出对策,走廊里又响起了脚步声,那些人又返回来了!他们直接冲到门口推了推,没推开,接着就开始疯狂地砸门了。
我和Asa迅速钻进了床底下。
很快那些人就把门撞开了,他们冲进来,打开灯,四下看了看,接着那个光头就弯下腰,朝床底下看过来
床底下并没有人。
就像丧尸突然闻不到了活人的气息,光头变得很狂躁,他带着两个相扑选手在房间里乱翻起来。
我跟你们说,藏在窗户外面真的很累。
在他们冲进来之前,我和Asa从床底下钻出来,迅速从窗户爬了出去,虽然情势紧急,但我还是顺利地关上了窗户。一直倒霉的人总会幸运那么一次——窗户的栓杆生锈了,卡住了,可是就在我关上窗户的时候,它竟然自己插进了栓孔!没人能够从外面把窗户插上,果然,里面的人走到窗前看了一眼,接着他们就跑出去了。
这三个笨蛋也不想想,屋里没人,那个拖布为什么把门顶住了?
窗沿太窄了,我的两个前脚掌踩在它上面,脚跟是悬空的,我的手紧紧抓着旁边的排水管,一动不敢动Asa和我的姿势一样。
按照正常的建筑制式,一层楼大概三米高,我们现在等于悬在十五米的高空。我心里暗暗祈祷着,这根管子千万不要断啊。
我的姿势太别扭了,腿肚子开始哆嗦,马上就要达到了极限。我还尝到了一股血腥味,不知道刚才磕到哪儿了,我的牙龈出血了。
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样子,我根本就不敢朝下看。
Asa说:“我挺不住了”
我说:“挺不住也得挺啊。”
旁边有一个窗户里亮着灯,他们在看DVD,我甚至听到了台词——你跳啊!昭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你倒是跳啊!——这他妈是我妈最爱看的电影《追捕》
这种时候腿麻了才是最致命的,我慢慢蹲了一下,试图让血液保持畅通,Asa试了一下,但他刚刚撅起屁股就马上站直了。
气温好像越来越低了,我的鼻涕像水一样淌出来,我腾出一只手不停地蹭,很快我的人中就开始火辣辣地疼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惨过。
我抽了抽鼻子,眼睛就湿了。
DVD终于安静了,那个窗户随之也黑了。
我看了看手表,这才四点半,天亮还早呢。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但总觉得太阳出来之后好像一切事情都会得到解决。
解决?那时候更被动,留守人员会纷纷站在楼下朝上张望,有人说:他们变成了两只壁虎哎。有人说:要上去抓吗?有人说:我们已经抓住他们了啊。
我不敢有困意,时不时地晃晃脑袋。
此时此刻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就像在看一部地球史纪录片,我已经头昏脑涨了,但刚刚演到恐龙灭绝。
长夜如亘古。
幸好东北天亮得早,终于东边泛起了鱼肚白。
我和Asa都听到了一楼那个收缩门拉开的声音。
我说:“Asa,可以走了!”
Asa微弱地说:“你能打开窗户吗?”
我一只手抓着排水管,一只手掏出了瑞士军刀,打开开瓶器,夹在了食指和中指之间。这是一个混社会的朋友教我的,他说,如果你跟人打架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刻,身边又没有趁手的“兵器”,可以把钥匙串攥在手里,让尖头从指缝儿伸出来,这样就等于手上多了几个锐器,攻击力极强。但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自己也会被钥匙伤到。当时我还嘲笑他X-man,金刚狼,没想到今天我还真用上了这一招儿。
窗户上是玻璃砖,我对准它猛地一击,只是裂了,我的手指却传来了钻心的疼痛。开瓶器削掉了我食指和中指之间的一块肉,最开始没出血,甚至有点发白,几秒钟之后,鲜血才涌出来。
我又重复了三次这个动作,玻璃终于碎了。
我把手伸进去打开窗户,笨拙地爬了进去,又把Asa拽了进来,他刚刚进屋就坐在了地上。
还好,没人听到我们破窗的声音,整个办公大楼悄无声息,我和Asa赶紧跑下楼去。
当我们来到一楼的时候,一下刹住了车——邢开正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吃着早餐,他旁边的椅子上摆着几个包子,一碗豆腐脑,两个茶叶蛋,一碟咸菜。
他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笑盈盈地看着我们问:“这是要出去啊?”
好像我们夜里的经历只是一场梦。
我把受伤的手藏在了背后:“嗯,晨跑。”
他又问:“你朋友也晨跑?”
Asa说:“对。男男搭配,晨跑不累。”
他还在笑:“晨跑要背着行李?”
我说:“负重晨跑。”
他颇有深意地“哦”了一声,接着说:“刚才我听见楼上有响声,是不是你们的窗户被风吹碎了?”
我赶紧说:“我们也听见了,应该是别的房间。”
他说:“那你们快去吧,我看你们还挺急的。”
对啊,晨跑很急。
我和Asa始终没摸清这个邢开的心思,反正他没有阻拦我们,赶紧朝外走去。走到楼门口,我还斗胆停下来,回头问了他一句:“那个跟你合影的日本人还在吗?”
他说:“他天一亮就离开了。”
我说:“去拍照了?”
他说:“他离开404了。”
在影视剧里,只要出现一个可疑的线索,后来总会有个交代,但生活不一样,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李喷泉的那张地图是怎么回事了。
我说:“他还回来吗?”
邢开一边四下观望一边压低声音说:“还问?你们是不是等着被抓啊。”
我愣了一下,来不及说“谢谢”,赶紧拉着Asa走出了办公大楼,快步朝前走去,走出一段路之后,做贼心虚地回头看了看,并没人追上来。
我们不敢停留,一直在废弃的房屋之间奔走,直到走出两三公里,Asa才说:“歇一下”
我们靠在墙上大口喘气。
Asa说:“刚才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说:“他放了我们啊。”
Asa说:“那昨天夜里他为什么不帮我们?”
我说:“我估计他没有钥匙。”接着我又说了一句:“他就是我亲爹。”
这一带都是民居,尽管都搬空了,依然能看出每户人家的差异,有的主人很勤劳,红砖墙砌得整整齐齐,还有镂空的几何图案;有的人家就比较凑合,院墙是木头的,用铁丝拧在一起,高高低低,东北叫“板障子”。
我和Asa随便走进了一座空房,Asa打开行李箱,掏出睡袋铺在了火炕上:“不行了,我得睡会儿”然后就躺了上去。
老沪给我的急救包派上了用场,我蹲在地上,从包里拿出一瓶水,把手上的血迹冲了冲,然后用绷带缠起来。
包扎之后,我站起来看了看,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光线昏暗,靠墙有个柜子,已经摇摇欲倾了,立着一个脏兮兮的相框,里面是个女孩的照片,看上去十七八岁的样子,梳着一根马尾辫,有两个不明显的酒窝。相框旁边摆着一个矮墩墩的瓶子,那是雪花膏,早就风干了。
很显然,这是一个女孩的“闺房”。我忽然生出了贾宝玉一般的情怀,这个女孩离开的时候正值青春期,可是她的化妆品太简陋了如今她在哪里?年龄应该跟我妈一样大了吧?
Asa已经睡着了。
我也铺上睡袋,躺了上去。
我们在这个不知道谁家的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后来,我被手疼醒了。
城市的习惯很难彻底摆脱——起床先找手机。我拿起手机后,忽然反应过来,这里是封闭的,没有信号。我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了。
我昏昏沉沉地坐起来,转头看了看,Asa的睡袋空着,估计他出去遛弯了。
我走出去,看到了一个洗手池,水龙头都锈住了,没有一滴水,我只好拿出饮用水简单洗漱了一下,然后就走出了房门。在404就有这点好处,日不闭户,行李扔在哪儿都不担心被人偷走。
我围着这户人家转了转,没看到Asa,正准备进屋,突然传来了脚步声,我转头看去,Asa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女孩,那是四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