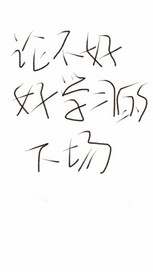丧葬方面,苏家村这一带有个十分诡异的风俗,那就是若是一个人没进家门前就咽气了的话,那么停灵就只能停在院子里,不能进屋,否则是不吉利的,后人会深受其害。
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苏润栀自然是不信这些的,也不会理会,奈何刘淑华现在信,苏怡华一直信,裘开符更是信的不得了,通过龚盈袖不停地向他传输这些“常识”。
短短时间内苏润栀就学到了好些以往根本不知道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倒像是经历了某种短期培训班,填鸭式的,不管你接不接受,反正他们只负责灌输。
你只需要记住并遵照执行就好。
当然,龚盈袖也不傻,知道苏润栀现在肯定心烦意乱,说这些他不喜欢的话稍不注意就会引发吵架和不合,于是也把事情做到了前头,这些常识也是顺带提出的。
这样一来,苏润栀倒是没有多反感。
死者为大,苏大山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和他们一家人永别,尊重他土生土长地方的风俗,也算是尊重他本人。
这一点,苏润栀并不反对,他也不是那种死板到底的人。
“老公,我怕你回去再准备这些来不及,所以就提前准备了。冰棺材也租了,一会儿运送的车会跟在你们后头。香蜡纸钱也全买了,他们是一家的。对了,红包我是提前给了的,到时候你不用管,不用给重了。我要照顾宝宝,暂时不跟着你去,过两天再回来。”
交代完这些,苏润栀便让开车离开,朝老家驶去。
因为简易氧气面罩的缘故,所以车开得不快,也早就说好了,若是人在车上去世,先前说好的三百块是不够的,需要另加红包,毕竟不吉利。
苏润栀一手按着氧气面罩使之与苏大山的面部贴合,一手略微用力有规律地挤压,使已经不能自主呼吸的苏大山能够吸到氧气,希望他能“挺过去”。
他都想好了,能坚持到家最好,万一不行,他也不可能真的完全按照习俗来:现在这天多热啊,要是停在院子里,后果简直不敢想。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不怕被拖累。
就这样,一直不敢停,这只手累了就换另一只手,手动给苏大山输氧气。当他两只手都开始抽筋的时候,他就看着苏大山紧闭的双眼和已经开始变色的脸,鼓励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这也是他这辈子能为活着的苏大山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哪怕再累也必须坚持,不能放弃。
刘淑华眼神空洞,全程不言不语,不哭不闹,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苏大山也是厉害,早就不能自主呼吸了,靠着这种简陋的设备一直坚持到下车,依旧没有咽下最后那口气。
跳下车,打开车门,在刘淑华的帮助下将苏大山背在背上,苏润栀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在心里暗暗说道,爸爸,儿子背你回家了,你要挺住啊!马上就到家了!
苏润栀背着人,刘淑华便主动接过简易氧气罩操作,二人配合着将苏大山背回了家。
堂屋里乱糟糟的,但也顾不着怎么收拾,时间要紧。
将苏大山放在他最爱的摇椅上,苏润栀和刘淑华快速地将堂屋里的东西搬空,又按照习俗取了几条长凳放上一个竹编的类似于凉席的东西,又在上面铺了一层白布。
外面,那些紧跟在后头的工人还在从车上往下面搬东西。冰棺材、香蜡纸钱等一应物事满满登登堆满了整个堂屋。
屋子刚收拾出来,苏润栀突然就听见苏大山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声响,意识到情况不对,苏大山可能要离开了,他将刘淑华立即唤了进来帮忙。
是的,苏大山咽气了,在回家十分钟后。
母子俩再次大哭,苏润栀跪着,刘淑华站着。
后来,村长就领着人来帮忙,院子里终于有了些人气。
阴阳老师也来了,让苏润栀提供全家人的生辰八字,翻翻书,写写画画,掐指算了一会儿,得出了一个让苏润栀无比震惊难以接受的出殡日子,七日后。
“老师,你能不能再算算,算个比较近的日子?你看这大热天的,停七天的话实在是有些久了……”
哪怕是冻在冰棺材里,人也早就硬了!算什么啊!
哪知那师傅两眼一瞪,对苏润栀的质疑十分不满。
“听我的还是听你的!这是按照他的八字和你们家的情况算出来的,根本就不能改!你自己看,他属鸡,你也属鸡,你妈属……不信你就去问别人,我可没乱说!要是乱改,以后你们家有什么不顺可怪不着我。”
苏润栀还没来得及反驳,他又说话了,因为他看见刘淑华了:他和刘淑华的亲妈也就是苏润栀的外婆算是旧相识,住的地方离得不是很远。
“诶,你们姐妹三个,没一个遗传到你妈妈的美貌,真是可惜。你们啊,一个个都是宽皮大脸,身量矮小,长得像你爸爸。”
苏润栀:……
不是说自己业务很精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简直是什么鬼!
算完之后就是装殓,先是穿衣服,苏润栀和他赶来帮忙的二姨亲自给苏大山穿的衣服,不知道为什么,摸到苏大山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怕,反而十分平静。
他原以为自己会很害怕的。
等所有事宜做完,他那脸大的亲戚、竹林的拥有者也来了,全程不说话,低头自觉地帮着忙上忙下。
苏润栀原以为自己会情绪失控,会不管不顾地找他拼命,要他把苏大山的命还来,又或者让他出去,不许他帮忙。但是,他啥也没做,就像没看见一样,随他去了。
有时候,忽视和自责才是最好的惩罚。
再说了,苏大山已经走了,大哭大闹不是他的风格,也没有任何意义,何苦呢!
接下来便是接待亲戚,来一个,烧纸上香,苏润栀便跪着还礼,大半天下来,也不知道递了多少次香,跪了多少次,他的腿都麻木了。
但也没办法,现在谁也帮不了他。
苏怡华倒是想来,但刚做了手术,还在医院里躺着,等待那个或好或坏的结局。
晚上倒是安静,亲戚们全走了,留下刘淑华和苏润栀母子俩在家。让刘淑华吃了药就去睡觉,苏润栀跪在那里守灵,陪着寂寞的苏大山。
他是真的恨那个阴阳老师,明明两三天就可以出殡的,非要这样整治他们家,足足算了个七天出来。
第二天,苏润栀跟村长抱怨了一番,村长一听,就给他指点了一番,说包括棺材和香蜡纸钱什么的都不该在城里买,而是应该把这笔生意交给阴阳老师,让人家也赚一笔。
现在,他赚不到这笔钱,自然是要出气的。
苏润栀这才明白个中缘由,只是,心里到底是不平的。这个阴阳老师也实在是没什么职业道德,又小气。幸好不是当官的,否则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就这样,足足等了七日。
期间,龚盈袖来帮过几次忙,帮着做饭,招呼亲戚什么的,直到出殡前一晚,亲戚们都来了,连裘开符和龚庆慈也来了,抱着千言给苏大山磕头,祈求他保佑千言健健康康,无病无疾。
最后一夜了,按照风俗还要请一个类似于乐队的团队热闹热闹,但苏润栀讨厌这种形式和俗套,特别是那种又唱又跳的,他真的看不惯。
唱给谁听?跳给谁看?
第二日便是出殡的日子,通过这十多天的消费,苏润栀只觉得自己已经麻木了。喊他跪就跪,喊他摔就摔,喊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仿佛行尸走肉。
末了就是吃酒席,他原本不想去敬酒的,但龚盈袖硬是拉着他一桌一桌的敬,每桌留下一两包烟,说是最近一段时间麻烦大家了,以后虽然不在这里住,但也会经常回来看看,大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可以找她。
一番敬酒下来,人人都说苏润栀运气好,娶了个会来事的城里婆娘,以他自己那样木讷的性子,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可苏润栀心里是有些生气的。
一是大家都笑意盈盈的,一边吃一边聊,只有他和刘淑华满脸悲伤,暂时还走不出来,忽地就想到了那首诗。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二是苏大山一咽气,苏家就发生了一件怪事,他们家用了多年的水井突然干涸,一滴水都抽不上来,连泥浆都没有。这样一来,便只能去邻居家要水。
要水可以啊,但要给红包,毕竟这是白事。
前几日家里只有母子两人,于是一般要两三桶水,但一样要给红包,前前后后下来,苏润栀都不记得自己到底给了多少红包出去,至少得有两三百。
这样的人,他不想与之打交道。
既然苏大山走了,以后刘淑华便只能跟他们住在城里。既然这样,他也几乎不会回来这个伤心地了。
他在这里悲伤,苏怡华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几日哭了太多,仿佛要把这辈子的眼泪流干。
特别是今天早上,她知道这是苏大山出殡的日子。
他那么爱她,她却回不去见他最后一面。
手术很成功,切面干净齐整,也就是说,病变的部位是切干净了的。只是,病理结果要下午才能出来。
“好了,躺着好好休息,不要跪着了,爸爸是不会怪你的。他那么爱你,会保佑你平平安安的。你好好活着,就是对他最大的孝顺,你说是不是!”
一边收拾一边劝慰苏怡华,许利心里也不是滋味。
不过短短十多天时间,苏许两家就发生了这么多事,真的是难以预料。
苏怡华觉得自己已经哭不出来了,呆呆的任由许利办完了所有手续,就等着拿检查报告了。
报告一天不出,她一天也难安心。
不知道是不是苏大山真的在保佑她,下午的报告显示一切正常,关键是没有浸润,也就是说,她彻底解脱了。
“爸,爸爸,谢谢你保佑我,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你保佑我的。谢谢爸爸,谢谢爸爸,我好了就回去看你。”
许利却道,“是要谢谢爸爸,但我觉得也要谢谢那孩子。”
那个被他俩选择流掉的孩子。
他来的不是时候,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提醒了苏怡华她的身体正在发生病变。由于警醒的很及时,所以才能一切顺利。
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自己的妈妈。
无论是苏大山还是他,终究是永永远远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