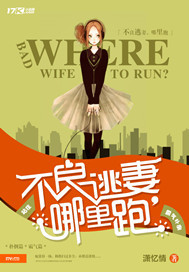记不清,在昏睡中度过了几日,醒来,再无睡意。
“怎么会这样?”
一连几日被无数液体洗涤过的身体,每一寸血管,都流淌着知名或不知名的化学品,人们称之为:药。
她记得,有人说过:应病与药,令得服从。意思是对症下药,对凡人可用,用在佛语中,是用尽心思说教人心的意思。
有那么一个人,他说的话,正如药,她每一个毛孔,都在吸纳,从耳朵到心灵。
可是,“那人,是谁?”
记不起。
……
傍晚,南城,东区别墅南城院子。
一女子,在路旁的桂花树下徘徊,“空山寻桂树,折香思故人”,手捧花枝,在四季常青的桂花树下,一抹红裙飞扬。
她皮肤白皙,容貌俏皮,因瘦骨嶙峋,吸引路过的人频频侧目。
“美女,坐车吗?”
超跑里的年轻小伙探出头,半开玩笑地询问,他并不打算在中秋夜,搭上一位病恹恹的女人,即使她容貌清丽,也只能是他闲来无聊的取笑。
女子应该是在寻家,没有一路查看门牌号,甚至对这里的一切并不关心,只是边走边闻花枝,傻笑。
“不用,我到家了。”声音平静,点点喜悦。
亮黄超跑从坡道飞速离开,一阵风,掀起她的裙角,她按住裙摆,背过身去,如花舞。
南城院子,按照古时南城大户的样子,打造的一座座别墅,乍看整整齐齐千篇一律,其实独门独户,各有千秋,都体现在了细节之上。
她要寻的,便是桂花树尽头的那户人家。
农历八月,月圆之夕,月上桂花,飘香人间。南城最浓郁的芬芳,在这里。
她偷偷溜进小路,从园林小径往上,爬过十九级台阶,立在台阶之上,正对大门。
过条车道,就是家。
头发丝满是树上飘落的桂花,带着花香回家,赶赴团圆。
“美妈,我回来了。”
她在喊沈美兰,可屋子里没有灯光,大门紧闭,无人应声。
一只乌鸦从屋顶一角起飞……“哇,哇”两声,粗劣嘶哑。
这里怎么会有B城才有的鸟畜?
她疑惑,后退两步,对空荡荡的院子里喊,“美妈,美爸,哥,你们在……”
刹那,两道刺眼的白光照射过来,灯光下拉长的身影,从阶梯上滚落。
“米然……”拉长的声嘶力竭,驾驶位冲出来的男人快步跑下台阶,长腿迈了不足十下,就到了台阶底层。
最老的桂花树下,红群女子,眼眸微闭,嘴角倾出血,鼻孔微微张合,闻着花香。
男人身形修长挺拔,此刻却弯了腰,越是接近,越是下弯,如迟暮老人直不起身,最后虚弱无力跪倒在侧。
“哥……我只吃桂花味的……”
唤出的时候,李米然眼角有泪滑落,此刻,她也要他记住……有个女孩,八九岁的年纪,蹲在桂花树下,用裙子兜住飘落的桂花,缠着美妈做南城特色的桂花月饼,她的景恩哥哥会躲在墙脚笑她,“跟馒头似的,有什么好吃?!”“我喜欢!我喜欢,我就喜欢!”女孩甩着小辫儿,用小手将比自己高一个头的哥哥推出厨房。
“米然……米然……”
男人心急如焚,逼迫自己的声线一如往昔,只是心被焚毁瓦解,烈焰灼伤到喉咙,哑然失声。
“可是,我不会……再……喜欢了。”
因为,我早就没了心!没了你,喜欢不了任何人。
摔倒,记起!一个是身体的伤,一个是心里的痛。没有心就好了,那样便不痛,亦不会受伤。
心上有洞,被人用钉子钉住,开始的时候,是在心上缝缝补补,可当一颗颗钉进去,心上满是洞,密密麻麻,都是被人凿的。
钉子敲敲打打的声音,让李米然害怕地眨了眨眼睛,即合不上,也睁不开。
合上,她再也看不到桂花树,睁开,眼前的人夺走过她的希望。
应病与药,用在她身上,如今,却毫无价值,治不了身,也治不了心。
“哥,你看……药都救……救不了我,你真……真失……败!”
学了十年医药的男人,最年轻的药学家,正抱着嫌弃他没用的女子,飞奔,奔向那片柚子树大街的方向,那里有无数生命的欢声笑语,更有无尽生灵的悲苦怜悯。
才25岁而已,你要他能有多成功?仅仅是学药的而已,他岂会不终之药。
“我救不了你,会有人可以,你要活着!活着!”
于景恩坐在车后座,抱着怀里的李米然,有种东西在慢慢消逝,慢慢,慢慢……
……
大学毕业那年,李米然22岁,她给哥哥打越洋电话,告诉他毕业论文通过,预示着她可以顺利毕业了。
电话听筒里,有个男声对她说:“再等一个月,我们在美国团聚,再也不分开。”
后来呢?后来的事,李米然不知道。
她又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