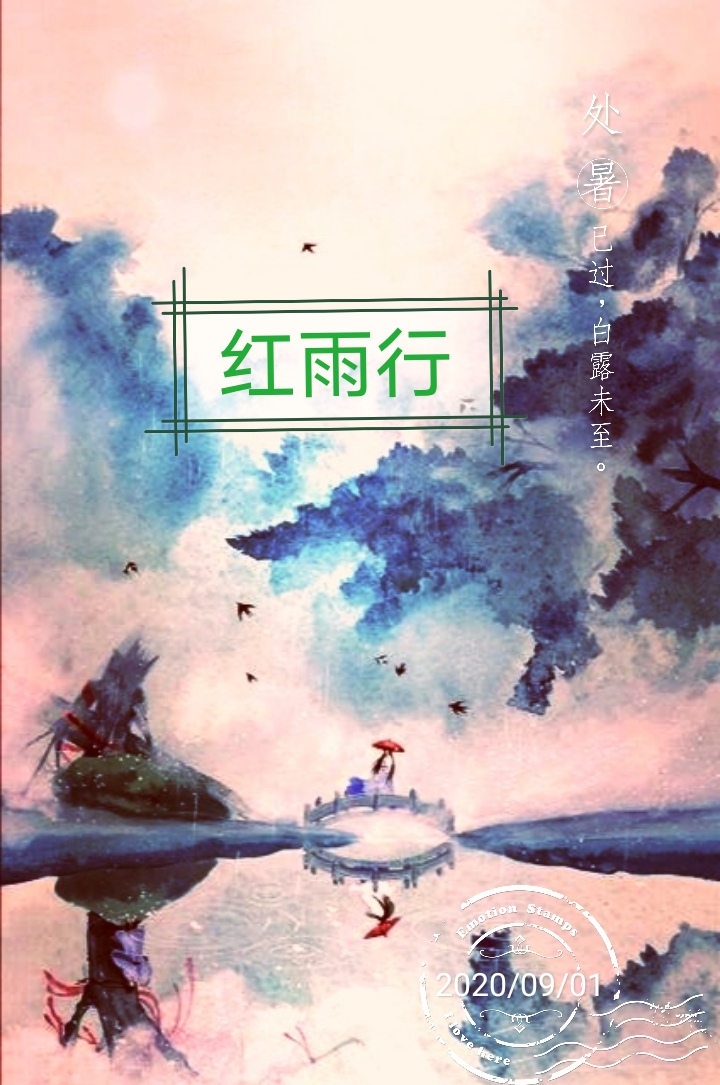新科状元何来走至半路时,皇上赵构突然紧急召他入宫。
何所惧一家人面面相觑,吕静自然不认得何所惧等人,只是客套的留两一顿饭。何所惧心里明白缘由,多说无益,只得找了由头先在临安住下,日后再做打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吕妍不得不先独自前往何来家中。
吕静见到七妹吕妍,又惊又喜。惊的是吕妍竟然放下身段甘愿做小,喜的是姐妹重逢,至于丈夫如何想法,一切等他回来再做定夺。两姐妹秉烛夜谈,直至拂晓。
却说金兵来犯,赵构吓破了胆。听闻朝中大臣秘奏,听闻平江府歌舞升平,一派繁华景象,便下了圣旨,封何来为国公,让他在平江府修建行宫,自己却在海上东躲西藏,四处逃窜。
平江府虽有所好转,但金军四处游弋,大有卷土重来之意。在这当前形势下,皇上却下了这道糊涂圣旨,让何来大为恼火。
工程迟迟不得开工,东躲西藏的皇上大为不满,遂召国公至江陵府面圣,后以抗旨罪名,将其押入大牢。
听闻丈夫面临牢狱之灾,此时,吕静已生产,育有一子两女,便带着吕妍、小翠和小红转移至平江府落脚,将她们安顿好,自己以国公夫人身份进宫面圣。
一番唇枪舌战,皇上大为不悦,吕静聪慧绝顶,洞察到他的想法,于是说道:“臣妾乃一介女流,只知相夫教子,不懂朝政。子无父,不成父子,妻无夫,不成夫妻。望皇上开恩,看在国公守护平江府有功放臣妾丈夫回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赵构冷冷说道:“有功之臣难道就可抗旨么?”
“皇上,金军占我国土,抢取豪夺,当下首要任务便是将金军赶出我大宋!行宫可建,但尚不在此时。平江府免遭金军涂炭,全仰仗国公治军有方。皇上非但不论功行赏,却将有功之臣关入大牢,焉有其理?”
“大胆!”童贯闻言大怒,“国公身怀武艺,统领四方,野心勃勃,实为大宋之患也!此人不除,大宋不得安宁!”
面对着莫须有的罪名,吕静冷冷一笑,丝毫不见畏惧之意。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若是皇上不放了自己的丈夫,那么只有劫持皇上这一条路可走。面对赵构的恼羞成怒,她环顾四周大臣,撇出一抹嘲笑,挺起胸膛,义正辞严的为自己的丈夫辩护:
国公博古通今,满腹经纶,才也;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德也。才德兼备尚未得赏识,几经贬谪,焉不是擢人者不公耶?况以国公之才德尚且如此,况余之辈乎!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历朝从文者皆羡入仕为官,独国公孤身入叛军以明志,其胆识焉能不敬哉!然,今既赋闲,言众而不闻,文奇而不纳,报国无门,身陷大牢,遑论知人善任哉!古语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谓之齐家方可治国,国公若无庇妻儿之能,焉能报效朝廷、铲除奸佞?
——好个巧舌如簧的吕静!
童贯暗吃一惊,见皇上被说得哑口无言,遂附耳几句,皇上吃惊的看了他一眼,心中似乎颇为犹豫。
“皇上,若国公成了气候,到那时怕悔之晚矣。若与完颜洪烈言和,此两人必先除之。皇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皇上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忽而说道:“言之有理!国公乃功臣,怎可关入大牢?”遂赦免国公抗旨之罪,同时下令赐御酒。
皇帝态度突变让柳诗妍始料未及,又见他与童贯窃窃私语,心道这御酒恐怕是杯毒酒,暂时也不动声色。何来上得金殿,见到妻子,又惊又喜,不顾旁人在场将她紧紧拥在怀里。
“让娘子担心,为夫之过也。”
吕静上上下下将丈夫打量一番,确认无恙这才露出一丝微笑。这时,御酒端上来了。
吕静冲着丈夫眨了眨眼,何来心领神会,谢过皇上恩典,一饮而尽。吕静见状,同样饮之。再次谢过皇上之后,夫妻俩正要退出,却听童贯叫道:“要到哪里去?”
何来答道:“回相公,回家。”
“可知家在何处?”
“临安。”
童贯大笑着摇了摇头,道:“坟墓便是你们的家!”
何来一听,脸色一变,突然捂住腹部大叫一声翻滚在地上,吕静正要去扶持,亦秀眉一皱,俯身蹲地,似乎疼痛不已。
“此毒名曰‘玉石俱焚’,中毒者三步之内五脏六腑俱碎,剧毒无比,天下无解!”
何来有气无力的说道:“我对皇上忠心耿耿,为何加害于我?”
童贯道:“你暗中勾结草寇,会同武林中人欲在慕容山庄密谋造反,你当皇上不知?平江府一战明明可以生擒完颜宗翰,却故意放他逃走安的是何居心?你的野心恐怕不是对付金军,而是我大宋罢?”
“你血口喷人,栽赃嫁祸!”
童贯冷笑道:“你若不死,皇上一日便不得安心。不过你放心,你俩死后,皇上一定会风光大葬!”
“多谢告知!”
突然何来弹地而起,双掌齐出,拍死了护在童贯身前的侍卫,一把抓住他高举过头,大喝一声:“若敢上前,我便摔死他!”
皇上大怒:“大胆!你敢威胁朝廷重臣,罪该万死!”
吕静忽而一个飞跃,众人只觉眼前一花,她便已经扣住了皇上的咽喉,大喝道:“真是昏君!国公一心护你,保护大宋忠心耿耿,你却恩将仇报!若非我事先识破,我夫妻俩岂非被你毒死了?护我夫妻出城,饶你不死,如若不然,便让你脑浆涂地!”
皇上被抓,非同小可。
一瞬间,守卫将二人团团围住。夫妻俩一个挟持着童贯,一个挟持着皇上出了皇宫,出了南门。
“出城了……可以……放了朕吧……”皇上吓得哆哆嗦嗦。
吕静怒道:“你若循规蹈矩,我不会为难你。你且听好,若是害我家人,枉杀忠臣,我便一剑杀了你!前有武则天称帝,今有我吕静称王!你若无情,休怪我无义!”
说罢,一掌拍晕了赵构,骑马扬长而去。皇上醒来,生了一场大病,直到数月方才有所缓解,自然这是后话。却说童贯恼羞成怒,下了重金要何来和吕静的项上人头。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日,何来夫妇寻到一间靠河边的客栈,要了两碗面正吃着,忽然眼前一花,吕静下意识的将丈夫一推,“夺”的一声,一把飞刀深深的扎进了桌子上。与此同时,三个蒙面人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吕静道:“你是何人,报上名来,为何要行刺?”
蒙面人甲冷冷一笑:“杀了你们,黄金万两,如今这世道,有这买卖算不错了!”
何来道:“想必是童贯花了重金请来的杀手吧?”
蒙面人甲冷哼一声,道:“将死之人,何必多问!”
说罢,这个蒙面人朝着吕静当头就是一刀劈下!另外两个一前一后将何来与吕静隔开。
只见吕静或前或后,忽左忽右,时而莲步轻移,时而侧身舒展,有时翩翩起舞美若天仙,有时从天而降快若闪电,她像一个优美的武者,像是在跳着一曲闻所未闻的舞蹈。
蒙面人虽然攻势凌厉,却始终不曾沾得她分毫,不由暗自吃惊,吕静何时武艺这般超群?原本以为只是一介女流,今日一见居然身怀绝技,当下也不敢大意,打起精神来,毕竟,那赏金还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
蒙面人大喝一声,卷起朵朵刀光,犹如大海中的波涛,汹涌澎湃的朝她席卷而来,方圆三丈之内折花断树飞沙走石,内功深厚,其势威不可挡。
却见吕静云袖轻摆招蝶舞,纤腰慢拧飘丝绦,随着柳玉芙的出招舞动曼妙身姿, 时而似一只蝴蝶翩翩飞舞,时而又似一片落叶空中摇曳,忽而又似丛中的一束花随着风的节奏扭动腰肢绽放自己的光彩,无论蒙面人的招式如何凌厉风行,她始终面带微笑妩媚动人,连裙摆都荡漾成一朵风中芙蕖,那长长的黑发在风中凌乱,美得让人疑是嫦娥仙子。
——这哪里是武功,分明是在跳舞!
——不,这不是跳舞,这就是武功!
何来明的暗的一齐下手,不论白的黑的,放倒这两个人是目标。那两个蒙面人论武艺与方羽不相上下,可要是论起暗器耍诈,那可与方羽相差太远,不消多时,只听两声惨叫倒在地上,两人都咽喉处插了两根筷子。
再看吕静,场中,那蒙面人虽然攻势凌厉,但得势不得分,而吕静虽然看上去凶险异常,但险而不危,甚至有点闲庭信步独赏月色美景的潇洒。
忽而蒙面人一声:“倒!”一个横扫千军快若闪电欲将吕静一刀砍下头颅。只见她双手撑地反身下腰,险险躲过这迅疾的一刀,儿在躲过的同时,玉足轻抬,在刀背让微微一运力——
蒙面人收刀不及,只听“咔擦”一声,刀锋深深的嵌入了他的脖颈,他把自己杀死了。
“妙哉!”真是精妙绝伦!”何来由衷赞叹,这一招,可以看出吕静的腰部具有十分的柔韧度,而且眼光颇准,稍微提早一些,遭殃的怕是她的脚了。
“妾身感激官人教我武艺,如今终于有用武之地。”说罢,吕静深深作了一揖。
“学武本为防身,娘子是否安好?”
“一切都好。”吕静拍拍手,整了整有些凌乱的衣衫。远远躲在远处观望的客栈小二看得早已惊呆了。
何来怔怔的望着妻子,只见她身着一身蓝色的翠烟衫,散花水雾绿草百褶裙,身披淡蓝色的翠水薄烟纱,内穿薄如蝉翼的胸衣,双峰圆挺,肩若削成,腰若约素,肌若凝脂,气若幽兰,眸含春水,清波流盼。香娇玉嫩秀靥艳比花娇,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一颦一笑动人心魂,生过孩子的她更显身段诱人。
“官人为何发愣?”
“好久未见,娘子身段真美。”
吕静轻轻的将一缕发丝掠至脑后,乌黑如泉的长发在雪白的指间滑动,一络络的盘成发髻,玉钗松松簪起,再插上一枝金步摇,长长的珠饰颤颤垂下,在鬓间摇曳,眉不描而黛,肤无需敷粉便白腻如脂,唇绛一抿,嫣如丹果,珊瑚链与红玉镯在腕间比划着,白的如雪,红的如火,慑人目的鲜艳,翠色的丝带腰间一系,顿显那袅娜的身段,冲着丈夫嫣然一笑,坐在何来身后,紧紧搂着他的腰,将头枕在他的背上,万种风情尽生,两人绝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