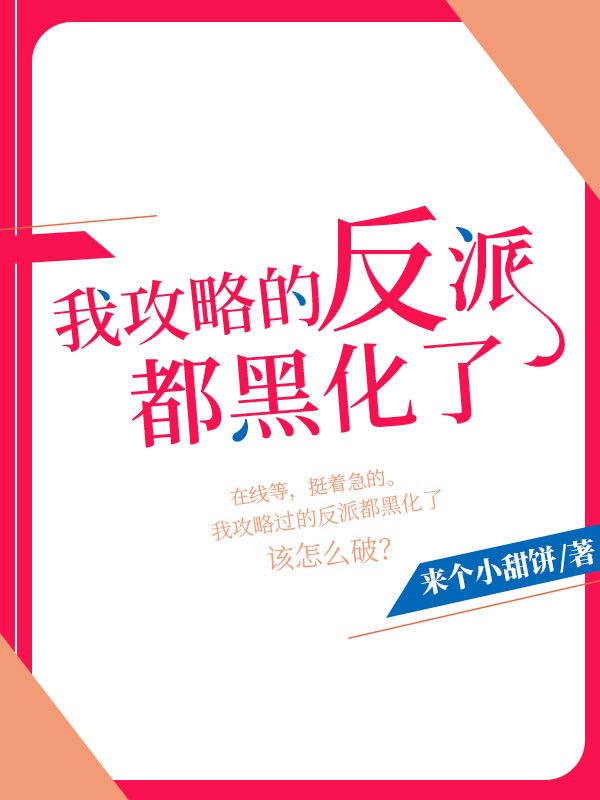“杀人了!杀人了!救命啊!救命!”
无名村外,夜色弥漫的林荫小道上,一名中年男人冒着倾盆大雨连滚带爬地嘶吼着,一边跑一边不住地看向后面,像是有什么凶恶的猛兽尾随着他,要将他一口吞噬。
手电筒那弱的可怜的光在他一路的颠簸和不住的颤抖下耗尽了最后的电量,灭了。四周陷入一片黑暗,连那皎洁的月也不愿多分享出一些光亮给他。
男人粗糙的大手笨拙地寻到手电的开关,以极快的速度按了一下又一下,那救命的光终是没有亮起。
小路分叉处,一个瘦小的身影轻巧地从树上落下,正好落在男人面前触手可及之处。
黑暗中男人看不清,一躲闪却猛地撞到了树上去。正头昏脑涨时,听得耳边传来一声淡漠的嘲讽,“吵死了。”
伴随两声尖锐金属刺破血肉的声音,男人腹部留下了一个黑色的血洞。洞中,涌出的却不是鲜血。
男人跌坐在泥水里,颤抖着用双手捂住腹部,面目几近变形。雨水缭乱地拍打在他惨白的脸上,顺着面颊流进嘴里,咕嘟咕嘟呛了好几口冰冷的水。
他挣扎着跪在地上,用早已不成调的声音磕磕巴巴地哀求道:“放过我吧,求求你,放过我吧。”
“想得美。”
站在男人对面的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她姣好的面容上,一道渗着血的伤口触目惊心,从左侧眼角一直划到了耳廓。姑娘抬起手臂潇洒地拭去脸颊上的血水,再次举起了那把泛着寒光的匕首。
“我,我不……啊!”男人话还未说完,女孩一刀狠狠刺进他的喉咙。瞬时,几点火花迸出撩着了男人卫衣的领子,几簇幼小的火苗只跃动了一瞬便被大雨浇灭。
男人瞪着眼睛不由自主地往后仰倒,僵硬得直直向后跌下,身体重重砸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溅起一片污浊的泥水。一双充满恐惧的眼睛呆滞地望着天空。
死不瞑目。
女孩蹲在男人的尸体边,拽起他衣服的一角擦了擦手中的匕首。接着,她戴上一只黑色绝缘手套迅速从男人腹部的伤口里掰出一块块墨绿色的芯片,甩甩水放进口袋。
撂下男人,女孩独自走到不远处的一株小树下。它没有多少叶子,但长得还算挺拔。那下面,埋着她的弟弟。她唯一的亲人。
女孩姓云,名遥。她的弟弟叫云昱。
其实两人并不是亲姐弟,只是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都成了孤儿,一直在孤儿院里长大。直到有一天,一对自称乡下来的夫妻领养了他们,他们才一起来到这个深山里的无名村生活。
好在这对夫妻为人和善,二人也度过了不少快乐的时光。到了上学的年纪,这对夫妻还送云遥去城市上学。
不过上天似乎对给予他们姐弟两人一些快乐的时光这一点极为吝啬。三年之后的一场火灾,夫妻二人命丧火场。
年仅十二岁的云遥拼命带着弟弟从火场中跑了出来。两人性命虽是无碍,可惜弟弟不幸毁容,原本白嫩的脸上留下了一大块狰狞的疤痕,连视力也受到了影响。
那天之后,他们就又成了被孤立的存在。村里人人都说他们是扫把星,谁搭理谁家就倒霉。
为了筹备养父母的后事、养活弟弟以及修复他脸上的疤,云遥选择继续在城市学习。课余时间去打工,兼职……总而言之,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挣钱。但无论再怎么忙,她也会每个周末抽出时间回到乡下照顾弟弟,也给他讲讲外面的世界。
无名村还有那对夫妻留下来的一幢小屋和一些生活用品。云昱到了上学的年龄但不想去城市读书——他的脸实在是惨不忍睹。云昱想,与其出去吓人,不如呆在家里。
知道他的顾虑,云遥也就让他留下来照看这些……算是回忆吧。
为了筹集云昱的手术费,云遥用了几年的时间兼顾学业的同时四处奔波,终于如愿积攒到了足够的收入。手术这不就有着落了吗!
拿到足够的钱之后云遥向学校请了假期,想着早些回去看弟弟,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
这次终于可以让弟弟做手术了!他再也不用一直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或是一年四季戴着口罩才敢出门了!他终于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了!
可不幸的是,一场临时的突发情况让云遥不得不暂缓回去的计划。也正是这场突发情况使云遥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了四天。所以,这周末云遥没能回去。
这可把云昱急坏了!他知道姐姐一定不会无缘无故不回来的,一定是出了事才会这样。四天的时间,他给姐姐打了足有三百多个电话,手机里传来的无一例外都是那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时候,云昱曾在养父母的深夜谈话中偷听到,姐姐和他是不一样的。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但姐姐不是。姐姐有着更隐匿的身份和更沉重的未来,至亲分离不再相见实属无奈之举。
这样不辞而别的状况在之前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姐姐中考结束后的暑假。云昱深知如果像上次姐姐她们去广西那样……后果不可估量。因为那次广西之行,姐姐回来时几乎只剩下半条命了。
可他一个未上过学的年仅十四岁的孩子,在这荒郊之中能干什么呢?
纠结再三,云昱决定带上家里所有的积蓄到学校找姐姐。毕竟放在家里不安全。姐姐说过,他们生活的这个村子,有很大的问题。
想到便做,他独自背上装有家里所有现金的黑色书包来到了村子几里外唯一的那个火车站。
火车站人来人往,谁都没有注意到身材矮小还裹得特别严实的云昱,以至于一名男子过路时不小心撞到了他。云昱跌倒在地上,不大结实的书包划到了墙壁转角上突出的铁片,一堆钞票散落出来。
云昱哪里顾得上疼,马上爬起来把钱往书包里装。
这位叔叔是他的邻居,以前养父母还在的时候他还曾受邀去过这位叔叔家摘果子玩。男人也认出了云昱,连忙蹲下将地上的钱捡起来塞给云昱。
云昱没有抬头,一边捡钱一边不住地道:“谢谢,谢谢叔叔。”
“没事没事,叔叔我也……”话还没说完,又一大批乘客要进来乘车。大厅的门被一下子挤开,站外刺骨的寒风直冲而入,刹那间卷起满厅红得刺眼的百元大钞。
其实云昱手里的钱并不多,可是钞票被风吹起后满车站地肆意飘飞给人在视觉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穷乡僻壤的弹丸之地哪里见过这么多钱!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直愣愣看着空中还在盘旋的满天钞票。
那一刻似乎所有人都没意识到这天上飞的红红的纸片是什么,只是觉得看这些玩意儿飘来飘去的好像还挺好看。但,仅仅过了几秒之后——很小的一声,“捡呀!钱!”
这一句话的声音虽小,却起了很大的带头作用。一瞬间,整个大厅的人都开始疯狂地捡那些钞票往自己口袋、书包里塞。
云昱身旁的叔叔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只剩云昱独自在车站里奔跑,一边和他们抢一边撕心裂肺的大哭大喊,“不要抢!是我的!求你们了!别抢啊!”
一阵风卷残云之后,大厅安静了下来,像是刚才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人悠闲自若的喝水,有人微笑着打电话,有人招呼后面走得慢跟不上脚步的老年人……
云昱痴痴的看着车站里的光景。
他傻了。
不知道说什么,可看着眼前的一切,感觉一切都是假的,像是做了个噩梦。可当他低头看到手里所剩无几的钞票,他又知道,这是真的。
他们……他们怎么能……面不改色……
隐约间,他听到姐姐在喊他。抬起头来,却是泪水迷蒙了眼眶,什么都看不清。眼前的世界蒙上了散不去的阴霾。
他记得,姐姐给他讲的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那么多寂寞难言的晚上,他曾无数次的幻想过姐姐讲述的那些万里星空、明媚山河究竟是怎样的动人心魄,那些奇岩巧树、浩野千里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秘密。他幻想过与这个世界的种种相遇,独独没有料到是这样的结果。
“对不起,姐姐……我对不起你,我……”云昱把自己缩的小小的,躲在垃圾桶旁泣不成声。
拐角处,离云昱很近的地方,一对母女小声地交谈着。
小女孩看着妈妈将几张钱往背包里装,问道:“妈妈,我们捡这些钱会不会不好啊,这不是我们的啊。”
女孩的妈妈拿手里还未装进去的钞票敲了敲女孩的头,“嘘——你小声点,懂什么。”
云昱似乎被“小声点”这三个字刺激到了。他猛地抹了把眼泪拽下口罩和帽子,站起来用尽所有的力气从喉咙最深处发音,冲那对母女喊:“还给我!”
这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把车站里所有的人都喊懵了。
不知是不是被他狰狞的脸吓到,小女孩一下子大哭起来。那位母亲一把捂住小女孩的嘴,呆呆的看着云昱的脸。
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吓人的人。
静默的氛围几乎是以光速传播至了车站的各个角落……
云昱不知道最后他是怎么回家去的。之后那一段记忆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无论怎么回忆都想不起来。那一整天他都过得浑浑噩噩,自己都反应不过来自己在做什么。等他觉察到的时候,已经是满身伤疤,满屋血渍。
“姐姐,我是不是疯了。”
一整天了,他什么都没吃。云昱翻出半块干冷的馒头就着水慢慢的嚼。他没有开灯,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门后,手里依旧抱着那件破损的黑色书包。包里,是少的可怜的钞票。
丢了,什么都丢了。
云昱把额头贴在冰冷的墙上试图让自己回忆起早上的事,他不认为自己有自残的倾向,他想知道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可一切都是徒劳,几分钟后,云昱沉沉地睡去。
门外,早已等候多时的邻居薛叔叔进入房间,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火车站的事已经传遍了周围好几个村庄,只不过被有心人利用之后是非早已倒戈。在这传言之下,云昱成了小偷。
没有人能解释一个深山里的孩子怎会有那么多钱,又拿着大把的现金慌慌张张出现在火车站。
这一夜的屋外。不知多少的流言蜚语,多少的指责谩骂,多少的恶意斥责,多少的冷眼不屑。第二天,所有的一切就化为了冰冷的沉默。
弱小,无助,死寂。
远在城市的云遥从睁眼的第一刻起,连校服都没换就赶回了家。而等待她的却不是弟弟,是家门前一群吵吵嚷嚷的人。
云遥扔下书包上前一把推开挡着门口正指指点点的邻里街坊。映入眼帘的是云昱孤单地躺在泥泞的地面上,身下血泊一片。
聪明如她。但此时云遥的大脑却断了根弦似的,久久反应不过来。云遥僵硬的走去,俯下身握住弟弟冰冷的手,眼中渐渐氤氲上了水气。
那双小手把她的理智生生冻了回来。
怎么会!怎么会呢!上周末她走的时候,云昱还拉着她的手跟她说:“姐姐,别太累了,你要注意休息啊,我等你回来呢。”
我等你回来。
我等你回来!
我等你回来……
这简短到只有五个字的句子一遍遍回荡在云遥的脑海里。无尽的重复着,重复着,重复着。
“你……等我……回来……”
可是,我回来了。
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