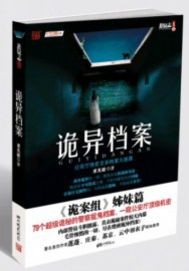张瓜子一家在安徽住了一月有余,夫妻二人开了一家瓷器店,专门倒卖各地各式的瓷器;瓷器这种东西,大都是卖给洋人的,国人大都是够用就好,并不会囤那么多;而洋人却将对于中国瓷器,青铜器和其他的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的囤积量作为自己势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尤其以古文物为主要。
这一月时间便使张瓜子彻底错过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机会;男昌起义打响,安徽通往男昌的火车停运,张瓜子一家被困在了这里,好在还有一间不大不小的瓷器铺。
张瓜子自始至终都在打理店铺的事情,每天起早贪黑;太阳刚刚划破苍穹,张瓜子便已经准备出门去进货和考察;日落西山,昏黄的电灯,张瓜子独自坐在木椅上,翻阅着各类与瓷器有关的书籍,又仔细观察着桌上的瓷器;早已将托付抛之脑后,一家三口的日子虽不富裕,但都还是幸福的,也是充实的。
张梅并没有去私塾,并非动乱年代没人敢开,而是张瓜子始终想着却又逃避着,承诺对于他来讲是不得不兑现的,而梅儿早已是他的心头肉,割也是割不掉的。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那托付之人像影子一般的形影不离。
正午,张瓜子像往常一样看在店里才刚吃过午饭。一位洋人走进,并递上一束菊花:“有个道士,和我说,拿着他的菊花到你这来,可以换一件瓷器。“
当洋人将菊花从风衣的口袋里取出时,张瓜子的心咯噔的颤了一下,仿佛什么在不断流出,冰凉的,总有一丝悲伤。
他知道,菊花的出现便是当年道士的提示,也是他与梅儿分离的信号;洋人见张瓜子愣在那里,便试探性地问了一声“sir?“
张瓜子慌乱的从身后货架上取下两件瓷器:“多给你一件,麻烦您带我去见一下给你这束菊花的人。“
洋人很莫名其妙,一个是给他菊花让他来换瓷器,一个是多给他一件瓷器,让他带着去找送他菊花的人,既然想要相见,为什么不自己前来呢?不过白捡的便宜总不能放掉,也便带着瓜子去了来时的歌厅。
当然,一个人想要隐藏是不必要出现的;等张瓜子和洋人来到歌厅时,早已不见道士的身影,只是门口的灯上多了一个挂着的、纹丝不动的纸人,面向远处的西天目山。张瓜子取下纸人,打开来看“见崖间一树且寻之,盘龙而走,遂至。“
寻着道士留下的字条,张瓜子别了洋人出城向着天目山深处进发。
虽然说有了道士提供的线索,可是这天目山上不见天,满是嫩绿色被阳光透的发黄的枝叶,根本看不见所谓的悬崖更别提那悬崖上的树了。
张瓜子索性笔直的向丛林深处走去,虽然被遮蔽了视野,只要一直向着天目山中心走去必然会找到,哪怕是找不到,大不了原路返回就是了。
阳光微斜,想必已是夕阳余晖,张瓜子慌了神,心想:这要是继续向着中心去,估计到了明天早上也回不去了。
张瓜子已然筋疲力竭,正巧了停在一条小溪旁;借着清澈的溪水,捧一把送入口中,瞬间缓解了那如同冒着浓烟滚滚翻腾的火山;俯下身蹲在临近溪边的空地上,扬起潺潺溪流,扑在脸上;轻松很多了,张瓜子随着溪流望向源头,这小溪是随着山体自上而下的,像是青蛇一般的盘绕在山间。
蛇!蚺,龙!
张瓜子突然想起字条的后半句“盘龙而走,遂至。”这眼前的岂不是字条上的盘龙!张瓜子豁然开朗,抖擞精神,本来疲惫的身体打了鸡血般的向着溪流源泉奔去。
原来那时就已经有火影跑了。。。
暮色已至,瓜子亦已至。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瓜子算是没有徒劳;眼前两颗对植青松之下一间古朴典雅,覆满青苔的道观呈现在眼前。
张瓜子踏着平整的由一块块清石铺成的小路,走向如受潮的红砖般色彩的木门,黄铜的狮头门环,两旁对联写着“青山自有青山路 明月哪来明月轮”;牌匾上像是重复书写过的四个大字“鄢月山庄”。
晃一晃门环,无人回应;从围墙的梅花窗看去,院内有三四间屋子,唯有一间亮着依稀烛光,却无人影;想必是已经休息了,张瓜子想。
虽然没有见到正主,但不无收获的是找到了托付的所在。
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的路确也不太好走;透过枝叶,星星点点的月光稀疏的撒在覆满落叶的山间野路上。看着一块黑一块灰的路,每一步都小心试探。
张瓜子其实胆小怕事,哪怕是在行伍呆了整整四年,也扳不掉不敢走夜路的毛病,更何况在这深山老林里,伸手不见五指。
走了有半个时辰,张瓜子挺不住了;下午上山就已经筋疲力竭,这到了山上也没来得及休息,又下山来,每抬一次腿,膝盖和胯骨轴都在咔咔作响,大腿肚子又不断抽搐;还是那个小溪,张瓜子想坐下休息一会;可这是南方,哪知道会不会窜出一条蛇来,哪怕是一只蚊子也要比北方大上两三倍,要是被咬上一口,这谁受得了!瓜子打消了休息的念头,痛饮了两三口水,奔着下山的方向挪动。
次日,瓷器铺没有开门,昨天的洋人等在门口,呆呆的,不知道从哪里又弄来了一束菊花,企图再换一件瓷器;张瓜子睡到巳时才醒,简单吃了口饭便带着老婆孩子奔后山(西天目山)去了,而后的事我们也都知道了,“鄢月山庄”的老道不愿收张梅为徒,这张瓜子却又受人之托务必完成,带着老婆孩子三番五次的拜访山庄,老道却始终是同样的答复——不收。
直到一日,张梅发起了高烧,张瓜子不得不带着梅儿就医,而放弃了去山庄再次拜访。这山庄的老道也是好奇的站在屋外等着叫门声,可惜迟迟未来;这三番五次前来的一家三口今日怎么没来?难道就这点耐心?不由得生厌。就在老道要转身回屋时,一个什么东西反射着月光,直直的奔着老道后脑飞去;老道是什么人?好歹修行了五十多年,这种小伎俩还是能反应过来的,身子微微一晃,只见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枚银针;
这针,他熟悉啊,是他师弟的手艺;回过头看向针飞来的方向,空空如也。
“师弟啊,你还在顾忌些什么?”
老道想不明白,师弟送来这枚银针是何意思,也许和这几日常来的张瓜子一家有关吧。
老道终还是收下了张梅,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发现,这个小女孩面相上并非常人;大耳垂,高山根,宽鼻翼,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只是这眉中多了几颗黑痣,而眼睛竟然是三瞳;这三瞳与双瞳不同,双瞳是两个瞳孔不重合,而张梅的三瞳是三个重合的瞳孔,每一个比前一个稍大一圈,呈红色、褐色、黄色,由内到外然后才是虹膜,才是眼白;这种人老道从未听说过,观内古书中也从未记载。这一连串的事情都是老道口中的“师弟”布的局,故一切还要等“师弟”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