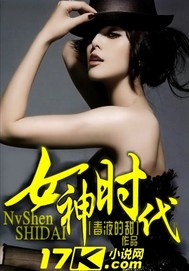孙叔况的病况稳定后,季长风便向张雀先说明,自己的包裹在城东的一个客栈里,须去取来。
遂告别了张雀先,望悦来客栈这边行来,一路上都阴阴郁郁的。
行到客栈,遇见白潮声等人,听了他的邀语,心下更是沉闷异常。
当是时,他只好快刀斩乱麻,咬咬牙,发声回拒了那白公子。
话道罢了,四下都是悄然。季长风一直将头埋着,不愿去瞧他人的神色。
他自知白公子情深义重,一片赤心,因而心下生愧,思量着该如何作释。
就在他这一思想之间,只听得一个拂袖,抬头时,已不见那白衣少年的身影。
季长风诧异,顾望了一圈也没寻到,只好问在旁的人。
李聪聪与那巫胖子都瞠目结舌的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看向青王汤媵沃时,只见后者摇头叹气,唏嘘着道:“佩服,佩服。”
见他这般举止,季长风心中莫名的不快,然而对方身份尊崇,他自不敢造次,只好复问了一遍。
然而汤媵沃并不答他,反倒嬉笑道:“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敢拒绝他的人。”
这头汤媵沃的声音刚落,那头李聪聪就叫喊起来:
“我说季长风你是不是误吃了黑驴蹄子啊——明堂少主邀请你,这么大的面子,你还敢拒绝?明堂啊——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的!”
季长风听了更是添堵,故意顶他道:“你个小孩子别多嘴!”
“你——”李聪聪立时给惹恼,捋起袖子做出干架的姿态,“你再说一遍小孩子试试——”
这时汤媵沃说道:“他往西面去了,你现在追还来得及。”
季长风闻言立时拔足往楼下跑。
一路上他专择那白衣裳的人看,插高簪抹白粉的象姑馆相公,呦呵拨浪鼓的七旬橘皮老头,擎了打衣棒在青石路上追娃娃的麻子脸女人??????都不是。
去了二三里地,看见一个阳伞店,里面立了一个白衣的背影。
行近了看,竟真是白潮声。他正拣了两柄伞在手里,犹疑不决,见到季长风来,顿时喜道:
“你来得正好,替我挑挑,哪一把好看?”
季长风本便不是雅好之人,这当下将那白潮声手中的两柄伞左左右右的看了又看,都是杏红伞面黄竹骨,不识得有什么分别,遂谦笑道:
“季某愚钝,看不出这两样伞,有什么不同??????”
白潮声觑他一觑,不满道:“当然有分别。”
见他不解,遂作释道:“这伞面仿的是杏花的颜色。杏花含苞未放时候,乃是全红,热烈,但是俗气;开放后逐一变淡,到了花落时候,就是全白了。
“因而,这杏花开放到五六分火候,就像素白的尺素书笺上落了一点胭脂红,最是好看。然而这个颜色却甚难调和,红一分或者白一分,都是不行的。”
季长风恍然,因笑道:“那??????这两把伞,哪把更接近?”
白潮声道:“自然是左手这把。但是这匠人画蛇添足,又在上面给我绘了些花枝,胡哨过头了,不干净。”
季长风道:“那便拿右手这把罢,上面什么也没有,而且颜色其实也相去不多罢。”
白潮声道:“不成,红过了一点,显得俗媚。而且还隐隐有个怪味,料来用的也不是什么好染料。”
季长风登时也别无话说,见那白潮声又在挑择店内旁的阳伞,心中略感疑惑,因问道:“白公子何以钟爱擎伞呢?不嫌??????不嫌烦琐么??????”
只听那白潮声悠悠应道:“我打小皮肤就不大好,不能在日头下晒太久。”
季长风又道:“那又何必专挑杏红色呢?能遮阳不就??????”
白潮声道:“不行,一定要好看。”
季长风登时又是失语,然而隐隐觉得,这白公子倒也是个有趣味的,不似平日那般沉闷寡世。
这么一想之间,那白潮声已瞧罢了店中的陈品,心无所善,遂道了一句“走了”,率先行出店去。
季长风愣了一愣,才要跟上,见到外头日光暴晒,灼眼烫肤,立时记起白潮声适才的言语,忙折返回去,随手捞了把伞,付过了铜钱,便急急将伞撑开,赶将上去。
那白潮声有意等他,故虽不回头,步子却自放慢了,这里才在嘟囔,怎还没赶来,便觉头顶一块阴影盖下来,转头去看,竟是那季长风擎了伞在替他遮阳。
“白公子不是说,皮肤不好么?那自是得??????”
谁知他话还没说罢,白潮声便将脸一阴,快走几步,躲开了伞的荫盖。季长风不解,赶上去道:“白公子你——”
“把伞拿开,我不要这伞。”
“为何?”
“这伞太丑了。”
原来事出匆忙,季长风慌不迭的随手拣了一柄,不知那上头绣了好大一朵红花,看在白潮声眼里,自是俗气难当,不堪着眼。
季长风不知底细,本是讨好之举,这下倒引人嫌弃,故丧气道:“能挡太阳就好了罢,我可是特意买的。”
白潮声觑他一眼,终归是放慢了步子,入到伞的荫盖里,放声唏嘘道:
“但愿路上不要有人认出我来才好。这么丑的伞,本公子的脸面都给你丢尽了。”
季长风笑侃道:“白公子生得好,就是擎一把破伞,也有姑娘为你神魂颠倒的。”
这一番美言,听得白潮声颇为自得,兀自笑了。他这一笑,倒真如那杏林尤物,占尽春风,真有引人神魂颠倒之颜色。
季长风在旁看见,忙错开眼去,平定了些许,这才支支吾吾道:“适才在客栈,对白公子,多有得罪了??????”
白潮声道:“得罪我?得罪我什么?”
“我???????拒绝了公子的一番美意??????”
“哦,不就是不想加入明堂嘛,你另有他选,怎算是得罪我呢?”
季长风听了此话,只当白潮声真不在意,遂心下一宽,喜道:“那就好。白公子适才不辞而别,我还当是您生气了。”
白潮声不成想他竟这般便信服了,诧异之余,也自恼这人的榆木心思。
当下也无可奈何,只好问道:“那你想去哪个玄宗应考?不会是云门罢。”
季长风道:“当然不会!那云门大宗师我已与他交恶多时了,且那日在冥宫被云门子弟束绑,为了挣脱,我还对他们大打出手,怎可能还选他们,这不是存心给自己找别扭吗??????”
白潮声点点头,转看他处,道:“如此说来,是要去太一道了??????”
季长风咂了咂嘴,将要说的话在肚里嚼烂了,这才吐出来道:
“白公子,我自小被我师父和师叔教养,他们一心只想让我们遁入太一,别无他选。我实有心傍依明堂,只是师命难违,也望您??????可以理解??????”
“理解理解。”白潮声吁了口气,依旧看着他处,不曾回头望他一眼,“你师父,是孙叔况?”
季长风吃惊,问道:“白公子何以得知?”
“姑苏剑道我还是有所了解的,那孙叔况在二十年前不就是凭借‘芙蓉一剑’扬名的么?只不过后来销声匿迹了这么久,我也差点认不出来你的招式。不过你那柄青剑,倒是绝对出自他的手中。”
“青剑?”季长风霎时间里忆起,当日解救熊荆于时,大梵天也因其手上的青剑,推测出他的师门,遂惑道:“这把剑,有什么独特之处么?”
“没什么特别的,但确乎是把好剑。上面有一个芙蓉图雕,很明显是孙叔况的手笔。也是,当年随他的剑法一并扬名的,还有他炉火纯青的铸剑才能。”
季长风因笑道:“师叔多年不曾铸剑,没想到能得到白公子的赏识,季某替师叔谢过了。”
白潮声听了这话,稍感诧异道:“你师叔?”
“是,他是我师叔。”
“那你师父是谁,除了孙叔况,我还没听说有谁得了‘芙蓉一剑’的真传。”
“我师傅隐姓埋名惯了,不便透露名讳。打小就是师叔在教导我们武功玄术。”
这厢说罢了话,两人正好行到一处桥前,看到水上有人立在舟前放炮竹,炮竹落在水里,扑通扑通的起来好大的水花,将左右邻近的舟上人都淋湿了。
被淋的人倒也不恼,反随着也放起炮仗来,登时水花一朵接一朵的开下去,将整个河面都开遍了,立在岸上的人受到水花的淋,竟放声大笑,于是引了愈多的人去围看,一道看一道喝彩,甚是热闹。
白潮声看了一阵,忽而兴起,蓦的转身对季长风道:“我们也一块去放炮竹罢,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