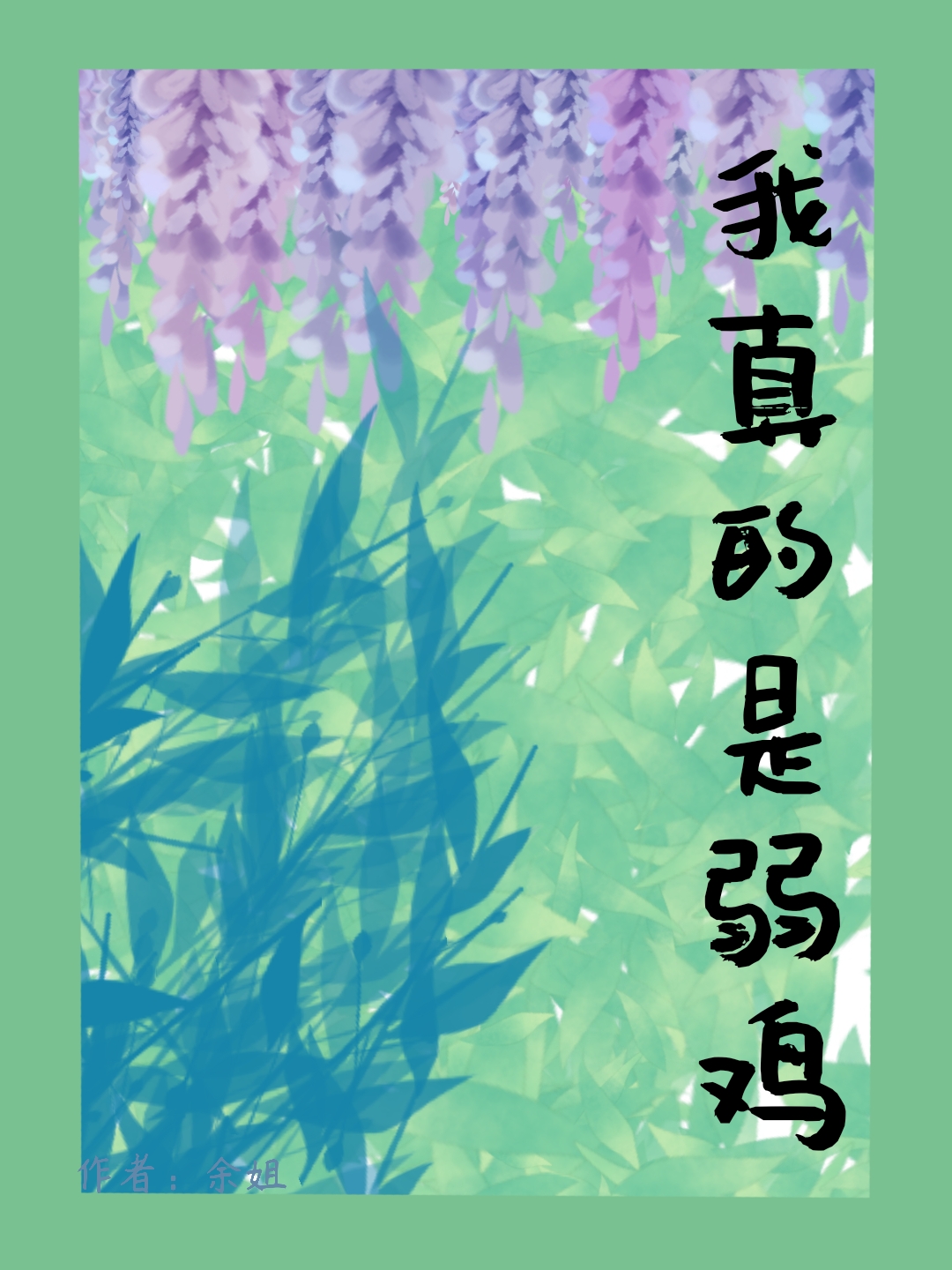转眼过了六七日,桂嬷嬷和春兰这几日来日夜轮流照顾着李允之,两人都不免感到乏累,尤其是年过半百的桂嬷嬷,更是觉得浑身酸疼到了骨子里。春兰劝她多休息,说自己年轻倒是不打紧的,可桂嬷嬷放不下心,说自己即使回房也是休息不踏实,不如多陪陪小姐。好在还有茶楼的掌柜,伙计和留下来的张岩,黎慎,他们负责烧水,做饭,跑腿打杂,不然桂嬷嬷都不知该怎么好。
至于魏舒烨,其实他每日都有来。可担心允之不愿见自己,每次都趁着午后允之喝完安神汤休息的时候才过来,静静地坐在她床边看看她,陪陪她,然后又趁着她醒之前悄悄离开。如此深情让桂嬷嬷这班李家人非常感激又欣慰,对魏舒烨越发的尊敬。
开始两三日,李允之每每入睡却总是不能安稳,不是被噩梦惊醒,就是呓语哭喊,浑身发着冷汗将衣衫沁湿,即便醒着时也是不言不语,独自发呆。好在这两日她的情绪总算稳定了不少,虽然还是不愿走出房门,但话比之前几日多了,胃口也好了不少,还会起床去窗前透透气。
现下她就端坐在窗子前,桂嬷嬷则一手托着药盒一手沾了药膏,就着明亮的光线轻轻的细致的为她抹着。抹的愈肤膏是李家药铺秘制的,提炼了数种名贵药材的精华加上雪貂油调配而成。一日数次几日下来,虽然淤青还在,但高肿的脸颊渐渐消了下去,伤口也结了痂,总算能看出点原来的模样。桂嬷嬷看着心里也好受了不少。
这时,春兰欣喜地进来禀报:“小姐,方公子和祁小姐将夏竹送回来了。”李允之一听赶忙起身让她们帮自己整理了衣衫,又用一方丝巾将自己的头遮得只露出眼睛来,这才去外面的小厅见他们。
夏竹是被张岩抱上来的。“夏竹。”李允之扑上前,伸手抚在她苍白如雪的脸上,泪珠打落下来。“夏竹,你现在好些了吗?”“小姐。”夏竹声音虚弱,看到自家小姐也是红了眼,哽咽道:“小姐,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没事了,多亏方公子和祁小姐救了我,照顾我。”李允之抬头看向他们身后的方祎和祁英,对他们点点头,先招呼桂嬷嬷和春兰赶紧将夏竹安置好。
待他们往另一侧的厢房去了,李允之转身对着方祎和祁英行了个大礼,“你们不但救了我和夏竹,还一直照顾她,允之不知该如何报答你们的大恩。请受允之一拜。”方祎和祁英急忙将她扶起。“允之你别这样,快起来。”祁英急了。
李允之攀着祁英的手臂继续说:“阿英,昨日听春兰说你那日也受了伤,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可我这模样也不好去给你赔罪,我心里很是不安。”
祁英将她拉起来:“我没事,你看我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倒是你伤还严重着,这又跪又拜的,扯着伤口可不好。”
几人在小桌前坐下,李允之还是不放心地问:“阿英,你的伤真的好了吗?”“好了好了。我给你看看吧,免得你担心。”阿英说着就撩起袖子,露出手臂那道粉色的疤,“看吧,伤口都愈合了。”“可这道疤……”允之还是过意不去,同为女子自然对自己的肌肤格外爱护。可祁英却是满不在乎的模样,她放下衣袖摆摆手说:“没事,我们习武的人免不得会受伤,一道疤算什么。”允之想了想叫来桂嬷嬷取了几盒愈肤膏递给祁英,“这药膏是我们药铺秘制的,抚平疤痕的效果极好,我也在用着,你试试。”祁英不在乎可自己终是不安心。
祁英接过那几盒药膏在手里把玩着,方祎在一旁说:“允之的一片心意,你就用着吧!说你糙还真是,女子家哪儿像你这般不在乎的。”祁英撇撇嘴瞪了他一眼,倒是收起了药膏,“那我试试,谢谢你啊允之!”李允之摇摇头,
“你说的让我怎么好意思。你为我做的哪是几盒药膏就能谢的。”
方祎又凑上来说:“我们也算是生死之交了,你们再这般客套来客套去,别扭的很。”
“对呀对呀,允之你再这样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祁英附和着。“别……”李允之急忙道。“我不说了总行吧!”方祎和祁英相视而笑,对她说:“这才对嘛!”
随后李允之陪在旁边请他们喝茶,又问:“夏竹到底如何了?”“郎中说她已无危险,只是到底还好好养一阵子才行。这丫头清醒过来就要回你身边,我们劝都劝不住,只好今日给她送回来了。”李允之听了很是感动,想起夏竹苍白的脸不禁又红了眼。“你别再伤心了,过去的事就别去想。等你和夏竹都好了,我们又能一起去玩了。”祁英安慰她。“嗯。”李允之赶紧擦了泪。
几人又聊了些别的,最后还是方祎怕扰了李允之休息,拖着祁英就起身告辞。“改日我们再来看你哦。”祁英依依不舍地跟李允之告别。“好,你和方大哥一定要来。”经过此事,三人的友谊变得更深了,就是对方祎,李允之也终于改口叫了方大哥。
夜幕时分,神情疲惫的王锐才刚从外边回到家,“老爷怎么样了?阿哲他可有消息?”王夫人就急匆匆迎了上来,焦急的脸上挂着泪痕,搀扶着她的王月音和两个哥哥王召,王含也是急切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王锐看着他们“唉~”了一声,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上首椅子上坐下,“老爷~”王夫人更急了,紧跟在他身后。王锐奔波了大半日又说了不少话早已是口干舌燥,见案几上放着茶端起来就喝,一入口却是冰凉苦涩,他恼火的掷了杯子手掌更是在案上重重拍了一下,吓得身旁的王夫人母女一跳。
“阿哲的事没那么容易了结了。”王锐耷拉着脸,叹了口气。王夫人一听就哭起来,
“啊,我的阿哲啊,怎么突然就遭了这么大的难啊?”“母亲……”王月音想安慰她,却被王夫人一把搂进怀里,“我的阿哲啊,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他在那里边受了多少的苦啊?”王月音跟着掉泪,王召王含也是垂着头愁眉不展。
王锐见她们俩又只会哭哭哭的,疲惫之余更是一个头两个大。“别哭了,这还没办丧呢!”他不耐烦地斥责了一句。王夫人抬起头看向他,“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担心儿子还错了?”王锐见她愈加伤心,又重重地叹口气,撇过头去。王含上前劝慰王夫人,“母亲稍安勿躁,父亲也是担心阿哲,今日又奔波了这般久才回来,就让父亲先休息会儿吧!”扶着王夫人在另一首坐下,随后兄妹三人各自也找了位置,一时间厅里沉默着,只有王夫人母女低低的抽泣声。
“老爷,你到底打听到什么了?”王夫人终归是担心小儿子,没过多久忍不住又问起来。
“我今日去见了大理寺里的金大人,任凭老夫怎么说他就是推三阻四的,只说阿哲的案子是圣上亲自督办,他也没办法。而且他说这两日阿哲之前做的那些混账事多多少少查到了些,人证物证都有,虽然阿哲始终没认罪,但也无济于事!况且案子还在继续查,估计……”说到这,王锐眉心的川字纹更深了。
“那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阿哲就是做事糊涂些也不至于大罪啊!”王夫人依旧偏袒着自己的儿子,在她眼中王哲和随从打几个人砸几个场调戏调戏女子,赔些钱也就是了,何至于让圣上亲自督办。
“金大人说了,其中一个案子,阿哲在一处花柳之地与他人为着抢一个风尘女子,不但唆使朋友将那人暴打一顿,还将他从楼上掀了下去,导致那人瘫了。据说已有多人证实是阿哲亲自抱住那人的腿把他掀了下去。这逆子,唉~”王锐握拳轻砸了下案几,顿了顿,转脸问向长子王召:“阿哲之前伤过的人,你查到了多少?可都交代他们了?”王召闻言面露难色:“回父亲,阿哲这些年做过的糊涂事不少,这一时间也难查周全。我这几日费了番功夫倒是找到几个与他有过节的,花费不少让他们即刻离开韩霜城,至于别的还在查找中。还有,平日里与他一起胡混的人我也安排了去处,让他们先躲躲。”王锐点点头,“能少一桩是一桩吧!还有,阿哲到底在何处被抓,抓去之前在干什么?这些你们可查到了?”
王哲顽劣成性惯了,家里除了王锐谁也拘不了他,可王锐哪有那么多的心力管他,加上王夫人又常常给他打掩护,故王哲更是逍遥痛快,有时连续几日都不着家。接到圣旨前,王哲亦是几日未归家,王锐虽生气却也没多想,突然间听闻王哲被捕一家人都甚感震惊。
“回父亲,我听闻阿哲近月来跟几个身份可疑的人走的颇进近,阿哲暗中与他们见过好几次,至于他们是谁要做什么还不清楚。阿哲贴身侍从阿吉也还未查到踪迹。”王锐的次子王含回答。王含所说的阿吉就是那日随王哲一同去掳劫李允之的车夫,他当时被方祎一脚踹下马车后撞到路旁的崖壁,当场就一命呜呼了。而去沁茗阁的路上,方祎又仔细向赵彻回禀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赵彻思考了一番后指派自己的一支暗卫趁着夜色照方祎所说的位置去寻找,将那些尸体带回找个地方安置起来待查验身份,故王家至今还不知道城外那片树林发生的事。
“身份可疑的人?”王锐垂首喃喃低语,而后眼尾一扫,“那几个人可有消息?”王含再回:“目前消息还不多,只知道其中有个人脸上有道长疤。”
王锐皱眉,沉着脸斥到:“这逆子平日里与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晃荡街市也就罢了,现下还与不清不楚的人扯到一块,不知又去做了什么混账事。”他的胸膛因着怒气起伏不定。
这儿子一直不省心,三天两头给自己丢脸,现下更是撞在了赵彻手里。这几日自己到处与人托关系,一来请他们帮自己向赵彻说说情,二来打探消息。可那些人都回复他,圣上说了,王哲的案子还在办理中,结果如何还未可知,还请王大人稍安勿躁。这会儿案子都被查出来几个,自己又有什么脸再去求赵彻。
“那父亲,此事可真没牵涉到其它?”王召上前俯在王锐身边小声问出自己心里最担心的问题。王锐顿了顿,摇摇头,“应当是没有,至少目前没有。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些。”王召点点头。
王锐这几日的奔波也不是一无所获,据他在各处安插的人回禀,王哲一事应是事出偶然,目前并未发现圣上有其它的意图。别人说的他或许怀疑,但其中一个叫阿德的小太监也这么对他说,他是信的。这个阿德原先是王家别庄的仆役,有一年王锐身体不适到别庄修养了月余,这仆役侍奉的他甚是贴心,给他留了好印象。三年前王锐趁着宫里增选太监的机会打算着在赵彻身边安插自己的人,便让人挑了几个送去,其中就有他想到的阿德。那阿德也没推拒,只说这是王大人看得起他,他愿为王大人效命以报王大人的提携之恩,遂净了身进宫去,这让王锐更是满意。
最后送去的几人只有阿德获得了洪公公的青眼被安排在赵彻身边侍奉茶水洗漱。他也是王锐安插在离赵彻身边最近的人了,赵彻在宫里的一举一动,见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阿德都会偷偷记下来告诉自己。这两年来自己凭着他的消息几次提前获悉赵彻对某些政务的看法,从而做了对自己有利的应对。还有两个在他面前曲意奉承却转头在赵彻面前挑拨离间过的官员,他们一个被自己设计落马重伤辞了官,另一个被自己揪了小辫子贬出了京城。王锐对此人还是非常信任的。
王锐现在只庆幸,自己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他对自己的这个儿子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知他不但胸无点墨而且脑子里也没一点正紧,何况他的性子就跟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实在难堪大用,所以自己平日里私下做的勾当都没让他参与。这会儿就算赵彻再从他身上查下去应当也不会查出什么来。怕就怕赵彻会因为此事怪罪自己。唉~还得想想办法,最好勾起赵彻念念自己往昔的情谊。
就在王锐一家沉浸在愁思中时,他的心腹护卫进来回禀说有人送来一张字条。王锐赶忙接过那张字条打开来看,“我有要事还得出门一趟。”匆匆对家眷们留下这句话后,他即刻出了门去。
皇宫后边的一处小山脚,一条小路连接着皇宫的小门,平时是运菜运水才走的地方。此时月色当空,小路上静悄悄的。一个年约二十余岁的小太监借着月光正张头张脑地四下环顾,怀中紧搂着一卷东西。忽然他面色一喜,迎向前去。“王大人?”王锐此刻罩着一袭黑色斗篷并拢上帽子遮住了自己的头,走近前才看到他的脸。为了避免被人发现,王锐早早下了马车,在护卫的搀扶下走了两里路才来这儿,这会儿有点喘。“阿德,你找我有何要事?”这个阿德正是王锐安插在赵彻身边的小太监。“王大人,我得了个重要的消息要告知您。”阿德将怀中的那卷东西递给王锐。王锐看了他一眼,赶紧打开,是一幅半身画。画上的人浓眉络腮胡,脸上还有道疤。“此人是?”王锐看到此人就想到了王含说的那几个身份可疑的人。“这人应该和三公子有所牵连。小的今日见圣上让人临摹了好几幅并吩咐拿去分发对比要捉拿此人。小的趁着领画的人不注意,偷偷留了一幅拿来交给王大人。”
王锐笑笑,对身边的护卫使了个眼色,护卫立刻从怀里掏出两锭金子递给了阿德,王锐一边收起画一般对阿德说:“你一向都做的很好,这些你先收着,往后更少不了你的好处。”阿德也高兴地收下了两锭金子,躬身说:“王大人言重,小的受您提拔之恩自当尽心回报。”王锐满意地点点头,“那老夫先回去,你有消息再通知老夫。”阿德恭恭敬敬地送走了他,再抬头时却是脸色诡异。
而王锐得了这幅画,在回去的路上就下令护卫加紧去查探此人的信息,找到后务必问出王哲跟此人的关系,接着当然是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