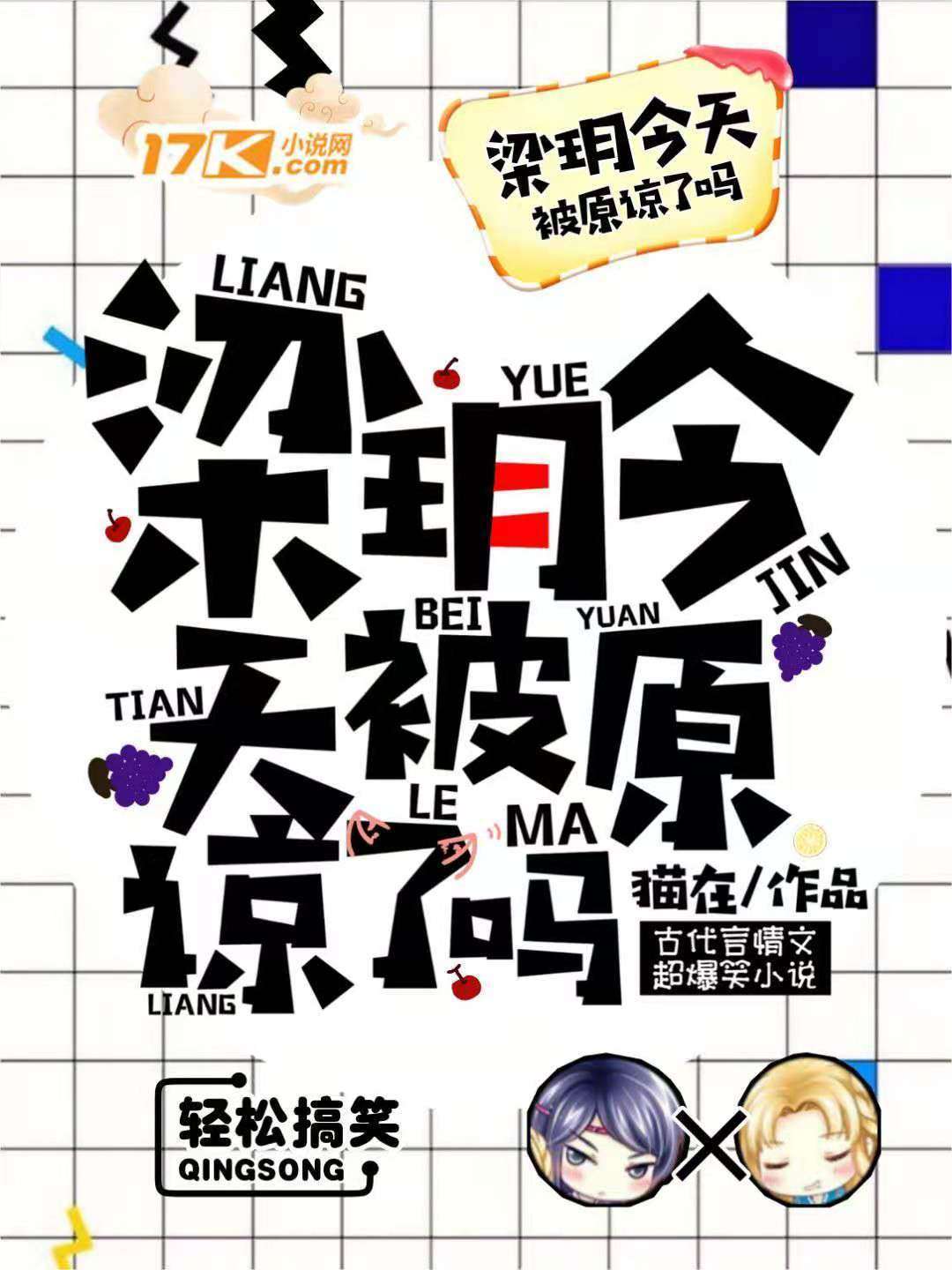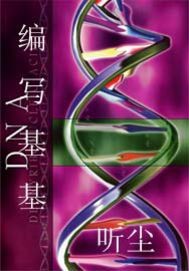“你来讲吧。”沐弘把阿寅推到前面。
“是。”阿寅跪下来对堂上磕个头,也不打开书简,跪着背诵道:“从春秋开始,史书上就有彗星的记录:春秋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史记秦厉共公十年,彗星现空;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自汉以来,彗星记录趋于完善,《汉书·天文志》记载六次,分别是汉文帝后元二年,汉昭帝始元二年,汉成帝元延元年,汉明帝永平八年,汉顺帝永和六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每七十六到七十九年,星官就能观察到彗星经空,并记录在案。最近一次记载是晋惠帝元康五年,距离当今七十七年。”
“你想说明什么?”李威开口问道。
“禀太尉,彗星是空中的一颗天体,有固定的轨道和运行周期,并不是什么凶兆。”沐弘接口回答。
“史书上可有相关灾殃记录?”王猛问。
“禀丞相,根据汉书,彗星出现的五年内并无灭国事件,除了建安二十三年那次,两年后,汉献帝刘协禅位于魏文帝曹丕。”阿寅回答。
“这不能算凶兆。刘协早就是曹氏家族控制的傀儡皇帝,被废是迟早的事,禅位算是温和的方案了。”王猛笑眯眯地说。
李威双眉紧锁,思索片刻,问道:“虽然史书中有多次记载,但你有何证据证明这些都是同一颗彗星呢?”
沐弘被问住了,内心惊骇:这个李太尉好厉害,一开口就能抓住要害。
“禀太尉,”阿寅接住,“奴婢比较了记载中描述的形状、颜色、亮度,以及经行轨道,确定是同一颗彗星。”
沐弘也想到了说辞:“下官的家乡世代相传有这么一颗周期出现的彗星,取名为哈雷彗星。”
王猛问:“民间也有天文观察者?”
“有啊,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聚在晒谷场上乘凉,老人就会指点孩子识别夜空里的星宿。流星雨出现的时候,年轻人还会爬到山巅彻夜等候。”沐弘回忆起前世的童年,他担心王猛深究,忙加上一句:“可惜,战乱来临,乡亲们死的死逃的逃,都失散了。”
众人沉默了一阵。天王终于开口:“如此看来,彗星之灾实不可信。”
王猛也说:“我大秦以法治国。若因一颗星的出现而大开杀戒,实乃荒谬。”
沐弘松了口气,心想这就是一锤定音了吧。
李威却说:“然而星象之学延续千年,不能全然推翻。况且明光殿出现的黑衣人,留下的警告与星象相符,不可不防。”
沐弘问:“那个贼人还没有抓到吗?”
李威沉下脸:“神明预警,你怎么说成是贼人?”
沐弘冷笑:“倘若果真是神明下凡,就该在青天白日之下,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现身于陛下和众位肱骨大臣面前,宣示上天的谕令。黑灯瞎火,在无人的偏殿故弄玄虚的,只会是鬼蜮小人,大人为何要相信这种鬼话?”
李威脸色铁青,无言以对。王猛含笑,点头赞许。
天王笑道:“沐卿言之有理,神人下降,应该来见朕才对,为何要躲在暗处?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两位重臣没有异议。
天王接着下达处分:“张孟作为星官,禀报天象异变是职责所在,但妄言灾祸,引发骚乱,是为失职,降一级留用。沐弘学识渊博,纠正谬误,升一级以示嘉奖。”
走出温室殿,外面天色昏暗下起了雨。初春的天气寒意料峭,雨滴中夹杂着雪珠,打在身上沙沙作响。沐弘让阿寅返回观星台,自己赶去凤凰殿报讯。
“这么说你搞定了?”慕容冲趴在床上,捧着一盆甜瓜啃食。
“陛下亲口说了彗星之灾不可信,丞相和太尉都没有异议。”
“有没有奖惩?”
“陛下把张孟降一级,把我提了一级,这样,我就和张孟平级了。”沐弘颇为得意,看到床上趴着的人,又觉心痛,“小王爷,是我失职,害你受苦了。以后我会盯住张孟,不让他再出幺蛾子。”
“张孟一纸上奏,搞得满城风雨,只是降了一级,这惩罚也太轻了吧?”慕容冲并不高兴。
“陛下为人宽厚,也许是看在他奉职多年的份上,不忍重罚。”
“一个小小的太史令竟敢预言灭国,胆子这么大,背后一定有后台。”慕容冲说,“你看会不会是王猛?”
“不像。”沐弘摇头,“王猛心高气傲,崇尚法理,不信鬼神,这次当庭辩论,他是支持我的。倒是建宁公李威,不停地提出质疑。”
“李威?”慕容冲显得茫然,“此人与鲜卑并无仇怨,为什么要来害我们?”
王猛指挥秦军攻灭燕国,慕容冲提起他就咬牙切齿。但李威在交战时期一直留在长安,辅佐太子守国,手上没有染血,慕容冲对他就没有多少怨恨。
“当然,也可能是他比较相信星象学说,不见得就是张孟的后台。”沐弘说。
慕容冲啃完一块瓜,把盆推开。叶玄过来把瓜盆挪走,绞了毛巾给他擦手擦嘴。
“张孟胡言乱语,给陛下带来天大的麻烦。陛下再怎么宽厚,也不该这样轻轻放过,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慕容冲皱眉思索,“要么张孟背后的人位高权重,陛下不得不给他面子;要么陛下心里并没有完全否定张孟……沐弘,你不能掉以轻心,没有揪出幕后之人,这件事不会完结……”
担心太后再次生事,这段时日,沐弘一直陪慕容冲住在凤凰殿。廷辩过后,大臣们听到风声,不再在星象上纠缠,长安城里渐归平静。
过两天沐弘回观星台,本想去盯一下张孟,却惊闻一件噩耗。
“怎么会这样?”沐弘大惊失色。
阿寅瘦小的身躯平放在木板床上,面容惨白,身体僵硬,没了气息。阿宽跪伏在床边,哀声哭泣。
沐弘一把揪起他:“阿寅怎么死的,你给我说清楚!”
“那天,张大人从宫里回来,非常生气,把阿寅痛骂了一顿,罚他跪在雨地里淋了一夜。第二天阿寅发起高烧,张大人把他关在杂物间,不给吃喝,也不许我们靠近。万师兄带着大伙向张大人下跪求情,张大人不理,直到夜间才放出来,阿寅已经爬不起来了。请了大夫来瞧,没能救过来,就这么没了……”
沐弘脑袋里轰轰作响,红着眼睛冲进官署,大喊:“张孟,你给我出来,有种冲着我来,残害弱小算什么本事?你出来,我要杀了你给阿寅报仇……”
官署里杳无人迹。万通赶到门口,说:“张大人今天没来。”
沐弘操起一把椅子,把屋子里砸得一塌糊涂。
任他怎么发飙,阿寅是回不来了。沐弘握着他冰冷的手,想起邬建带着一群小黄门登上金凤台让封枢面试的情景,高台上风急云轻,封枢拉着阿寅的小手,眼中满是期许。
邬建、封枢都不在了,如今他又失去了阿寅。这个孩子年龄还没有慕容冲大呢,聪明刻苦,极具天份,却因帮他的忙而丢了性命。他那天为什么急着跑去凤凰殿呢?他为什么没想到张孟大败亏输之后不会疯狂报复呢?他只想着炫耀自己的胜利,却把这个柔弱无助的孩子丢到了脑后。这段时间他犯了多少错误啊:忽视太史令的职责,害慕容姐弟遭殃,忽视对阿寅的保护,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悔恨像一锅滚油煎烤着他的心,他扬起手,左右开弓把脸打得噼啪作响,阿宽惊叫着拉住他:“大人,你这是怎么了?”
“是我害死了阿寅……都是我的错……”沐弘痛苦万分。
“怎么能怪大人呢?要怪也该怪我呀……”阿宽放声大哭。
奴婢的命就是贱,沐弘向太常寺申诉,只获得一张对张孟的记过处分。惩罚失当,致人死命,主官无需承担罪责。张孟这几天躲着不露面,沐弘也没处寻他。
守灵三日后,万通建议入土为安,沐弘拿出钱来,让他买一口上好的棺木,并安排殡葬事宜。
“大人,阿寅想回邺城呢。”阿宽私下里禀道。
“他留了遗言吗?”
“是的,阿寅临去前清醒了一忽儿,他说他想回邺城埋在师傅身边。”
“也好。”沐弘想了想,“先入棺吧,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了,就送他回去。”
“不劳大人远行,奴婢带阿寅回去。”
“长安到邺城,路途遥远,你还小,一个人怎么行?要么让万通和郝乐陪着一起去。”
“不用麻烦师兄,奴婢自己能行的。”
沐弘把他看了看,他从没留心过这个孩子,此时见他原本讨喜的圆脸瘦成猴腮,眼睛里充满哀伤。
“你和阿寅朝夕相伴,感情深厚,我能理解。”沐弘叹道,“都怪我没有保护好阿寅,害他惨死,怎能再让你出去冒险?”
“不怪大人,都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阿寅……”阿宽哭倒在地。
“你不必自责。”沐弘劝解,“张孟借阿寅泄愤,你怎拗得过他?”
“那天大人回来过,我见到了,却没有禀告。”
沐弘恍惚想起他是回过一趟观星台,因衣袍被雨淋湿,他趁傍晚雨停的间歇回来换了件衣服。
“我看到大人匆匆来去,若赶着禀告一声,大人一定会救下阿寅。但我没有……因为我一直嫉妒阿寅,他比我聪明,比我勤奋,那些深奥的书籍,他看一遍就能记得,而我怎么也学不会……师傅也好,大人也好,眼里只有阿寅,从来没人注意过我……我嫉妒他,我想让他受点罪,却没想到害了他的性命……”
沐弘惊呆了。人心幽微,即使一个孩子也难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