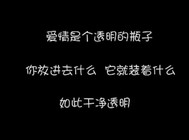中国人有理难伸?伍挺举据理力争
麦基洋行里,麦基正在审读一份报表,里查得匆匆进来。
见他面色惨白,麦基惊问:“What's the matter?(怎么了?)”
“He's gone,I mean Comprador Duan.(他不见了,江摆渡段。)”
“Gone?”麦基怔道,“Where? (不见了?去哪儿了?”)
“What's worse,(更糟糕的是,)”里查得摇头,“he took a note away, as well as a cash check from HSBC.(他带走一张庄票和一张汇丰支票。)”
“A note?(庄票?)”麦基震惊了,“A Note of Maosheng?(茂升钱庄的庄票?)”
“Yes.(嗯。)”
“How much?(多少钱?)”
“10000 liang of silver for the note of Maosheng and£200 for the check.(茂升钱庄庄票一万两白银,汇丰支票是200英镑。)”
“Where is he now? (他去哪儿了?)”麦基忽地站起,报表掉在地上,猛捶桌子,几乎是吼,“Get him! Get him at once! Take back the note! Take back the check!(找到他!立即找到他!收回庄票!收回支票!)”
“Yes. (好的。)”里查得匆匆走出。
麦基呼呼喘气,脸色铁青,跌坐在椅子上。
喘会儿粗气,麦基渐渐平静,伸手拿过电话:“I'm McKim,please get me through to the police station.(我是麦基,请接巡捕房。)”
大卫段一头撞进广肇会馆的总理室里,犹自惊魂未定,扶住门框边呼呼喘气。
马克刘打开他随身携带的箱子,看到满是黄澄澄的金条,张口结舌。
彭伟伦上前几步,亲热地拍拍他的肩:“小段,干得好哇,一箭双雕!”
大卫段稳住心神:“谢??谢彭叔褒奖!”
“彭叔全都安排好了。”彭伟伦从怀里掏出一张船票和一沓子美元,“马上就有一班到**的船,这是船票,你先到**,再由**赴美。我在美国有家企业,你就在那儿安身。这箱金子永远是你的,暂先存放我处,待我换成美元,一分不少,全部给你汇去。记住,没有我的话,你不能回来!”
“谢谢彭叔,”大卫段点头,“我听彭叔的。”
彭伟伦看看手表:“这辰光,麦基肯定报警了,不过,巡捕房不会那么快。他们要到洋行了解情况,然后再到你的住处搜查,然后才能想到封锁码头。你现在就走,万无一失。”又转对马克刘,“刘老弟,你送小段,记住,一定要送到船上。去吧,夜长梦多,彭叔不留你了!”
大卫段跪下,朝他重重地磕个头:“谢彭叔安排!”
天色傍黑,茂升钱庄准备打烊,伙计正在关门时,里查得的轿车在门外戛然而止。
见门将关住,里查得钻出车门,急急朝钱庄扬手:“No, no, no.”
关门的伙计停下来。
里查得大步挤进只剩一条门板的大门,匆匆走向柜台。正在盘点的账房把头与伙计皆吃一惊,纷纷停下手中活计。
“请问,”里查得声音都变调了,“江摆渡段来过没?大卫段!”
“来过了!”账房应道,“你要寻他?”
里查得惊道:“他做什么来了?”
“取银子,说是洋行急用。”
“什么时间?”
“没多久。这刚走。”
“No,”里查得跺脚,“你们不能让他取走银子!”
众人面面相觑。
“怎么回事?”大把头急问。
“是这样,”里查得这也冷静下来,连比画带说,“他犯错了,他是大偷,他偷走了洋行的庄票,你们不能给他支付!”
大把头与众伙计无不震惊。
里查得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地驱车离去。
翌日清晨,王探长赶至洋行,通知他们案犯极有可能离开上海了,他们正在全力追捕。
“I knew it.(早知道了。)”麦基不无郁闷,冷笑一声,扬手赶客,“I knew it yesterday. I never thought you could get him back. Get out. Get out of my sight!(我昨天报案时就知道了。我就没指望你们能够把人追回。滚,滚离这儿!)”
王探长听不明白,转向里查得。
里查得朝他笑笑:“我们总董的意思是,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
王探长连连打拱,似也看出麦基脸色,扭头走去。里查得送到楼梯处,与他别过,返回麦基办公室,见他坐在大转椅后面,仍在呼呼喘气,面孔都变形了。
“What shall we do now?(下面该怎么办?)”里查得问道。
“Ooooh,”麦基匀住气,长叹一声,“the shadow of devil always follows us. The goods were soaked, and now the damned thief! You know, we have been short of money for years. What we earned in the rice trade is far from enough. 10000 liang of silver is not a big sum, but it's in the 520yd.com need money. We need money right now!(魔鬼的影子总是跟着我们。货物浸水,这又遭遇这该死的窃贼。你知道,这几年来我们一直银根紧缺,贩米赚的那点钱远远不够。一万两银子不是大数目,但恰逢其时呀。我们需要钱,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钱哪!)”
“Yes.(是的。)”里查得计上眉头,“I think we might get the 10000 liang of silver back.(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一万两银子讨回来。)”
“Well, how?(哦?向哪儿讨?)”
“Maosheng Money House. It is the money house that gave that money to the damned Duan! They should have done a thorough check, at least, they should give us a message before they cash the note. It's a large sum of cash, isn't it?(茂升钱庄。是茂升钱庄把这笔钱付给该死的那个家伙。在兑现庄票之前,他们应该好好审查一下,至少说,他们应该给我们捎个信。这不是笔小数,对不?)”
“Yes, (你说得是,)”麦基眼珠子一动,“you are right. But how?(但怎么讨呢?)”
“Bring them to the Mixed Court. They have never won a single case since the court was founded.(向会审公廨起诉他们。自公廨成立以来,他们从未赢过一场官司。)”
“OK.(好吧。)”麦基重重点头,“You go and get our lawyer.(你联系律师。)”
会审公廨一张传票,将茂升钱庄上上下下全搞蒙了。
俊逸两眼如炬地盯视会审公廨的传票。
大把头将兑付过的庄票并排儿摆在桌上,指着其中一张:“老爷,这就是那张庄票,是我们茂升开出的。认票不认人是多年来的老规矩,洋人起诉我们,完全不合情理!”
“是哩。”老潘接道,“如果我们不认庄票,以后谁还敢收我们的庄票?”
俊逸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两眼紧盯在庄票和公廨的传票上。
房间里空气凝结。
“唉,”俊逸终于发出一声长叹,“理是理,但要分个地方。要是在我们地界上,就由我们去说。问题是在会审公廨,那是洋人的地盘,不认我们这个理呀!”
“那也得有个解说,”大把头辩道,“会审公廨里也有我们的谳员,可以让他通融通融。洋人有的是钱,不会在乎这点儿。”
“问题不在钱上,”老潘点中要害,“在这庄票上。如果我们认罚,以后再与洋行做生意,还开不开庄票呢?”
“不瞒二位,”俊逸点头,“我忧心的正是这个。一万两银子,我赔得起。规矩坏了,我赔不起呀。”
“老爷,这??”大把头哭丧着脸,“这该哪能个办呢?”
俊逸眉头拧起,良久,摆手道:“你们去吧,让我好好想想。”
二人出去,俊逸在椅子里硬着头皮坐了一会儿,起身出门,径直走到钱庄大门,没叫马车,而是闷头沿大街漫步。
顺安小跑着追前几步,小声叫道:“鲁叔!”
俊逸顿住步子。
“鲁叔,我??”
俊逸看他一眼:“有事体吗?”
“鲁叔,都怪我??一切都是我的错。”
“哦?”俊逸以为又出什么事体了,盯住他问,“啥事体错了?”
“那张庄票。”顺安嗫嚅道,“江摆渡段寻到我,是我把庄票送到柜上,又把钱交给姓段的。我后悔死了。第一次做事体,就捅出介大娄子,我??我给鲁叔丢脸了!”
“呵呵呵,”见是这事,俊逸笑出几声,拍拍他的脑袋道,“晓迪呀,这不关你的事体。放心吧,没有人责怪你!”
“鲁叔,我??”
“做你的跑街去。眼下生意不好,你多努力。鲁叔指靠你哩!”
“鲁叔放心,”顺安哽咽了,“小侄??一定努力!”
“哈哈哈,彭哥,”马克刘喜不自禁,“好事体不来不说,一来就是接二连三哪。”
彭伟伦嘴巴没张,眼睛却在斜睨他,半是质询。
“麦基洋行向会审公廨起诉茂升钱庄了!”
彭伟伦没有应声,手指却有节奏地敲起几案,鼻子里轻轻哼起一曲广东民谣。
“彭哥,”马克刘愈加兴奋,“您这一箭不是双雕了,是三雕呀。”
彭伟伦停住哼曲,一手继续敲着,另一手端起一杯茶水,轻啜一口,放下。
“彭哥,你这曲儿还没哼完呢!”
“呵呵呵,”彭伟伦微微一笑,“是该接着哼了。你安排一下,到报馆里寻几个有正义感的记者,让他们好好编排编排。洋人无理反成原告,中国人有理无处申诉,唉,”故意摇头,“要多憋屈就有多憋屈嗬!”又提高声音,慷慨激昂,“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人哪!呜呼哀哉, Chinese(中国人)!”
“彭哥,”马克刘竖起大拇指道,“真有您的!老弟服了!”
茂升钱庄外面的大街上,几个报童竞相叫卖:“看报,看报,生意伙伴变成冤家对头,麦基洋行监守自盗,会审公廨状告茂升钱庄,无理反而胜诉。茂升钱庄认票不认人,有理反而败诉,白赔洋人白银一万两哟??”
一辆马车停下,俊逸跳下车,听到声音,掏钱买了几份报纸,掖在胳肢窝里,大步走上台阶,走进经理室,将几份报纸浏览一遍,凝眉良久,召来老潘,要他通知茂记所有掌柜速到钱庄议事。
一个时辰后,八大把头与十几个掌柜陆续赶到,齐伯也破天荒地出现在议事厅,但没有坐,如往常一样站在门口。
鲁俊逸最后一个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摞报纸。
议事厅里鸦雀无声。
俊逸走到主位坐下,声音低沉,扬起一张判决书,开门见山道:“就在昨日,租界会审公廨判决茂升钱庄赔付麦基洋行一万两规银,一个月内付清。我鲁俊逸认罚,因为我并不想多生事体。然而,不生事体,事体照样寻上门来。”
鲁俊逸放下判决书,扬起手中报纸。
所有目光都盯在这些报纸上。有几人面前也摆着同样的报纸。
“诸位,”俊逸将报纸扬起,抖了抖,“想必你们都看过这些报纸了。事体既然曝光,就不单是我们一家的事体了。如果我们认赔,不仅是我鲁俊逸面上无光,茂升钱庄大门上的那块匾牌,也将无法硬朗起来。如果我们不认赔,我们的对手是洋行,判决这起凯思(case,案子)的是会审公廨。在这样的地方,与这样的对手对阵,我们根本没有胜机!”
众人面面相觑。
“不瞒诸位,”俊逸脸色严峻,“我鲁俊逸自经商以来,遇到过不知多少难过的坎儿,可哪一个也没有这一个难过。我有三个晚上不曾合眼了,左思右想,始终未得摆脱之方。今儿召请诸位,也算是集思广益,共同开个处方。成也好,败也好,是大家的主意。”
没有谁说话,场上掉根针都能听见。
顺安左右看看,见谁也不说话,牙一咬,朝众人抱拳一圈:“诸位同仁,鲁老爷把话说到这儿,我就先说两句。我虽然是新任跑街,但与诸位相比,却算是与麦基洋行交往最多的人了。我把我所晓得的事体讲予诸位,算作抛砖引玉。”
众人皆看过来,纷纷点头。
“诸位同仁,”顺安又是一拱手,“我多次去过麦基洋行,晓得这个洋行很有实力,不会在乎一万两银子。我听密斯托里查得说,单是上次与我们合作的那笔大米生意,他们就赚下不少洋钿。我私底下问过江摆渡,他悄悄告诉我,说是除去运费及其他成本,每石净赚五块呢。”见众人面面相觑,皆现惊诧,也顿一下,以便把握节奏,“江摆渡还说,如果不是跟我们有合同,他们能赚七块呢。我说出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一点,他们有钱。他们那么有钱,仍然与我们打官司,说明这场官司不在钱上,想必是另有原因。”
顺安此话,自是弦外有音。众人先是面面相觑,继而一齐盯向他,欲听下文,顺安却不再说话了。
沉默有顷,大把头终是憋不住:“晓迪,这原因你晓得不?”
“我也猜不透,”顺安显然等的就是这一问,“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生我们的气了,故意报复我们?”
“晓迪,”老潘接腔,“这个你要讲讲清爽了。我们既没招惹他们,也没亏欠他们,他们能生我们什么气呢?”
“这??”顺安的眼角斜向坐在他正对面的挺举,“我是不好多讲的。我只是在想,洋人如果是生气,就一定有原因。”
顺安这一斜眼,众人显然看得明白。
所有目光无不射向挺举。
“晓迪,”大把头恍然有悟,目光从挺举转回顺安,“照你这讲,难道是因为合同的事体?”
“袁师兄,”顺安抱拳应道,“我没有这样讲啊!”
“是哩!”杂货店申掌柜一拍面前桌面,“定是因为那份合同了!”
“快说说,”布店掌柜应声附和,“那份合同怎么了?”
“按照合同,”杂货店申掌柜应道,“洋人一石就得少赚两块,六万石就是十二万块。洋人少赚十二万块洋钿,自然会怨恨我们,借此机会出口恶气!”
众人尽皆大悟。许多掌柜本来就对挺举因大米出风头早有忌恨,此时无不落井下石,纷纷点头。
布店掌柜故意问道:“我想知道,这份合同是啥人签的?”
众人再次把目光射向挺举。
挺举闭上眼去。
“诸位,”俊逸见顺安把火引到挺举身上,极是不满,白他一眼,重重咳嗽一声,“大米合同是我签的,与他人无关,大家也不要曲解晓迪的意思。售米与此番赔款是两桩事体,风马牛互不相及。反过来说,恰恰是通过售米事体,麦基洋行才肯把生意由善义源转至我们钱庄。我希望大家牢记这点,不要妄自猜度。”
“对对对,”顺安急切表白,“鲁叔??鲁老爷讲得是。我只是觉得,洋人也许是生气了,至于他们为何生气,我实在不晓得,这几日一直在琢磨因由哩。”
“鲁叔,”挺举睁开眼来,目不斜视,直盯鲁俊逸,将顺安岔开的话题重拉回来,“我想问一下,按照公廨程序,这次判决是否就成定案了?”
“这倒没有。”俊逸应道,“我问过了,如果不服判决,我们可在七日之内申请复议。复议之后再经判决,才是最终定判。”
“诸位同仁,”挺举环视众人,声音不高,但一字一顿,一副毋庸置疑的语气,“我的建议是,申请复议!”
所有目光望向鲁俊逸。
凡在上海滩历过事的人无不晓得,向会审公廨申请复议、推翻洋人判决几乎等同于徒劳。在众人眼里,挺举此时提请复议,显然是为摆脱窘境。
然而,挺举的提议也无可辩驳,因为他们此来不是要争论长短是非,而是要磋商解决方案。挺举的方案虽说于事无补,却也是将死马当活马医,不定能医出个名堂呢。再说,此时此刻,真还没有比之更有力或更有利的建议。
冷场有顷,俊逸高声问道:“哪个还有高招?”见没人应腔,摆手,“散会。”
众人散场,俊逸留下老潘、大把头、顺安和挺举,带他们进经理室,叹道:“唉,反正也是无路可走了,我决定,听从挺举,申请复议,你们还有什么要讲?”
“老爷,”老潘苦笑一声,“申请的事体,我没啥意见。无论如何,我们茂记总得做出个样子,是不?”
“潘叔,”挺举神态庄重,“我们不是做出样子,我们是必须打赢这场官司!”
此言一出,莫说是老潘、大把头、顺安三人,即使是俊逸也是一震,不由自主地看向站在门口的齐伯。
齐伯不动声色,仍如竖枪一般。
“鲁叔,”见挺举有意与老潘打擂台,顺安赶忙圆场,“小侄觉得,挺举阿哥方才所言,是针对外人的,并非一定要打赢官司。阿哥的意思,其实与师父所讲是八九不离十。”又看向挺举,“阿哥,我们这场官司,是给外人做个样子,让他们看看,我们努力了,我们没犯软蛋。至于公廨哪能个判法,我们也没办法,是不?甭讲是我们了,就连朝廷也拿洋人没办法,是这理不?”
“鲁叔,潘叔,”挺举没睬顺安,顾自看向俊逸和老潘,“我对会审公廨不太了解,这想问一下,公廨里都有啥人?作判决的又是啥人?他们是哪能个判决的?”
鲁俊逸看向老潘。前几日听审,是老潘代表茂记去的。
“是这样,”老潘解释道,“会审公廨有会审主官一人,副官六人,设有秘书处、华洋刑事科、华务民事科、洋务科和案卷室。其中,会审主官是洋人,副官中,有四人是洋人,两人是华人。我们的案子非刑事案,划归洋务科审理。也就是说,全部由洋人审理!”
“这??”挺举略怔一下,“复议也是洋务科审理吗?”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我对公廨原本一无所知,只是因为这档子事体,才晓得一点儿。听说涉洋案件,很少有提请复议的。”
“我打探过了,”俊逸接过话头,“涉华案件如果申请复议,就须由陪审官出面裁决。陪审官为二人,一是外国领事,二是中方谳员。中方谳员由道台任命,专司华人案件。如果涉洋,就须外国领事参与会审。”
“中方谳员是谁?”
“叫沈先农,是道光举人,在公廨尽职二十多年了。”
“人品如何?”
“吃不准他,听说是个老油条,早年去英国习过洋人法律,甚通洋务,就为官来说,他比袁道台资历还老,照理说早该提升了,可他这个谳员位置,没人能代,洋人也离不开他。”
挺举闷头思考一时,抬头说道:“鲁叔,如果你放心,我愿去拜见一下沈谳员,向他提请复议!”
“我也是这意思。”俊逸点头应道,“提请复议,必须经过沈谳员。你们去比我去合适,我去了,就没个回旋了。”转向老潘,“老潘,你带挺举去,成不?”
“这??”老潘苦笑一声,“我见过沈谳员,觉得这人不太好说话,脾气也怪,跟他话不投机哩。”
“鲁叔,”挺举看下顺安,“我和晓迪一道去吧。涉及洋行,晓迪熟悉。”
看到师父不想蹚这池子浑水,挺举却硬要扯上他,顺安大是不满,却又不能讲什么,咳嗽一声,在下面踢他一脚。
“也好,”俊逸转向顺安,“晓迪,你辛苦一趟。”
“我??”顺安被逼到墙角了,只得点头,“欧凯,小侄听鲁叔的!”略顿一下,“鲁叔,你介了解沈谳员,他这人可有嗜好?”
“听说是个戏迷。”
顺安挠挠头皮,吧咂一下嘴皮子。
“正好哩,”挺举顺口笑道,“见谳员了,你就给他唱一出!”
“阿??阿哥!”顺安正在生挺举的气,以为他这是在故意揭他老底,满脸潮红,跺脚道,“啥人会唱戏了?你??你哪能乱讲哩?”
“好好好,”挺举意识到了,赶忙纠正,“是我讲错了。走吧,我们这就去,免得他去??”本要说出“看戏”二字,急又憋住。
俊逸自是不晓得原委,交代几句细节,又从柜中取出一个礼盒,递给顺安道:“晓迪,你把这个拿上。这是上好的长白山老参,值五十两银子。”抬腕看下时间,见时已过午,“快去吧,上海的戏多在后晌开场,看戏前他的心情最好!”
挺举、顺安不敢耽搁,出门叫了两辆黄包车,一路小跑地赶赴会审公廨。
会审公廨位于北浙江路段(今浙江北路),是很大一片府院。二人在路口下车,打听到沈谳员的宅第不在公廨,而在一个街区之外的另一块街区,遂一前一后,沿北浙江路大步流星地急赶过去。
步行也就一刻钟。
眼见走到北浙江路口,路上一直阴沉着脸的顺安陡然住步,冷不丁说道:“阿哥,我必须对你讲个事体。”
“讲吧。”
“是三个事体。”
“欧凯。”见他脸色阴沉,表情严肃,挺举觉得奇怪,笑一下,学他的洋腔缓和气氛。
“第一个,从今往后,你不能当着我的面再在别人跟前提到戏字。”
“欧凯。”
“第二个,从今往后,你不能啥事体都要扯上我,如果一定要扯,得事先和我商量一下。”
“欧凯。”
“这第三个,是我须得向你解释的。方才议事辰光,我讲的那些话,不是有意针对你的,你甭误解。”
“哦?”挺举盯住他,半笑不笑道,“你都讲到什么话了?”
“就是??”顺安脸上一涨,“你晓得的,你全都晓得的!我发誓,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全让鲁叔讲清爽了!”
挺举扑哧笑了。
“阿哥?”
“啥辰光了,看你还在扯些什么。”挺举指指前面,“沈谳员家这就到了,你该去琢磨哪能个说辞才是!”
“这??”顺安怔了,“是阿哥要来,是阿哥硬拉我来,哪能要我琢磨说辞哩?”
“你呀,”挺举指点他的鼻子,“我是在替你圆场,替你跑腿,晓得不?我是谷行掌柜,你是钱庄跑街。眼下出事体的不是谷行,是钱庄,出的又是涉洋事务,负责联络洋行的又是你,这事体与你哪能脱得了干系呢?”
“这??”顺安语塞了。
“阿弟,此地不是谷行,不是卖米,钱庄的事体我是外行,只有你懂,见沈谳员,自然是你打头阵。我来,不过是陪陪你,为你壮个胆!”
“可??是你在鲁叔跟前夸下大话的!”
“鲁叔为这事体几天几夜没睡好觉,大家谁也拿不出好主意,你讲讲看,我不这般讲,你能拿出好办法吗?”
顺安咂巴几下嘴皮子,又闭上了。
二人又走几步,顺安紧赶上来,赔个笑道:“阿哥你讲,见到谳员大人,我该哪能讲哩?”
“嘿,”挺举斜他一眼,“你这嘴巴不是一向抹过蜜吗,该讲什么哪能让我来教哩?快走吧,免得谳员大人去看戏了。”
沈宅非私宅,是道台府专为中方廨员盖的官邸,一溜儿五座,数沈谳员的最大,前后三进院子。
二人按响门铃,一个丫鬟开门,瞄他们一眼,见顺安手提一个大礼盒子,便笑逐颜开,问明因由,禀过主人,引二人直入客堂。
二人来得恰到好处,沈谳员已经换好服饰,心情果然不错,嘴里哼着曲儿,似乎是在等候接他去看戏的马车。
顺安在前,脸上堆笑,深鞠一躬道:“晚辈傅晓迪见过谳员大人!”
“傅晓迪?”沈谳员朝他点下头,目光落在他身后的挺举身上。
“晚辈伍挺举见过谳员大人!”挺举也鞠一躬。
“二位是??”沈谳员上下打量他们一阵儿,欲言又止。
“回禀大人,”顺安又是一躬,“我们是茂升钱庄的,此来冒昧求见大人,大人能够拨冗召见,我俩感谢不尽。”说着双手呈上参盒,“这盒长白山老参是我家鲁老爷特意奉送大人的,些微薄礼,难成敬意,望大人笑纳!”
沈谳员略一拱手:“谢谢你家老爷了。”接过礼盒,审也没审,放在身后几案上,指指凳子,“二位请坐。阿凤,上茶!”
引他们进来的丫鬟早已端上两杯茶水,摆好,退下。
顺安、挺举于客位坐定。
“你二人来,可为那起讼案?”沈谳员笑眯眯地看向二人。
“是。”顺安拱手应道。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是哩。”顺安赔笑道,“只是我家老爷对此判决有不同看法,让我二人前来求告大人,看看能否申请复议!”
“哦。”沈谳员点下头,“复议的事体,照程序是可以的。判决后七日之内,涉案双方均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沈大人,”顺安又是一笑,“我二人来,不仅仅是为复议的事体,是另有事体相求。这宗案子牵涉面较大,我家老爷不方便亲自登门。不过,我家老爷特意吩咐我俩,要我俩恳请大人务必斡旋,与洋人领事交涉,看看能否改判。无论成与不成,我家老爷都有厚报!”
“唉,”沈谳员长叹一声,摆手道,“厚报也好,薄报也罢,于老朽都是奢求。你二人可以回禀你家老爷,我只能为你们申请复议,至于改判之事,也让他不可奢求。”说着以杯盖拂茶,歪头看向二人,“二位还有其他事体吗?”
拂茶意在赶客,顺安下意识地看向挺举。
“沈大人,”挺举拱手道,“晚辈有事体请教!”
沈谳员按住杯盖:“请讲。”
“既然是复议,也就存在改判的可能。大人为何不让我们有此奢求?”
“呵呵呵,”沈谳员有点惊讶,盯他一阵,半是苦笑道,“你好像是刚来上海的吧?”
“这有关系吗?”
“这么讲吧。”沈谳员直盯挺举,晃着头道,“老朽进公廨已有二十余载,由书记做到谳员,亲手办理讼案逾千起,但凡涉及华、洋,华人未曾有过一起胜讼,也少有人申请复议,即使申请,也从未发生过改判先例。”
“大人是说,公廨不是讲理之处?”
“唉,”沈谳员又是一叹,有点不耐烦了,皱眉道,“哪能对你讲哩?公廨是个可以讲理之处,但它是为洋人讲理的,听清爽没?”说着将杯盖合上,站起来,“若无他事,老朽这要听戏去了!”
“大人且慢,”挺举伸手拦住,“晚辈还有一问!”
沈谳员长吸一口气,复又坐下,脸色明显不悦:“讲吧。”
“请问大人,何为谳员?”
“这??”沈谳员勃然震怒,忽身站起,“这跟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挺举稳稳坐定,振振有词,“大人息怒,请听晚辈一言。据晚辈所知,谳员是受道台委派,在会审公廨与洋人法官共同审理华、洋讼案的朝廷命官。洋人法官自为洋人谋事,作为华方谳员,如果永远只是陪坐,沈大人一坐二十余年,心里甘吗?坐得定吗?”
“你??你??”沈谳员手指发颤,指向挺举,气结。
顺安脸色煞白,急扯挺举。
“大人息怒,”挺举根本不睬顺安,“晚辈是在为大人着想。茂升钱庄可以损失一万两银子,可大人您呢?大人自称老朽,再过三年、五年,抑或八年、十年,大人必将离开公廨,告老还乡。那辰光,大人儿孙满堂,倘或哪个不晓事体的孙子、孙女闲问大人,老阿公,听说你是上海滩的大法官,专审洋人,为我们中国人主持公道。老阿公你讲讲看,你是哪能个审判洋人、为我们中国人主持公道哩?请问大人作何回答?”
沈谳员一屁股跌回座上,额头汗出。
“大人请看,”挺举从袋中摸出一张报纸,“麦基洋行讼茂升钱庄一案,已不再是寻常讼案,它已上升为公众事件。认票不认人是钱庄恒久的规矩,洋人与钱庄做生意几十年了,早已晓得。麦基洋行监守自盗,不讲公理在先,却又自恃强权,起诉茂升,这是典型的蔑视公理,仗势欺人。公廨既然是讲公理之处,大人作为会审公廨的唯一中方谳员,与洋人公使平起平坐,将此讼案如何复议,沪上会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
沈谳员掏出丝绢,不停擦汗。
“沈大人,”挺举起身,深深鞠躬,“晚辈年幼无知,言语冒犯,望大人海涵。晚辈只是想说,洋人是人,华人也是人。洋人不把我们华人当人看,我们华人却不能自我作践,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哪!”
“先生尊姓大名?”沈谳员又擦一把汗,盯住他问。
“晚辈伍挺举,不敢在大人面前称尊!”
“伍先生,”沈谳员缓缓起身,向挺举深鞠一躬,拱手道,“我沈先农谢谢你了,你为我上一大课,谢谢你了!”
“晚辈告辞!”挺举鞠躬回礼,与顺安一道,扬长而去。
一出沈谳员大门,顺安就发作了,手指挺举,气得说不出话来:“伍挺举,你??你畅快哩!你激昂慷慨,你代表正义,你??”
挺举没有睬他,顾自闷头往前走去。
“听清爽没,”顺安追上几步,一边走,一边数落,“沈大人是哪能讲的?”学沈的语调,“‘我沈先农谢谢你了,你为我上这一大课,谢谢你了!’我问你,这话哪能解哩?沈大人是六品谳员,比县太爷还大一级,你算老几,敢给沈大人上课?我费尽心思,这又搭上鲁叔一盒长白山上好人参,五十两银子,让你全搞砸了!”说着重重摇头,长叹一声,“唉,我的好阿哥呀,你叫我??这回去了,哪能个对鲁叔交代哩?”
然而,最终的判决却大出顺安所料。
一周之后,会审公廨宣判,洋人陪审官(英国领事)亲自宣布最终判决,呜里哇啦一阵,沈谳员方才起身,念判决书的中文版:“??麦基洋行内部职员监守自盗,过失在先;茂升钱庄在支付巨额庄票之前未能及时通报洋行,过失在后。有鉴于此,经过复议,议定涉案双方各自承担涉案金额之半数,茂升钱庄当于判决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麦基洋行失银五千两。此判。”
由于媒体的传扬,上海各界都在关注此判,到场的各家报刊记者有数十人之多。
沈谳员念完判决,在场华人无不惊喜交集,起立鼓掌。早已扎好架势的各路记者更是纷纷记录、拍照,灯光闪烁。
判决宣读完毕,麦基微笑起身,在照相机及记者的围堵之下落落大方地走到俊逸跟前,伸出手道:“Congratulations to you, Mr. Lu! A law suit is a law suit, business is business. You are still my business partner.”
麦基讲得太快,鲁俊逸没有听懂,看向里查得。
里查得翻译道:“鲁先生,祝贺你。讼案是讼案,生意是生意。你仍旧是我的合作伙伴。”
“欧凯,欧凯,”俊逸双手握住麦基,呵呵笑道,“也祝贺你了!我很乐意与你做生意!”
洋人纷纷散去,沈谳员迟疑一下,缓步走到挺举跟前,拱手道:“非常遗憾,伍先生,但我已经尽力了!”
伍挺举鞠一大躬:“晚辈晓得,谢大人了!”
鲁俊逸正要抽身过来,感谢沈谳员,谳员却视而不见,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晃地缓缓走出公廨。
望着沈谳员的背影,顺安大怔。让他有所不解的是,为什么伍挺举那样子骂他,那样子待他,沈老头子非但不记恨,反而对他恭敬有加?
此番复议,会审公廨改判洋行失理在先,算是破天荒了。第二日,上海多家媒体都在报道此事,《申报》更在头版显要位置刊载鲁俊逸与麦基经理握手言和的巨幅照片,一时间,茂记大战洋行,打成平手,上海滩华界为之震动。
看到铺天盖地的溢美之词,茂记上下无不兴奋,鲁俊逸更是荣光无限,心情大好。是日中午,俊逸特别在南京路的一家豪华中式饭店里置下酒宴答谢沈谳员,使顺安去请,却被谳员婉言谢绝。
然而,饭局已定,俊逸不便撤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茂记八大把头及所有掌柜全部请到,欢庆这一巨大胜利。
宴席上,杯盘狼藉。
挺举却一杯未喝,坐在一侧默不作声。
挺举申请复议成功,既出老潘意外,也让他内中五味杂陈,略略一想,决定移花接木,将这份功劳揽到弟子顺安身上,便冲顺安举酒贺道:“晓迪呀,师父万没想到你介有能耐,竟然连铁案也翻得动,讨回五千两银子不说,也为我们茂记打出名声来了。我都看了,报纸上沸沸扬扬,全都在张扬这事体哩,尤其是那张大照片,嘿,老爷与洋大人膀子挨膀子,手还握在一起,神气着哩。这报上讲,洋人与中国人打官司,双方战成平手,这在会审公廨是破天荒哩。来来来,你算是为师父争脸了,师父敬你一杯!”
顺安就坡下驴,举酒应道:“师父褒奖,弟子愧不敢当!此番复议成功,全在鲁叔洪福齐天,师父教导有方,弟子不敢居功!”
众把头、掌柜见老潘这么说,也都以为是顺安的功劳,纷纷向他敬酒,独把挺举晾在一边。
俊逸看不过去了,亲手为挺举斟一杯,递给他道:“挺举,来,鲁叔敬你一杯!”
“鲁叔,”挺举推开酒杯,“这杯酒我不能喝!”
“哦?”俊逸惊愕了,“为什么?”
“因为它的味道太苦了。”挺举缓缓起身,向众位抱拳,“鲁叔,潘叔,还有诸位同仁,你们喝吧,我有点不大舒服,先走一步。”言讫,大步出门。
挺举回到茂平,心里像是堵着什么,越坐越闷,干脆起身出门,沿大街信步走去,几乎是本能地来到清虚观里。
道人似是早已候着他,见他闷头进来,也不招呼,顾自拿了几炷香,跟在后面。
“道爷,”挺举觉出来,顿住步子,对他苦笑一下,“今朝不进香了,随便转转。”
道人点点头,放下香,返回门房。
挺举信步走到三清殿,见门前既无看相长者,也无阿弥公,略觉失望。
挺举迟疑一下,迈上台阶。刚跨一步,觉得背上一麻,似有一物击来。挺举打个惊怔,回头看去,什么也没有。朝地下一看,见是一粒桐子在地上蹦跶。
此处并无桐树,这样的桐子只在外面的马路上才有。挺举觉得奇怪,又看看四周,并不见异常,抬腿复上台阶,刚动一步,又是一粒桐子。这次是在脖颈上,打得较重。挺举回头再看,仍无一人,只有一粒桐子在台阶下面的地面上滚动。
挺举摸摸脖颈,索性坐在台阶上。
四周一个人也没,一片死寂。
挺举凝神苦思,不得其解,起步又朝上走,刚上一个台阶,又是一粒桐子,这次正中头顶。
挺举顿步,朗声说道:“何方高人,请现身赐教!”
没有一点儿回应。
挺举摸摸头皮,极是纳闷,就试探着再往上走,两耳警惕地倾听四方。
没有桐子了。
挺举一直走到台阶的最上级,回首又看四周,见仍无动静,这才转身进殿,在三清爷的像前跪下,闭目冥想。
就在此时,他的后脑勺上又中一粒桐子。
这一次,挺举纹丝不动。
又是一粒。
挺举仍旧不动。
又一粒飞来,正中后背。许是这一次太重了,挺举情不自禁地哎哟一声,忽身跳起,见身后是两个桐子和一粒小石子,捡在手里把玩一阵儿,复转身,又跪下去。
四周静得离奇,挺举的心也跟着静下来。
静下来,就听到动静了。就在身后传来极其细微的声响时,挺举重重咳嗽一声,镇定地说:“出来吧,我晓得是你了!”
外面静一阵子,一个声音飘进来:“嗨,傻小子,你哪能晓得是本小姐哩?”
挺举被她的声音吓得打个哆嗦,回身见是葛荔,又惊又喜,激动地叫道:“是??是你!”
“咦?”葛荔怔了,“方才你不是晓得了吗?”
“我??”挺举结巴起来,“是??小姐??”
“嗬,”葛荔恍然悟了,“原来你是蒙我的呀!嘿嘿,想着你傻哩,倒是本小姐看走眼嗬。好好好,算你赢一局。喂,本小姐问你,到此地做啥?”
“我??随便转转。”
“嘿嘿,随便转转?还想蒙我呀!告诉你,你来此地是寻人的!”
“你??哪能晓得哩?”
“我不仅晓得你寻人,且还晓得你要寻的是啥人!”
“啥人?”
“你来是寻那个看相的老阿公,对不?”
“是哩。”
“讲吧,你寻那个老阿公,可是有卦要占?”
“是哩。”
“跟我走吧。”葛荔不再多话,扭头走下台阶,“那个老阿公正在候你哩!”
“候我?”挺举震惊了,紧跟几步,“前辈哪能晓得我要寻他哩?”
“嘿嘿,”葛荔回他一句,“刚说你不傻,你就又犯傻了。你也不想想,那个老阿公是靠什么吃饭的!”
挺举挠挠头皮,憨厚一笑:“是哩??”
自从离开宁波,尽管挺举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她的存在,但真正见面,真正面对这位梦中小姐,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在这种场合下。
出来清虚观,葛荔大步在前,挺举在后紧跟,一边走,一边欣赏她走路的样子。走有一个多街区,二人谁也没说一句话。
葛荔拐进一条略窄的巷道,顿住步子,等他走上来,与他并肩而行,边走边歪头望着他:“伍生员,咋地了?”
“不??不咋地。”挺举心里咚咚直跳。
“既然不咋地,哪能哑巴了呢?”
“你也没讲话呀。”
“我在候你话哩。”
“我??”挺举嗫嚅道,“我??其实??一直都在等你!”
“咦,你哪能讲反话哩?我走在前面,是我在等你才是!”
“不是这辰光。”
“那??”葛荔惊愕了,“啥辰光?”
“自来上海那天起。”
“哦?你等我做啥?”
“我要谢谢你!”
“为何谢我?”
“因为你把我从火神爷口中拖出来??”
“嘻嘻,”葛荔顽皮一笑,“这个倒是要谢的。要不是本小姐身手快,世界上就没你这个生员了。”说着眉头一挑,“说到这个,本小姐倒想问问你了,既然要谢,你该寻我才是,哪能这般守株待兔哩?你们读书人就是这般做事体吗?”
“我早想寻你来着,可我晓得,你不想见我!”
“咦?”葛荔来劲了,“你是哪能晓得的?”
“我总是觉得,你就在我身边!”
“嘿!你这讲讲,你是哪能觉得哩?”
“我??”见葛荔的大眼睛火辣辣地紧盯过来,挺举越发不自然了,“在??在我孤独的辰光,在我??无望的辰光,我??总是觉得身边有个人,她??就在不远处,伴着我,盯着我,我??我晓得是小姐!”
“你??”葛荔身体震颤,“哪能晓得她是??本小姐哩?”
“起初,我也吃不准,”挺举似是背书,“但那天凌晨,在谷行里,有纸头打在我背上,我见到纸头,就晓得是小姐了。”
“嘻嘻,”葛荔假作镇定,“不过是扔个纸头嘛,你哪能证明她就是本小姐呢?”
“能证明的!”挺举语气肯定,“因为我晓得,世上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子待我!”
葛荔全身又是一阵震颤,勉强稳住神,化作扑哧一笑:“是哩,伍生员,你的直觉不错,是本小姐在一直盯你哩!”
“这??”挺举迟疑一下,稳住心神,“请问小姐为何一直盯我?”
“因为你欠我一笔旧账!”
“是哩,”见她这般应对,挺举倒也泰然了,“那笔旧账在下也是记着的。请问小姐,在下何时清偿为妥?”
“这个嘛。”葛荔完全恢复自然了,“就要看本小姐的心情喽!”
“在下恭候。”挺举朝她拱一拱手,“敢问小姐,你是哪能认识那位老前辈哩?”
“老前辈?”葛荔眉头又是一挑,“你讲那位看相的吧?他是本小姐的老阿公呀!”
“啊?”挺举愕然,“小姐是??”
“说你是书呆子,你甭不服气!”葛荔指着他的鼻子数落道,“介许多辰光,介大的恩情,你口口声声要寻本小姐谢恩,却连恩人的名姓都不晓得,这叫什么来着?口口声声只叫小姐,天底下的小姐多去了!”
“我??”挺举急忙拱手,“敢问小姐芳名?”
“你可以叫我葛荔,葛藤的葛,荔枝的荔。”
“葛荔?”
“原本是叫葛藟,草头下面三个田字。”
“在下晓得,”挺举顺口应道,“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咦?”葛荔怔了,“你晓得此诗?”
“这是《诗》中的一篇,取自王风。敢问小姐此名,可与此诗相关?”
“正是。”
“那??”挺举盯她一会儿,“小姐不会??是个孤儿吧?”
“咦,”葛荔愕然,“你哪能晓得本小姐是个孤儿哩?”
“此诗为流浪乞子之歌,不忍卒读。”
“为啥不忍卒读?”
“葛藟本为野葡萄,此诗喻无依无靠之乞子,就如山中的野葡萄,攀枝附岩,寄人篱下,受尽颠沛流离之苦!”
“嘻嘻,”葛荔心里一酸,回他一笑,“还好本小姐没有那么惨!”
“是哩,”挺举点头应道,“我观小姐,当是乐天达观之人,甚为羡慕哩。敢问小姐,何又易名葛荔?”
“这倒是个小故事哩。”葛荔呵呵乐道,“这名字是阿弥公起的。阿弥公姓葛,平生就爱吃野葡萄,为我取名葛藟。在我八岁辰光,阿弥公吃野葡萄时酸坏牙了,不再喜欢野葡萄,喜欢上荔枝了,就把我这名字改了。”
“呵呵,”挺举笑了,“这倒有趣。阿弥公又是何人?”
“我还没讲完呢,你就打岔!”葛荔白他一眼,嗔怪道。
“你讲。”
“这是我的其中一个名字,你还可以叫我另一个名字。”
“啥名字?”挺举来兴致了。
“申小荔子!”
“申小荔子?”挺举不解地望着她。
“这是老阿公起的,老阿公姓申。”
“你有两个老阿公?”挺举大怔。
“是呀!”葛荔调皮地歪头看向他,“不服气是不?”
“服气。”
“服气就成。”
“这??”挺举略略一顿,半是打趣她,“在下是叫你申小荔子呢,还是叫你葛荔呢?”
“嘻嘻,”葛荔慧黠一笑,“这个嘛,你就得视情了!”
“视情?”挺举不解。
“哎呀,你哪能介笨哩!”葛荔嗔他一眼,“视情就是,见到阿弥公,你得叫葛荔,见到老阿公嘛,自然就是申小荔子了。”说着抬头一望,指向前面一处黑漆门楼,“到了!只顾与你瞎扯筋,害得我差点走过头哩。”
这是一座古宅,有些年头了,单看外观,既典雅,又气势超凡。联想到她的老阿公不过是个看相的,挺举吃一大惊,因为眼前这座宅院与他想象中的算命人的居所完全不同。
“呆鸟,”葛荔推开院门,“愣在外面做啥?没见过老宅子呀。”
“这??”挺举仍没反应过来,“这是你家?”
“咦,难道是你家不成?”
“介气派的房子!”
“再气派也赶不上你们鲁家的大宅院哪。快进来,老阿公候你来着!”
挺举走进院门,越发错愕。院子不大,但极是整洁,摆放着各种花卉、盆景,一看就晓得主人是个极雅致的人。
挺举跟在葛荔身后,脚步没停,直进中堂。
一到中堂,挺举眼前蓦然一亮。中堂上悬挂一幅字画,画在中央,画面上是个怪老头,仰天而嘘,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似怒非怒,似喜非喜,表情稀奇古怪,完全不同于别家堂画。画两侧各悬一个条幅,构成一副对联,上联是“看遍天上星辰”,下联是“阅尽人间稀奇”。书法苍劲,力透纸背,与画面相得益彰,形成绝配。
挺举的眼球被这幅字画紧紧攫住了。
“嗬,”葛荔打趣他道,“到底是学问人哪,一进门就看书画。”
挺举似是没有听见,目光滞留在书画上。
“请问生员,看出名堂没?”
“镜湖双叟!”挺举脱口而出。
“什么镜湖双叟?我问你看出名堂没?”
“这书画??”挺举的两眼仍旧盯在书画上,“可是镜湖双叟所作?”
“镜湖双叟?”葛荔怔了,“啥人是镜湖双叟?”
“就是两位书画前辈,一书一画,皆是前辈大家!”
“哈哈哈哈,”葛荔大笑起来,“什么前辈大家?叟是老头,双叟就是两个老头,对不?”
“是哩。”
“要是此说,倒是应上哩。”葛荔的俏嘴巴一努,“喏,一书一画,两个老头全在这里,一个不少呢!”
挺举顺着她的嘴角望去,这才看清楚近在身边的情景:一张木榻上,盘腿坐着申老爷子和阿弥公。二人各守榻的一端,中间摆着一盘雅致的棋局,纵横棋盘上摆着几枚黑白子,显然处在开战状态。
二人各自闭目端坐,就如在大殿前一般。观表情及棋局,二人似乎不在下棋。
挺举并无别话,倒头就行拜叩大礼,礼毕方道:“晚辈伍挺举叩见二位镜湖前辈。晚辈有眼不识泰山,惭愧,惭愧!”
申老爷子眼睛未睁,缓缓说道:“什么镜湖呀,年轻人?”
“镜湖双叟,也就是二位老前辈啊!”
“呵呵呵,”申老爷子笑出几声,“年轻人,你何以一口认定我们就是镜湖双叟呢?”
“晚辈先父曾得双叟联璧书画一幅,风骨与此处书画一般无二,晚辈是以认定二位前辈就是镜湖双叟!”
“哦?”申老爷子略略一怔,“你先父可否告诉你,他是如何得到双叟之画的?”
“听先父讲,”挺举应道,“二十多年前,他到杭州陪同先祖父参加大比,机缘巧合,在西湖畔上救下一个醉汉,意外得到双叟之画。”
听到此处,一直没有说话的阿弥公双手合十,脱口而出:“阿弥陀佛!”
听到这声阿弥陀佛,想到方才葛荔介绍的阿弥公,挺举豁然明朗,喜道:“前辈可是??阿弥公?”
阿弥公双手合十,没再吱声。
“年轻人,”申老爷子敛起笑,一本正经道,“你看错了。老朽不晓得什么镜湖不镜湖的。墙上所题,是我二人涂鸦之作,聊以打发寂寞的。你所说的双叟,倘若真有,怕也不在凡尘了。”
“可??”挺举怔了,“这书,这画?”
“年轻人,是你见识少了。在大上海,似我等题字作画之叟,数以百千,挂在家中自娱尚可,若是挂出去供人雅赏,可就贻笑大方喽!”
“这??”挺举有点茫然,不由自主地再次看向中堂字画。
“年轻人,”申老爷子一字一顿,“你来此地,不会是为求证镜湖双叟的吧?”
挺举这也想起此来根本,拱手道:“晚辈??遭遇一事,苦思无解,特来寻访前辈,求前辈点拨!”
“遭遇何事了?”
“麦基洋行诉茂升钱庄一案。会审公廨一审判决茂升败诉,茂升申请复议,公廨改判涉案双方各自承担五千两。会审公廨自成立以来,涉及华洋讼案,华人从未胜诉。此番茂升虽未完胜,却也没有完败,钱庄上下欢喜,上海商民同庆,唯独晚辈诚惶诚恐!”
“你为何惶恐?”
“因为庄票。庄票是钱庄根本,认票不认人是钱庄规矩,洋行与钱庄在合作之始,就已知晓。洋行内部监守自盗,却将损失转嫁于钱庄,而会审公廨一味偏袒洋人,混淆是非,践踏公理,无视庄票信用。如果此案成立,庄票之神圣将不复存在,后果不堪设想。”
“哦?”申老爷子微微一笑,望着他道,“你且讲讲,有何不堪后果?”
“上海所有洋行无不通过钱庄对华商做生意,华商也通过钱庄沟通洋行。钱庄是沟通华、洋的媒介。钱庄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庄票,此判决表面上是一万块洋钿,实际是对庄票尊严的践踏。此例若开,庄票信用不复存在,钱庄业将遭灭顶之灾!”
“晓得了。”申老爷子点点头,“还可复议吗?”
“是终审判决。”
申老爷子陷入沉思。
挺举也闭上眼睛,依旧跪着。
“小荔子,”申老爷子突然出声,“拿纸笔来!”
葛荔拿来笔墨,将笔递上,送上砚台,将一张宣纸交给挺举:“拿好!”
挺举双手拿纸,眼睛大睁,紧盯申老爷子的手。
申老爷子饱蘸墨汁,只见笔头晃动,却听不到笔纸摩擦所发出的嚓嚓声,纸亦丝毫未动,就好像是对空舞笔一般。
挺举正自惊愕,申老爷子已经放下笔,复又闭眼。
挺举低头再看宣纸,上面竟然渐渐现出“断臂立雪”四个大字,每一道笔画无不苍劲有力。
挺举惊得呆了,许久,喃喃道:“神笔呀!若非亲见,岂能相信?”
“嘻嘻,”葛荔瞥他一眼,“伍掌柜,伍生员,字已求到了,老阿公这要下棋哩!”
挺举醒悟过来,审视四字,却是茫然无解。再看申老爷子,已然入定,根本没有再说话的意思。看那阿弥公,也是一般模样。
挺举看向葛荔:“小姐,在下??”
葛荔将砚台、毛笔拿到中堂几案上,放下,拿个鸡毛掸子返回。
“还不走人呀?”葛荔扬起鸡毛掸子,“生员大人,总不能让本小姐赶客吧!”
挺举翻身站起:“小姐,我??”
葛荔扬掸子逼他出门,一直赶到大门外。
“小姐,”挺举回身,拱手道,“在下愚笨,还求小姐问问前辈,指点一二!”
“什么小姐?本小姐难道没有名字吗?”葛荔劈头一顿数落,“还是大生员呢,哪能介笨哩?既然庄票不能做数,不给他们开也就是了!”话音落处,嘭地关上院门,又从里面闩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