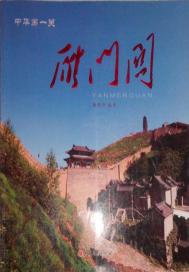鲁碧瑶恋父生怨?甫顺安妒兄励志
过完春节,麦基一行从印度凯旋。从声势上看,麦基洋行发了大财。
回到上海的第二日,麦基派里查得送给茂记三张请柬,邀请鲁俊逸、伍挺举和傅晓迪参加他的家宴。
顺安的请柬是师兄庆泽转给他的,说是辰光不早了,要他快去鲁宅,与老爷一道赶往麦基宅第。看到庆泽的语调和眼神尽皆酸溜溜的,顺安颇为受用,美言安抚师兄几句,装起请柬,顺道拐进一家西装店,购下一套早已瞄好的新装,美滋滋地回到鲁宅。
顺安的新房间很大,宽敞明亮,配有衣柜、书架、衣帽架和一张写字台,另有笔墨纸砚和一架算盘。
顺安在写字台前小坐一会儿,从跑街包里掏出请柬,眯着眼缝儿欣赏。请柬上面满是他不认识的洋字,只有三个汉字,“傅晓迪”,写得虽不在体,甚至歪歪扭扭,倒也不失工整。看样子,想必是麦基手迹。
洋人设私宴招待茂记,只请三人,鲁叔、挺举和他傅晓迪,这是天大的面子。顺安看着请柬美一会儿,将新买的衣装取出来。
这是一套深灰色呢绒西装,配一顶蓝黑色毡帽,还有衬衫和领带。顺安穿戴齐整,在屋子里小转一圈。尽管在店里早已试过,顺安仍旧不放心,想再看看效果,房间里却无镜子。顺安灵机一动,将铜脸盆里倒满水,搁到地上,待水静止,俯身欣赏水中的倒影。
顺安正在盆边顾影自赏,院中一阵脚步声近,经过他的门前,在另一扇门前落定。不一会儿,听到开门声。
是挺举。
想到促成这桩好事情的是挺举,顺安不免感激,将请柬小心纳入西服袋中,扭开房门,拐进挺举房间。
挺举的房门敞着,房间在大小上与顺安的完全一样,家具也相差无几,只是少了个衣柜,多了个书架。桌子上同样放着一张请柬,是齐伯刚刚交给他的。
顺安进来时,挺举正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袱,解开来,取出一件长衫,用力连抖几下,显然是要抖得舒展些。
“阿哥,你这是??”顺安怔了。
“呵呵呵,”挺举抖过,又将长衫摊在床上,用手平整几下,满意地笑了,穿在身上,“阿弟,你来正好,帮我看看,挺括不?”
“阿哥呀,”顺安急了,“你这??太土气了!入乡随俗,懂不?洋大人请客,你该穿上正装才是!”
“这个是正装呀!”
“在洋人那儿,西装才是正装,”顺安指指自己身上,“就是我身上这种!到洋人家里,你穿长衫,就像是鹤群里立只土鸡,会让人笑掉大牙!”
“西装是洋人穿的。我是中国人,穿上洋装才叫别扭哩!”
“真是急死人!”顺安不管三七二十一,只几下就脱下他的长衫,“走走走,我这领你去,有现成的毛呢洋装,一套不过三十块。你又不是没钱,鲁叔奖你介许多铜钿,捂在袋里一毛不拔,留着泡堂子呀!”
“去去去,”挺举一把推开他,将长衫复又穿上,指着他的衣服,“就你这身破玩意儿,紧得绷身,还有那条带子,勒在脖子上,气也喘不过来,”又将宽大的袖子甩几甩,“哪有老祖宗传下的这身大褂子舒服!”
“唉,”顺安连连摇头,“遇到你这只土鸡,真正没治了。”
话音落处,听到齐伯在前院里叫他们,二人不及再说,匆匆出门。赶到前院,鲁俊逸已在等候,也是西装革履,一身笔挺!
院子里,一辆洋轿车停在正中,里查得候在打开的车门旁,恭敬侍立。几人钻进轿车,车子一溜烟儿驶出院门,拐过几个弯,转入麦基豪宅。
听到喇叭声,麦基大步迎出。车子停下,里查得下车,打开车门,伸手扶出俊逸、挺举、顺安三人。
几个人皆是西装革履,只有挺举一身秀才长衫,显得分外扎眼。
麦基走下门前台阶,顿住步子,眼睛自然落在挺举的长衫上,微微一笑,不行握手礼,反学中国人弯腰拱手,揖一个别扭的中式大礼,用生硬的中文说道:“欢迎诸位光临寒舍!”
俊逸回过一揖:“三克油麦克麦克!(Thank you much much, 多谢多谢。)”
麦基笑几声,上前握住他的手,学俊逸的样式:“三克油麦克麦克!”又上前握住顺安,“三克油麦克!”
顺安握住麦基,声音打战:“三克油麦克麦克!”
麦基松开他,转向挺举,深鞠一躬,改说中文:“谢谢你,伍先生!又见到你,我很兴奋!”
挺举亦回一躬:“谢谢你,麦先生!”
麦基的目光落在他的长衫上:“这件服装好看,我可以买到吗?”
“你买不到。”
“为什么?”
“这是我姆妈做的。”
麦基肃然起敬,伸出大拇指:“你的姆妈,了不起!”略略一顿,脱下西装,递给里查得,又看向挺举,“伍先生,我可以试穿一下吗?”
“可以。”挺举脱下长衫,递过去。
麦基穿上,左扭右扭,手舞足蹈,咧嘴呵呵直乐。
洋人真是奇怪,一旦高兴起来,简直像个孩子。顺安傻眼了,看向俊逸,见他也在发怔。
麦基乐一阵子,这才想起待客,脱掉衣服,还给挺举,从里查得手中接过自己的衣服穿上,转向俊逸,伸手礼让道:“鲁先生,请!”
鲁俊逸等走进豪宅,见里面果然奢华,客厅里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西洋物事,看得几人眼花缭乱。
由于已到宴会辰光,麦基引领他们穿过客厅,直入一旁的宴厅。里面是个长形台桌,桌中心摆着各式西点,两侧俱是靠椅,每个靠椅前皆放一块台布,布上放着餐盘,餐盘一侧是刀叉餐具,另一侧立着一只高脚玻璃酒杯,里面早已斟好小半杯红红的法国葡萄酒。
这是一次完全的西餐。
“鲁先生,请坐!”麦基走到一侧,指着对面的四个席位,朝几人礼让。
俊逸一看,两边各有四个座位,而麦基坐在第二个上。按照礼仪,俊逸当与麦基正对,所以,就安排顺安坐在第一位,他正对麦基,坐在第二位,挺举挨他坐在第三位,最外面一位,就由里查得坐了。
几人刚刚坐下,旁边传来一阵响动,一扇门打开,麦基太太端着一盘糕点,款款走进。
麦基太太走到桌前,面带微笑,将盘中早已切好的蛋糕分散到中央餐台上,在麦基身边正对顺安的位置坐下。
几人刚落定,又是一阵响动,一个洋少女款款走出,手中端着一盘切成碎块的各式果品色拉,因拌有许多奶油,看起来黏糊糊的。
少女走到麦基旁边,给众人一个甜笑,将色拉盘子摆在桌子中央早已留好的空当里。
少女一边摆放,一边将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直盯伍挺举。
伍挺举惊呆了。
坐在她对面的不是别个,竟是天使花园里的麦嘉丽!
麦嘉丽一身盛装,宛若仙女,与她在天使花园时判若两人。
麦嘉丽看一会儿伍挺举,转对里查得,用英语说道:“Can I sit in your place?(我可以坐你的位置吗?)”
里查得笑笑,起身让位。麦嘉丽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在挺举跟前站定。里查得走到对面,坐在麦基旁边。
“Long time no see you!”麦嘉丽伸出手来,两眼如火,讲的却是中国式洋泾浜英语。
“麦??麦小姐?”挺举面红耳赤,身子不由得歪向俊逸,紧张得声音都变调了。
“耶耶耶,正是麦嘉丽。”麦嘉丽伸出手,“密斯特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我数月没见,隔了多多个秋,是不?”
“你??我??”挺举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我要谢谢你,替我照顾天使花园!”麦嘉丽话音落处,伸手拉他起来,张开双臂,给他一个熊抱。
挺举始料不及,待反应过来,已被她抱在怀里,推托不得,窘态百出。鲁俊逸、顺安从来未曾见过这般场面,看得傻了。
这是麦嘉丽特别隆重的感谢方式,麦基、麦基太太习以为常。见几人这般反应,尤其是挺举,脸上红得像喝多了酒,麦基、麦基太太皆乐起来,里查得更是大笑不已。
“鲁先生,伍先生,傅先生,我来介绍一下,”麦基敛住笑,待麦嘉丽与挺举双双坐下,指麦基夫人介绍道,“这是我太太,Madam Mac.”又指麦嘉丽,“这是我女儿,Carrie Mac.”
麦基夫人和麦嘉丽点头微笑,俊逸等三人也都抱拳致意。
“鲁先生,伍先生,傅先生,请用餐。”麦基夫人朝众人笑笑,用蹩脚的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些菜点是我和嘉丽做的,请品尝!”
俊逸冲她抱拳:“三克油,三克油(thank you,谢谢)。”
“鲁先生,”麦基举杯,亦用中文,说得艰难,似是刻意学到的,“印度人不饿了。谢谢你,谢谢你和伍先生的大米,干杯!”
众人干杯。
“鲁先生,”麦基看向俊逸,“今日我请你们三人来,一是吃饭,二是感谢,三是想和你们继续做生意!”
“欧凯(OK)。”俊逸拱手应道。
麦基示意里查得。
“鲁先生,”里查得对俊逸道,“我们总董决定,麦基洋行所有票银业务将由善义源钱庄转至茂升钱庄,这是合同文本,请鲁先生审查!”说着从包里摸出一份文件,双手呈给鲁俊逸。
面对这个意外惊喜,俊逸却似没有反应过来,一下子呆住了。
“OK?”麦基盯住他,问道。
“欧凯,欧凯。”俊逸回过神来,脸上堆笑,伸手接过合同,转递给顺安。
“为再次合作,干杯!”麦基举酒。
商务总会的新会馆三楼是总董室,长案两旁的软椅上分坐彭伟伦、张士杰、鲁俊逸和祝合义四人,长案顶端是主席位,查敬轩端坐于高椅中。
“诸位总董,”查敬轩看向几人,直奔主题,“今日召请大家来,主要是商议沪宁、沪杭、粤汉、川汉铁路的路权事宜。”
彭伟伦的位置靠窗,他微微别过脸去,看向窗外,一手中指的指节在几案上一弹一弹,但没有弹出声。
“如诸位所知,”查敬轩斜他一眼,接道,“从东北到南粤,我们的路权多被洋人拿去。此番修筑沪宁、沪杭、粤汉、川汉等铁路,洋人再次伸手,老王爷本已照准洋人所请,不料民怨沸腾,各地商会纷纷抗争。新任邮传部大臣丁大人顺应民意,先请示王爷,又与英人谈判多次,终将部分路权放还国人!”
彭伟伦扭过来,半是哂笑:“此事全都晓得了,请查总理拣关键的讲!”
“彭协理,”查敬轩回以哂笑,“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嗬!”
彭伟伦冷冷哼出一声,再次看向窗外。
“关键的就是,”查敬轩瞥他一眼,“路权分配及修筑方案。就此二者,丁大人皆有明确交代,具体请士杰阐述。”
士杰摆下手:“还是总理讲吧。”
“好吧,”查敬轩朝他笑笑,“士杰客气,我就代劳了。丁大人之意是,由于英人早在筹建沪宁铁路,合同在先,此路仍归英人督建,但沪杭、杭甬、苏杭三线,则归我沪浙苏三地商民筹建,浙、苏均已成立铁路公司,沪也决定由我商会筹组沪路公司,至于粤汉铁路,由粤、赣、湘、鄂四地商民承办,川汉铁路,则由鄂、川两地商民承办。”
彭伟伦冷笑一声:“既然丁大人已经明确交代过了,还在此地商议什么?”忽地起身,“要是没有别的事体,在下先走一步。”说完愤然退场。
众人愕然,面面相觑。
士杰、俊逸、合义尽皆看向查敬轩。
查敬轩苦笑一声,摆手:“散会。”
俊逸、合义并肩走向大门。
“今天这会,”俊逸边走边感慨,“老彭也太那个了,一点儿不给老爷子面子。”
“照理说,”合义应道,“老彭讲得也是没错。既然事体已经定下,直接宣布就是了,还让我们讨论什么?不瞒你讲,我所担心的是,这样下去,商会早晚会成为摆设。”
“是哩。”俊逸点头,“再好的事体,一到我们手里,就得变味。譬如说选举,西人是投票,我们是丢豆子。虽说丢豆子也是民主,但总让人觉得怪怪的,心里不是个味儿。”
“呵呵呵,那些框框还不是你一条一条写出来的?”
俊逸写出的并不是丢豆子,但此时对祝合义却不便解释,嘴巴动几动,又合上了。
走出大门,二人扬手别过,各自跳向自己的马车。
车夫回头:“老爷,去哪儿?”
“老地方。”俊逸闭上眼睛。
所谓老地方,就是阿秀的新居。
自阿秀悄悄来到上海,如果没有特别事务,俊逸几乎每晚都来,并在二更之后返回鲁宅应对瑶碧。
俊逸喜欢阿秀,像喜欢她阿姐一样喜欢,因为阿秀与她的姐姐阿芝在各方面均不相同,却又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他不同时期的欲望。阿芝一身大小姐脾气,为人强势,敢作敢当,为爱情不惜与同样强势的母亲决裂,于当时相对弱势的俊逸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福祉。阿秀则小鸟依人,连说话声音也是轻悠悠的,为人处事任何人都不肯得罪,对他更是爱慕有加,百依百顺,于方今已呈强势的他来说,也是上天赐予的福祉;阿秀的明眸流转、风流姿态、一颦一笑甚至吴侬软语的腔调都像极了当年的阿芝,每次见面,都让俊逸有恍若隔世的感叹与感慨,一腔对阿芝的感情与抱憾都被投注到阿秀身上。
当然,自上次回乡,尤其是在挺举到沪之后,俊逸又为喜欢阿秀寻到了一个更为紧迫的理由:早一日为鲁家生个儿子。
俊逸用阿姨备好、阿秀试过水温的水,洗去满身的疲惫、劳顿与失落的情绪。每逢此时,每逢他坐在这个安静、避世的角落,俊逸都有一种放下尘世一切的感觉。在这个充满暖意的小院里,看到阿秀为他精心备下的可口饭菜,俊逸总是心神俱歇,每一根毛发都是松弛的。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俊逸情不自禁地吟咏起诗篇,向阿秀举杯。
酒不醉人人自醉,阿秀俏脸粉红,举杯,侧身,襟袖遮面,樱唇轻启,抿一口,顾盼生情。俊逸看得兴起,不再矜持,轻舒猿臂,抱起阿秀径自走向二楼。
罗帐温暖,灯光暧昧。俊逸吻着阿秀的鬓发、眉眼、挺直的鼻尖、樱唇和酥胸,阿秀也吻着阿哥闪亮的印堂、丰厚的耳垂和宽阔的胸怀,**不止。俊逸迫不及待地要,阿秀甘心情愿地给,千般缱绻,万般恩爱,尽在默契之中。
云蒸霞退,俊逸坐起来,撩开锦被,就着灯光审视阿秀的秀丽肚皮,将脸轻轻贴在她的小腹上:“阿秀,有动静没?”
阿秀晓得他问的是什么,神色惶然地低下头去。
“不急,”俊逸轻揽阿秀,给她个笑,“你一定行的!”
“阿哥,我??”阿秀呢喃一声,盖上锦被,拉灭开关,才又接上,几乎是呢喃,“熄灯了嗬!”
黄昏时分,夜色渐渐笼罩鲁宅。
晚餐备好了,放凉了,但碧瑶没心去吃。
秋红从前院回来,咚咚咚踏上闺楼,刚要张口喊她,隐约听到哭声,紧忙捂住嘴唇,蹑手蹑脚地近前,见碧瑶正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面,看着黑乎乎的夜空,一边啜泣,一边声情并茂地吟咏:“人去,人去,影也留他不住??”
秋红怔了。
碧瑶将“影也留他不住”连吟数遍,捂住嘴唇抽泣。
“小姐?”秋红轻声叫道。
碧瑶却似没有听见,拭下泪水,继续望向窗外,接着吟诵:“??晚来风倦帘旌,又见花前月明。明月,明月,何苦阴晴圆缺。”提高声音,悲泣,“明月,明月,何苦阴晴圆缺??”拉开长腔,哭得愈见悲切,“何苦阴晴圆缺啊??呜呜呜??”
“小姐?小姐??”秋红吓坏了,冲到她跟前,摇着她胳膊大叫。
吃她一叫,碧瑶倒被吓到了,止住哭,不无嗔怒地扭头看她。
“小姐,你??哭啥哩?”秋红赔小心道。
碧瑶抹去眼泪,像是换了个人:“咦,我啥辰光哭了?”
“方才呀,”秋红有点愕然,“小姐哭得好伤心哩!”
“去去去!”碧瑶白她一眼,厉声责道,“你懂个屁,我这是在吟诗!”又将摆在窗台上的一本书连抖几抖,“就是这本,懂不?”
“小姐,”秋红笑了,“这本书我晓得的,是啥个小姐写的,对不?”
“是吴藻,方才我念这首,叫转应词,写得好哩!”
“啥叫转应词?”
“转应词就是转应词,”碧瑶不屑对她解释,“讲给你也是不懂!”猛地想起什么,“咦,方才让你做啥事体来着?”
“嘻嘻,这不是正要向小姐禀报哩!”
“快讲!”
“老爷依旧没回来,你看,书房里漆漆黑!”
“就你眼尖!”碧瑶生气了,“我早瞧见漆漆黑哩!我要你去守在大门口,守没?”
“守了,”秋红又是嘻嘻一笑,“我守好久哩,一直没见老爷个人影,这怕小姐着急,我才??”
碧瑶呆怔一会儿,吟道:“人去。人去。影也留他不住??”陡然激动,对着窗外大声叫道,“阿爸,你??你在哪儿啊??”
“小姐?”秋红让她这声喊吓坏了。
碧瑶把手中诗集朝桌上一掼,扯住秋红:“走,跟我这寻阿爸去!”
二人咚咚咚咚走下楼梯,穿过闺院拱门,疾步走到前院,直向大门外面走去。
“小姐呀,”秋红嘟哝道,“这半夜三更哩,上海介大,我们哪儿寻去?”
“我才不管哩,”碧瑶顾自前行,“我要一条街一条街地寻他!”
“小姐,”齐伯匆匆追上来,“你们去哪儿?”
“寻我阿爸!”
“小姐呀,”齐伯笑道,“老爷这就回来哩,你再等等!”
“齐伯,”碧瑶冷笑一声,“你讲实话,我阿爸究底哪儿去了?”
“商会里有事体,老爷天天忙哩!”
“商会,商会,”碧瑶气得跺几下脚,“天天都是商会!我鼻子也不信,啥事体能让他天天晚上不回家?”
“这??”齐伯支吾不出了。
碧瑶声音决绝:“齐伯,要是不放心,这就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
“你不是天天讲他在商会里吗?我们这就去商会看看!”
齐伯晓得她的脾气,不敢违拗,只好叫来几辆黄包车,径去商会,远远望见商会大楼里漆黑一团,几层楼的窗户里没有透出一丝儿灯光,只有大门处懒洋洋地守着一个门卫。碧瑶询问门卫,说是楼里的人早就走了。
“齐伯,”碧瑶黑着脸,看向齐伯,“听见没?你再睁眼看看,这楼里有人吗?我的阿爸又在哪儿?”
“这??”齐伯被挤到墙角了,只得赔个笑,“待会儿老爷回来,老头子一定问问他,究底他这是去了哪儿呢!”
碧瑶抿紧嘴唇,泪水流出。
俊逸回来时,已交二更,宅院里黑乎乎一片,只有野虫在叫。
俊逸站在前院听一会儿,径直上楼,开启书房,打开公文包,将包中物事尽皆取出,正在清理,楼梯声响,听脚步声是齐伯。
“老爷?”齐伯提着一壶热水进门,给他个笑。
“瑶儿她??”俊逸压低声,“没啥事体吧?”
齐伯苦笑一声:“闹哩。”
“睡没?”
“睡了。”齐伯又是一声苦笑,“闹到一更多。”
“唉,”俊逸回个苦笑,“这孩子,宠坏了。”将包中文件等理进抽屉,起身,“齐伯,您也睡吧。”
翌日晨起,碧瑶被鸟叫声吵醒,噌地跳下床,打开窗子,听到前院传来嘿嘿嘿的声音,知是俊逸与齐伯在打太极。碧瑶晓得,这些日来,只要不下大雨,俊逸总要跟从齐伯在前院里打几圈。听这嘿声,他们刚开始。
碧瑶听一会儿,似是想到什么,不顾洗脸,跑出闺房,沿过道溜进俊逸房中。
鲁家的三进院子实际是三排房子,前面两排是双层,后面一排是单层。前楼是客厅兼俊逸的书房、香堂等,算是鲁家门面,中间是主楼,与前楼之间形成的院子被一道花墙围起来,算是碧瑶的活动场地。主楼的底楼是库房,边上一间住着齐伯。楼上则分两部分,东面一半是碧瑶的闺房,西面一半是俊逸的居室。后排为杂院,为鲁家的厨房及闲杂物事堆放处。三排房子形成三进院落,因宅地大,园林美,布局合理,做工精细,用料考究,装饰也不错,看进来堂皇雅致。
碧瑶在俊逸的起居室里扫瞄一圈,走进卧室,见旁边衣架上挂着俊逸的衣服,床头放着他的贴身褂子。浴室外面一只小木盆里,杂乱地扔着他的换洗内衣,这辰光还没被阿姨收走。
碧瑶拿起他的内衣与褂子,嗅嗅这个,摸摸那个,又将外衣的所有口袋掏了个遍。
然而,碧瑶一无发现,所有物事都还正常。
碧瑶略觉失望,正自困惑,眼前一亮,目光射向挂在衣架上的外套,手也跟着伸出去,从衣领旁边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根长发。
这是一根属于女人的头发。
碧瑶如获至宝,面孔扭曲,怔怔地盯着它。
碧瑶将这个新发现紧紧捏在手心,得胜般回到自己房间。
挺举与顺安住在鲁家最后面的杂院里。杂院是下人住的,紧挨一条小巷,朝巷子开扇小门,由下人出入。自齐伯来后,鲁家杂院就没什么下人了,只有烧饭的张妈和陪碧瑶的秋红,因为打扫庭除之类杂役,包括门卫,齐伯全都自己做了。张妈负责三餐,还要照顾家人,平素回家居住,秋红住在碧瑶旁边,整个后园实际只有挺举、顺安二人居住。
平素上工,挺举还图方便,常与张妈出入小门,顺安则不然,若无急事,一定要走正门,因为正门不仅代言他的身份,还能使他“偶遇”小姐。尽管小姐从来没拿正眼看他,但顺安一旦操下这心,就不会轻言放弃。再说,几日前他已在三清殿前许过愿了,三清爷灵验与否,他还想一试,因而近段时间,顺安在由后院走到前院时,尤其留意。
真也神了。
这日晨起,顺安挎起跑街包,刚刚拐出后院,竟见碧瑶站在拱门口,笑吟吟地招手。
顺安吃一大惊,以为看花眼了,顿住步子,揉揉眼睛又看,见真是小姐,竟是傻了,声音发着颤:“小姐,你??叫我?”
“傅晓迪,过来呀!”碧瑶的声音轻而甜,再次招手。
顺安没动,眼前浮出碧瑶撕书的情景,不由得打个寒战。是哩,大清早这般和风暖阳,不定后面跟的就是风暴呢。
顺安诚惶诚恐地望着她,脚步没动。
“晓迪,”碧瑶急了,省去了傅字,声音发嗲,“快过来呀,人家有事体!”
顺安硬着头皮过来,头低着,不敢直视。
“看把你吓的。”碧瑶扑哧笑了,拿出一套新书,递过去,“这四本书,还你!”
见是还书,顺安倒是怔了:“还??还我?”
“是呀。我把你的心肝宝贝撕了,不该还吗?”
“那是我送小姐的!”顺安急切表白。
“嘻嘻,你介欢喜它们,我哪能夺人所爱哩?”
“小姐,你??你不晓得??我??”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晓迪,我这寻你,还书是次要,主要是求你一桩事体!”
“事体?”顺安回过神来,嘴皮子功夫也上来了,喜道,“小姐,你万不能说求。有啥事体,只要吩咐一声,晓迪赴汤蹈火,在所不计!”
“太好了。”碧瑶给他个笑,“我想让你盯个梢!”
“盯梢?盯啥人?”
“我阿爸!”
天哪!顺安不由自主地连退几步。
“怎么了?”
“是??是盯鲁叔?”
“是呀,盯我阿爸呀。”
“盯??盯鲁叔做啥?”
“这你管不着,只管盯住他就成。”
“我??”
“干得好,我有赏!”
“赏??赏??”
“就是报答你!”
听到“报答”二字,顺安打个惊怔,好像从一场噩梦里完全醒来:“我??我要上工,跑生意??”
“哎呀,”碧瑶急了,“你这脑瓜子哪能介笨哩,我又不是让你去做跟屁虫,只是让你傍黑收工时远远跟在他后面,看他都在忙些啥事体!”
“这??”顺安抓耳挠腮,眼珠子乱转,看样子似在寻求脱身。
“傅晓迪!”碧瑶猛地敛起笑,脸色黑沉,嗲味自也没了,“我是瞧得起你,才把这桩好事体让予你做。你若不肯,我就寻别人去了。谷行里想必有人肯做这事体哩。”说着转身就要走人。
听到“谷行”二字,顺安急追两步:“小??小姐,晓迪??肯哩!”
“这就是了。”碧瑶回转身,改作笑脸,“你要记住,无论我阿爸去哪儿,做啥事体,你都得一五一十向我报告,一星点儿细节也不可落下!”
接下来几日,顺安开始留意鲁俊逸的动向,发现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商会会馆。顺安打探门卫,方知商会里近日正在筹备修建铁路,且鲁俊逸是负责为杭甬铁路筹款。听到向老家修铁路,顺安不由得一番欢喜,但这欢喜在联想到甫家的破院子及那样一对爸妈后迅速退去,重又回到心上人交给他的差事上。
在第三日苍黑时分,顺安再次赶到商会,靠在斜对面房子的影壁一侧,候至天色黑定,望见俊逸、祝合义、查锦莱诸人有说有笑地从会馆大门健步而出。
顺安一个闪身,躲在一棵树后。
俊逸与查锦莱、祝合义诸人一一揖别,跳上候着的马车,车夫吆喝一声,马车嘚嘚嘚地绝尘而去。
顺安招辆黄包车,远远跟在后面。
俊逸的马车左拐右拐,在大英租界一条僻静巷子口停下。俊逸跳下马车,对车夫交代几句,摆摆手,望着马车驶离,才转身拐进巷子。
顺安跳下黄包车,打发了车夫,闪身跟在身后。
俊逸走进巷子深处,在一个院门前停下,抬手敲门。院门吱呀开启,俊逸闪进去,院门再度关上。
顺安两眼大睁,心儿怦怦直跳,迟疑良久,悄悄走近,隔门缝看进去。
院中,阿秀正在侍奉俊逸洗脸,一个阿姨正在上菜倒酒。
“乖乖,”顺安倒吸一口气,缩回头,捂住眼,心道,“怪道小姐上心,原来鲁叔金屋藏娇哩!”略顿一下,扭头回走,边走边思忖,“这该哪能办哩?大丈夫自当三妻四妾,鲁叔如此有钱,却无一妻,养个女人还要藏在此处,为的必是小姐。小姐这般追究,防的也必是此事。这这这??我该哪能办哩?”
转瞬走到大街上,顺安正要打车回去,却又想道:“这辰光回去,小姐必在守着,若是问我,又该哪能个应答?也罢,我且守在此处,一则躲下小姐,二则看看鲁叔究底在这里能待多久。若是夜半回去,万一出个啥事体,也好有个照应!”
这样想定,顺安就又拐回巷子,在阿秀的小院子外面寻个阴影坐下。
接下来几日,顺安开始躲避碧瑶,清晨起床,也不再走前面正门,而是悄悄溜出通向小巷子的后门。碧瑶越是逮不住他,心里越是毛躁,终于在一个早晨不顾一切地走到后院,早早堵在顺安的房门外面。
顺安开门,大吃一惊,未及掩上,碧瑶已是跨步进门。
“说吧,”碧瑶大大咧咧地在他的书桌前面坐下,拢把头发,二目逼视,“为啥躲我?”
“哪??哪里躲了?”顺安结巴了。
“既然没躲,为啥不走前门?”
“我??走了呀,可??没见小姐来着!”顺安黑下心编谎。
“你骗鬼!”碧瑶生气了,小纤拳擂在桌面上,面色紫涨。
“我是走了,”顺安只好圆谎,“前天有事,走得早,天不亮就出去了,昨天夜里执行小姐差事,起得晚,小半晌才走,还误了事体,挨师兄一顿话头。”
碧瑶眼睛眨巴几下,觉得自己也并没有一直盯住过道看,许是冤枉他了,紧又换过脸色,冲他笑道:“好了好了,不说这事体,快讲讲我阿爸!”
“这??”顺安朝伍挺举的房门努下嘴。
碧瑶明白,压低声音:“你小声点儿!”
顺安晓得再无退路了,只好一五一十,将鲁俊逸前几日的夜间活动悉数讲一遍,只略去租界阿秀的院子,说鲁叔如何在商会里忙活,商会如何修建铁路,这铁路从哪里到哪里,需要多少银子,鲁叔如何了得,如何一直忙到深夜??
“不信不信我不信!”碧瑶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嚷嚷起来,“你骗人,我鼻子、耳朵、头发、眉毛全都不信!”
“嘘!”顺安急将指头放在嘴边,压低嗓音,做出一脸委屈状,“千真万确呀,小姐,我??我向你保证,一连几天,鲁叔去的就是这几处,商会、酒楼,查老爷子和祝老板府宅,每次都有大老板跟着,一大群人哩??”
“你起誓!”
“苍天在上,”顺安一丝儿犹豫也不打,立马举手,“我傅晓迪向小姐起誓,若是所言不实,天打雷??”
“好了好了,”碧瑶摆手打断他,不耐烦道,“啥人要你的破誓了?我有个主意,今朝苍黑辰光,你在院门外面等我!”
当日黄昏,碧瑶女扮男装,与顺安一道守在总商会门外。
果然,没守多久,俊逸、祝合义等人有说有笑地走出会馆,但并没上车,而是沿南京路有说有笑地走向外滩。顺安看一眼碧瑶,二人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眼睁睁地看着鲁俊逸几人走进一家酒店。
“小姐呀,”顺安有点得意,“看到没,我没瞎讲吧。老爷这??到酒店里商议大事哩。”
“晓得了。”碧瑶胡乱应一句,两道目光聚焦在酒店的金色大门上。
“小姐呀,”顺安见她扎下架子,就又慢悠悠地说道,“我守几天了,就是这家酒店,鲁叔他们几人天天晚上来到这里,一边喝酒,一边洽谈公务!”
“晓得了。”碧瑶又是一声。
“小姐有所不知,”顺安做出难受的样子,“男人们一旦喝起来,真就没个底哩,又是猜拳又是行令,这又加上商量事体,没有几个时辰出不来。前些日,我天天守在这里,晓得他们,不到三更天,出不来哩!”
“我等到天亮!”碧瑶一字一顿。
“这可不成,”顺安急了,“这辰光是早春,夜里凉,尤其在这江边上,万一把小姐冻伤风了,晓迪可就吃罪不起了。”
“冻死我也不关你的事体!”碧瑶铁心了,“要走你走,我一个人守!”
顺安心里叫苦,却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好心情忐忑地守在一边,不敢靠她太近。
该来的还是来了。
俊逸与祝合义等人在酒店门外,揖过作别后,跳上等候着的马车,车夫吆喝一声,马车嘚嘚,绝尘而去。
碧瑶和顺安招了两辆黄包车,步步紧跟。
俊逸的马车,左拐右拐,拐到一条僻静巷子,马车停下, 俊逸下车,朝车夫摆下手,醉醺醺地一摇一晃,走进弄堂。
碧瑶高度亢奋,噌地跳下黄包车,急追过去。
车夫急叫:“小姐,钱!”
顺安跳下另一辆车,给两个车夫各塞一只角子,追向碧瑶。
碧瑶隐在黑影里,眼睛紧盯醉醺醺的俊逸,好像他立马就会消失似的。
虽已酒醉,俊逸仍熟稔地走向一处宅院,抬手敲门。
院门吱呀打开,一个女人低声道:“老爷回来啦!”并顺手接过俊逸的公事包,俟俊逸走进,将院门关闭。
碧瑶快步赶至,隔门缝向内观望。
顺安也急赶过去,紧张地守在她旁边。
里面传出俊逸的声音:“阿秀,让你等急了。”
阿秀的声音:“没事体的。”
俊逸的声音:“嗨,他们几个硬要拉我喝酒,灌多了。”
阿秀的声音:“是哩,酒气大哩。快,水烧好了,先洗洗,再喝点茶解酒??”
碧瑶听得真切,怒不可遏,举起拳头砸向房门。
夜很静,碧瑶砸得重,声音山响。
房子里陡然静寂。
不一会儿,传出俊逸的声音:“啥人?”
有脚步声下楼,打开房门,走到院子,朝大门口走来。
大概是手震疼了,碧瑶用脚踢,边踢边呼哧喘气。
俊逸提高声音,语调严厉:“啥人?”纷乱的脚步声移向院门。
碧瑶退后一步,摆好架子,准备迎战,大口喘气。
就在此时,顺安不知从哪儿涌出一股勇气,猛然出手,掏出手绢塞进她口里,将她拦腰抱起,不顾她的撕打咬捏,沿巷子没命跑去。
顺安一气跑到街上,方才将她放到地上,扑通跪地。
碧瑶气疯了,面孔扭曲,朝他狠打一记耳光,从牙缝里挤出:“傅??傅晓迪??”
顺安连连磕头,带着哭腔:“小??小姐??”
碧瑶气得眼泪出来:“你??你凭??凭啥??拦我?”又是一记耳光。
顺安伸脸过去:“小姐,你??你再打!多打几下出出气!”
碧瑶啪啪啪又是几记耳光:“讲,凭啥拦我?”
“小姐呀,”顺安捂住脸,半是哀求,“晓??晓迪不能让你进去呀。你这一进去,鲁叔就会晓得是??是我领小姐来的,是我盯他的梢,我??岂不??死定了!”
碧瑶喘气:“你??你晓得这??这野女人是啥人不?”
“不会是野女人吧,想是鲁叔在此地歇歇脚,写啥东西哩。听声音,那女人不过是个老妈子。你看,上海滩上,到哪儿去寻到介清静的地方哩!”
碧瑶气杀:“你??你晓得个屁!”扭转身,大踏步走了。
顺安怔一下,紧随于后。
碧瑶回身,恨恨地指着他:“傅晓迪,我让你盯梢哩,这就是你盯的梢?”
“小姐,我??”
“滚,滚滚滚,甭再让我看到你!”碧瑶扭过身,飞快跑去。
见她是朝家的方向跑,顺安也就松口气,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二人刚走没有多久,齐伯也急匆匆地走过来,直接拐进巷子,走到阿秀宅院外面,敲门。
“啥人?”俊逸刚上二楼,听到响声,从窗子里探头问道。
齐伯压低声音:“老爷,是我!”
听到是齐伯的声音,俊逸吃一大怔,匆匆下楼,打开院门:“介晚了,啥事体?”
“小姐不见了!”齐伯急切说道。
“啊?”俊逸的酒劲这也完全醒了,陡然意识到方才的打门声或是碧瑶,怔在那儿。
“小姐是迎黑辰光不见的,晚饭没吃。我问秋红,她也不晓得。”
“阿秀,”俊逸反应过来,朝楼上叫道,“我有桩急事体,今晚不回来了,你闩门睡吧!”说完与齐伯匆匆走了。
二人回到府宅,见闺房的灯亮着,相视一眼,急赶过来。
秋红坐在楼梯口,早已听到二人,站起来,弯腰候在一侧:“老爷?”
“小姐呢?”俊逸急问。
秋红指下门里,压低声:“屋里厢哭呢。”
俊逸嘘出一口长气:“你在此地做啥?”
“小姐发脾气,把我轰出来了!”
房间里果然传出碧瑶隐隐的哭声。
“发啥脾气?”俊逸佯作不知。
“不晓得哩。方才她打外面回来,跟疯了似的,进门就哭,还打我,我??不敢问她!”
“晓得了。”俊逸摆摆手,转对齐伯,“齐伯,你带秋红到灶房里弄点吃的,小姐怕还没吃饭哩。”
齐伯应一声,招呼秋红下楼。
俊逸走进房间。
碧瑶早就听到声音了,哭得愈加伤心。
俊逸在她身边坐下,拍她:“瑶儿?”
碧瑶号啕大哭。
俊逸轻轻拍她:“瑶儿,啥事体,介伤心哪?”
碧瑶陡然止住哭,忽地坐起,动作之大,吓俊逸一跳。
“甭碰我!”碧瑶歇斯底里。
“瑶儿?你??”俊逸愕然,“我是你阿爸呀!”
“阿爸?”碧瑶冷笑一声,“我没有你这个阿爸!”
“瑶儿?”俊逸压低声音,语气严厉,略顿一下,又放松了,“瑶儿,好好讲,究底是为啥事体?”
“啥事体?”碧瑶冷冷说道,“你自己做下的啥事体,还问我做啥?”
“瑶儿,你??”俊逸心知肚明,此时却只能装糊涂,“哪能扯到阿爸身上哩?”
碧瑶火辣辣地盯住他:“我扯的就是你!”
“瑶儿?”
“好,我这问你一句话!”
“你讲。”
“如果一个父亲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孩子,却又一直骗她,那他还是个父亲吗?”
“瑶儿,”俊逸让她挤到墙角了,勉强挤出笑脸,“你??哪能问到这个哩?”
“我要你回答!”
俊逸苦笑一下:“不会有这种父亲的。”
碧瑶一字一顿:“他就是你!”
“瑶儿,你??”俊逸大窘,“哪能这样讲话哩?阿爸啥辰光骗你了?”
“啥辰光?你一直在骗我!”
“瑶儿,”俊逸急了,“你哪能乱讲哩?”
碧瑶猛地掀开被子,跳下床:“我乱讲没乱讲,你自己晓得!我问你,这些日里,你为啥天天晚上不回家?”
“我??”俊逸支应道,“阿爸这不是忙嘛。要修铁路,要筹款,要起草协议,要制订章程??阿爸一天到晚只在会馆里,忙得东不是东,西不是西。”
碧瑶冷笑一声:“到这辰光了,你还在演戏!”
“瑶儿,”俊逸沉下脸来,“你哪能这般跟阿爸讲话哩?”
“那好,”碧瑶两眼逼视他,从桌子抽屉里摸出一个包包,解开,现出一根长头发,“你看清爽,这是什么?”
“这??一根头发呀。”
“啥人的头发?”
“这这这,”俊逸苦笑一声,“啥人的头发,阿爸哪能晓得哩?”
“哼,”碧瑶鼻孔里哼出一声,一字一顿,“它就沾在你的衣领上,是我亲手取下来的!”
“唉,”俊逸轻叹一声,“这能说明什么呢?阿爸到理发店??”
话没说完,碧瑶尖声截住:“阿爸,你??甭再讲了!这根头发,我已经晓得是啥人的了!”
见碧瑶把话说到这步田地,俊逸轻叹一声,不作声了。
“我且问你,”碧瑶却是不依不饶,“前些日就不讲了,只说今天晚上,天黑之后你在做啥?也是在筹款吗?”
“与你祝叔、查叔、周叔几个在酒店里吃饭,商量事体。你看,阿爸这还一身酒气哩。要是不信,明朝你去问你祝叔!”俊逸强自辩道。
“吃过饭之后呢?”
“这??不就回来了吗?”
“阿爸,”碧瑶见他仍不承认,跺脚哭道,“你??你骗我,你一直骗我!”
俊逸的声音软下来:“瑶儿??”
“你到我阿姨那儿去了!”碧瑶带着哭音,指头发,“这根头发就是她的!阿爸,你??你在我姆妈跟前答应过我,你不要阿姨,你谁也不要,你只要我,可你??这又偷偷把她接来,你??你??你??”气结。
“你??哪能晓得的?”俊逸显然不死心,仍在寻找机会。
“今天晚上,我就跟在你身后,从商会一路跟到饭店,又从饭店跟到那个女人的住处!”
俊逸呆了。
碧瑶扑入他怀里,声音凄切:“阿爸,你??你哪能骗我呀?”
俊逸傻在那儿,一只手下意识地轻轻拍她。
“阿爸,”碧瑶哭得越发伤心,“你是不是不要瑶儿了呀,阿爸?瑶儿??瑶儿只有阿爸你呀,阿爸??”
俊逸依旧愣在那儿。
“阿爸,你??你说话呀!”
“瑶儿,”俊逸回过神,轻轻抱住她,哽咽起来,“是阿爸错了,阿爸不该骗你??阿爸哪能不要你哩?阿爸只有你一个女儿呀!可是,瑶儿呀,你也不能任性,你长大了,你不能再像小辰光那般,你要理解阿爸呀,瑶儿!”
“阿爸—”碧瑶搂紧俊逸,“我不要理解阿爸,我只要阿爸,阿爸,你不能再去找那个女人,你要天天回来陪我!你答应过我的,你当着姆妈的面答应过我的!”
俊逸搂紧她,泣不成声。
“阿爸,”碧瑶不依不饶,“你必须答应我,你必须再次答应我,你不能去找那个女人,你必须天天回来陪我!”
突然,俊逸松开碧瑶,擦去她的泪水,也顺手抹去自己的,敛起面孔,异常严肃地久久凝视女儿。
许是从未见过俊逸用这般眼神看她,碧瑶有点惊愕,语气由要求变为恳求:“阿爸,你??就答应我吧!求求你答应我吧!”
“瑶儿,”俊逸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说道,“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了,是不?”
碧瑶使劲摇头,语无伦次:“阿爸,瑶儿不想长大,瑶儿只要阿爸,瑶儿啥都不要,瑶儿只要阿爸快点儿答应瑶儿,阿爸只爱瑶儿一个人,只陪瑶儿一个人??”
“瑶儿,”俊逸打断她,“阿爸答应你,阿爸答应天天回来陪你,但你也必须答应阿爸一桩事体!”
碧瑶急问:“啥事体?”
“你必须记住,”俊逸的语气毋庸置疑,“从今往后,你不许再到阿姨住的地方去!”
“我不,我不,我偏不!”碧瑶又闹起来,“我明天就去寻她,我要她滚回老家去,我要她永永远远滚回老家去,不许再来纠缠阿爸!”
俊逸声色俱厉:“瑶儿!”
碧瑶从未见过他的这个语气和神态,情不自禁地打个哆嗦。
“阿爸再讲一遍,”俊逸下定狠心,一字一顿,“从今朝起,你再不许到阿姨住的地方去!若是你不听阿爸的,阿爸??阿爸就??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碧瑶似被这句话的强大威力吓傻了,脸色惨白。
“瑶儿,”俊逸缓和语气,“你记住,这是阿爸的底线!你可以不欢喜阿姨,但不可去找阿姨的麻烦!你是你,阿姨是阿姨,你俩井水不犯河水,晓得不?”
碧瑶仍旧怔在那儿,不知所措。
为达到效果,俊逸起身,一手放在碧瑶肩上,一手扳过她的面孔,重申要点:“瑶儿,你必须记住,你是你,你阿姨是你阿姨,阿爸两个都要!”言讫,在她肩上重重一按,转过身,不再顾及碧瑶的感受,大踏步而去。
一直走到楼下,方才听到碧瑶被强烈压抑后的悲泣声。
俊逸没有停下,反而加快脚步,沉重的皮鞋踩在砖石地板上,一下接一下的咔嚓声越响越远,直到消逝在前院,然后是重重的上楼梯声,再后是书房门的开启声,甚至拉电灯开关的声音也那么刺耳。
碧瑶两手捂住耳朵,将头埋进被子里,呜呜咽咽,哭了个悲切。
书房里,鲁俊逸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摸出一支雪茄,放进烟斗里,点上火,深吸一口,缓缓吐出。
俊逸一连抽有不知多少根,越抽越没睡意,眉头也越拧越紧。阿秀与碧瑶,就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齐伯推门进来。
房间里烟雾弥漫,齐伯被呛得接连咳嗽几下,叫道:“老爷??”
俊逸把烟掐灭。
齐伯推开窗子,敞开房门。
“齐伯,”俊逸苦笑一下,“哪能没睡哩?”
“睡醒了。”
“你讲,这事体哪能办哩?”俊逸又是一声苦笑。
“老爷,”齐伯晓得他指的是什么,顺口接道,“小姐长大了,好像满十六哩。”
俊逸长吸一口气:“你的意思是??她思春了?”
“女大不中留呀,”齐伯点头,“小姐年方二八,照理说,是该嫁人了。要是小姐心里有个念想,也许不会??”
“是哩。”俊逸眼睛一亮,叹道,“唉,是我错了。我总是把她看作孩子,总想把她留在身边。齐伯,你这讲讲,给她寻个啥样的人合适?”
“要看老爷是啥想法。是看重人品,还是看重家世?是看重生意,还是看重小姐?”
“要是??”俊逸忖思一时,“都看重呢?”
“如果各方面都看重,我倒是可以推荐个人。”
“啥人?”
“挺举。”
俊逸心里咯噔一声,眼睛不自觉地瞄向墙上的那幅画。
“老爷?”齐伯晓得他在记挂什么。
“我晓得了。”俊逸收回目光,冲他笑笑,看下手腕,起身,“快一点了,我们睡吧。”
二人出门,齐伯锁上,跟在俊逸身后,回到中院,各回各的房间去了。
是夜,直到鸡叫,鲁家宅院里,有一个人仍未睡着。
是顺安。
顺安无法入睡,因为这是一个与他密切相关的夜晚。他的耳边回荡着俊逸与齐伯的对话,因为在二人说这些话时,他就站在离后窗不远的甬道暗影里。深夜静寂,再小的声音也会被放大:
??
“是看重人品,还是看重家世?是看重生意,还是看重小姐?”
“要是都看重呢?”
“如果各方面都看重,我倒是可以推荐个人。”
“啥人?”
“挺举。”
??
又是挺举!
挺举,挺举,挺举??
顺安一会儿坐起,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在房间里转圈子。
渐渐地,顺安的心静下来,重新躺回床上,凝视头顶的天花板,脑海中闪回一系列场景:
—伍家书房里,挺举身穿长衫写字,自己穿着书童短衫站在一边磨墨。
—进举途中,树荫下,也穿上长衫的自己向挺举鞠九十度大躬。
—四明公所停棺房,自己为改名换姓,向挺举下跪。
—茂平谷行,挺举运筹帷幄,发号施令,自己数拨油灯,拨打算盘,忙不迭地记账。
—二人寝室,鲁俊逸交给他们两个信封,挺举一千元庄票,自己仅仅一百。
—茂升钱庄大客堂里,挺举穿着掌柜服,与众多掌柜、把头级别的人一起开会。
—大街上,自己依旧挂着跑街包,低头哈腰地跟在徐把头身后,听着他的训斥。
—麦基家宴上,喜笑颜开的麦嘉丽落落大方地坐在挺举身边,挽住挺举的手说,爱蜜思油麦克麦克。
—碧瑶将自己所送的四本书一本本撕碎。
—碧瑶的声音:“我是瞧得起你,才把这桩好事体让予你做。你若不肯,我就寻别人去了。谷行里想必有人愿做这事体哩。”
—大街上,疯了般的碧瑶一下接一下地狠狠掌掴他。
??
顺安翻身坐起,面孔渐渐扭曲。
顺安跳下床来,再度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拳头渐捏渐紧,面孔由扭曲转为刚毅,心里发出一个声音:“傅晓迪,你已经不是甫顺安了。你不再是伍家的书童,你也不再是戏班主的儿子。你,世家出身,你,进举生员,你与伍挺举、徐把头是排在同一条食槽前面的犍牛,草料只有这么多,他们吃多了,你就吃少了!”
顺安二目放光,又走几步,脸上现出决战前的果决与刚毅:“你要拱,你必须拱,你必须左腾右挪,把徐把头拱到一边去,把伍挺举拱到一边去,再把鲁小姐拱到怀里来!傅晓迪,你没有退路,你只有拱!拱拱拱,你必须一拱到底,把槽里的犍牛全部拱走,独占整个食槽!”
然而,先朝哪个方向拱呢?这又如何下口呢?顺安长吸一口气,在床上盘腿坐下,学起伍挺举遇到大事时的范儿,闭目冥思。
显然,横拦在他面前的最大犍牛不是徐把头,而是挺举阿哥。挺举把什么都占尽了,只留给他一个机会,就是鲁小姐,可齐伯今晚竟然??
眼见齐伯如此这般、一如既往地帮衬挺举,顺安既犯酸,也无奈。鲁叔虽没认可,却说了个“晓得了”。这个“晓得了”当作何解?这个茧该怎么破?
对了!顺安心里陡然一亮,眼前浮出那日在麦基家的情景。麦小姐对挺举那般表现,麦基、麦夫人非但没有制止,反倒呵呵直乐。这事体只有一个解释,麦小姐欢喜挺举,麦基、麦夫人不定也相中这个女婿了。若是此说,倒也是个解。挺举阿哥如果成了洋女婿,齐伯、鲁叔也就只能断掉这个念想,小姐早晚??
不对!顺安念头一转,心里打个咯噔。即使自己成为鲁家女婿,挺举却是洋人女婿。天哪,洋人,挺举阿哥岂不是仍旧压着自己一头?
唉!顺安轻叹一声,耳边响起姆妈甫韩氏的唱腔:“既生瑜,何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顺安苦笑一声,喃声学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