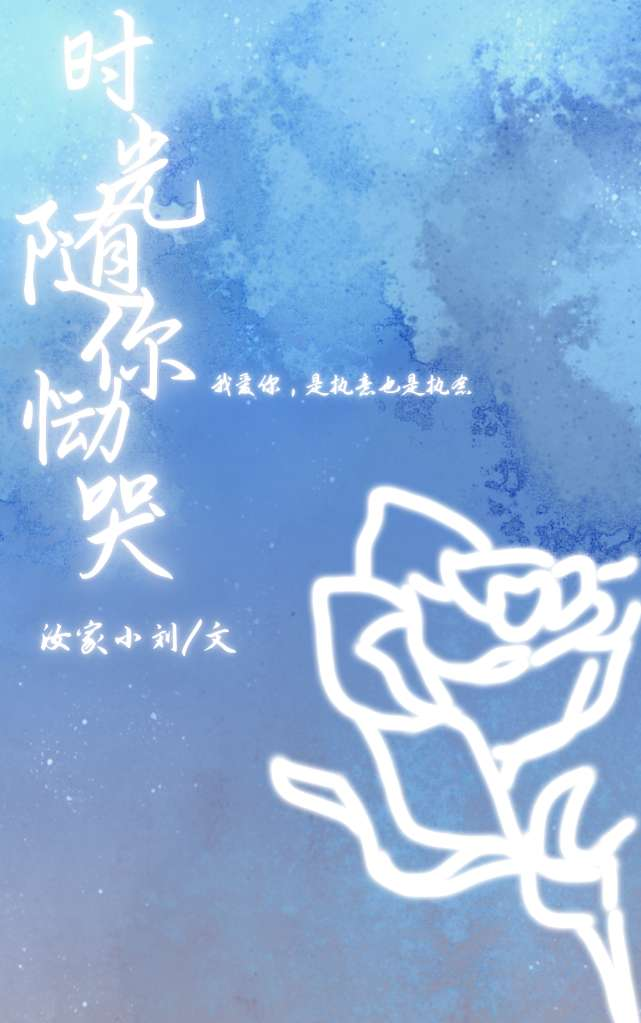晴川吃过张涛安排的接风宴,几天都平静得很,各方面的势力都很默契地没有组织行动,就连满街的地痞无赖都少了许多。
晴川和黄公子上任以后,并没有像张涛想象中那样高压搜捕抗日分子,而是把精力全用在了稳定社会治安上面。
吃饭不给钱的无赖、当街调戏妇女的流氓、欺行霸市的痞子被抓起来几十个。一个老太太在大街上买粮食时发现钱包不见了的小事竟然也惊动了晴川,他亲自带着二十几个日本宪兵和大票的汉奸特务满大街地抓小偷,最后追了好几条街把倒霉的小偷一枪打死了。
看到鬼子大官拿着滴着血的钱包往自己手里塞,老太太吓得一个劲跪在地上磕头。
与此同时,《满洲日报》、《日满亲善报》、《锦州时报》等伪满的报纸在事情过去了半个月以后像后返劲儿一样地用很大版面刊登了“满洲张涛参议”协助皇军打击抗联乱匪,并亲手击毙了6个抗联分子的“英雄事迹”,称赞张涛是“满洲青年的楷模,日满亲善的榜样”。
张涛烦躁地扔掉了手中的报纸,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在客厅里面来回踱步:“小鬼子这到底是想做什么,他们自己装好人,到处嚷嚷我是大汉奸,什么意思呀。”
四叔忧虑地说:“就是这个意思,抗日不坚定的,肯定就被小鬼子给糊弄了,抗日坚定的,也得先骂你再骂小鬼子。少爷,小鬼子这是把你盯死了,还好明天样品就能过来,过几天你就要去新京和黑龙会做生意交货,鬼子的怀疑多少能减轻一点。老百姓那边,唉,老百姓那边慢慢来吧。”
正说着,管家张贵走了进来:“张参议,香满楼的张掌柜过来结账了,穿得挺干净的(后面没有尾巴)。”张涛一笑:“人家来结账还管人家干净不干净,你去对一下账,让掌柜的到书房见我。四叔也一起唠唠吧。”
不多时,张来财就走进了小客厅,张涛和四叔已经坐在沙发上等他了。张涛招呼张掌柜坐下,一语双关地说:“也没有多少钱的事情,怎么张掌柜还亲自跑了一趟。”
“张先生倒是坐得住。我这次来有3件事情,第一,张参议您已经成了特高科内部认定的‘杀八方’嫌疑犯,现在发生的所有事儿,都是对着你来的。现在还只是开始,特高科制定了一个捉鬼计划,目的就是让你露出马脚,把你的势力一网打尽。”张来财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说。
“久保老鬼子从来都是盯着我,我都习惯了。”张涛自嘲地一笑,“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张掌柜一笑:“我们自有我们的办法。这第二条消息您应该更感兴趣。小黑山旁边姥姥岭的绺子要投日本人了,领头的报号‘活牲口’。”
张涛一下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如果他真的当了狗,老狼营可就危险了。第三条是什么?”
张掌柜呵呵一笑:“坐不住了不是?这第三条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现在还没有影响到滨岛,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不再和你联系,这是为了保护张先生,还请理解。”说到这里张掌柜的胖脸上出现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东北军一枪不放就把大好河山让了出去,你们最起码还在坚持抗战。现在东北到处是臭肉,出几个苍蝇也不稀奇的。还说让我小心点,倒是你们应该小心点才对。”张涛安慰道,“是谁叛变了?实在不行我去把他给插了就一了百了了!”说到这儿,目露凶光,杀气在身上腾地就起来了。
张掌柜知道张涛绝对不是个老实的主儿,生怕再惹出什么漏子来,连忙道:“还不知道是谁叛变了,最近我们在锦州、义县的同志接连被捕,好几个情报站和交通站都被摧毁了,我们就分析肯定是出了叛徒。我们会小心的,至于惩罚叛徒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办,就不劳张先生操心了。”
张掌柜告辞之前,再三嘱咐张涛要注意安全,张涛连连答应把张掌柜送出了参议府。
“‘山兔子’!”张涛沉着脸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一个护院应声走进了客厅,这人的外貌和兔子根本就不沾边,既没有长耳朵也不是三瓣嘴,身高足有两米开外,长得黑瘦黑瘦的,活像一棵雷劈过的树桩子。
这“山兔子”跟张涛算起来已经有两年的交情了。原来本是一伙胡子的“眼梢”,一次踩盘子的时候被人家的炮手发现,“山兔子”胳膊上中了一枪。恰好张涛外出给碰上了,就把他救了回来,并治好了他的枪伤。听说“山兔子”的绺子被日本人给打得倒了旗,就把他留在参议府上当了名护院。张涛的20个护院里面,“山兔子”的功夫和枪法都在中下等。但是这家伙有三绝:一是认路,不管多偏僻的小路、山路,只要是没有出关,就没有“山兔子”不认识的。二是化装,他要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就是他爹也认不出是他。三是赶路,尤其是走山道,两条大长腿一迈,谁也撵不上他。跑得比兔子快,这才是他的外号“山兔子”的由来。
“张参议,您叫我。”“山兔子”走进来后,鞠躬行了一个礼,消瘦的脸上表情木讷。
“‘山兔子’,你得上趟小黑山,有几句话带给‘杀八方’和刘小姐,你过来。”张涛招了招手,“山兔子”听话地走了过去,张涛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以后问道:“咋样,记住没?”
“山兔子”依然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当眼梢子的第一关就是记性,张参议放心,这几句话我要是说走了样,回来您把我的两只兔耳朵割去下酒喝。”
“耳朵就不用了,你的耳朵又没有猪耳朵好吃,不过这次不同往日,鬼子盯得紧,你不能骑马,还得化装出城,越快越好。”张涛急急地说道,“要是晚了,老狼营没准让人家倒了旗了。”
“张参议放心,要是真那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现在准备准备就走。”“山兔子”没有废话,转身就跑了出去。
出城检查站。
几个伪军和鬼子一丝不苟地检查和盘问着过往的行人。一个驼背的乞丐排队接受检查,这乞丐不知道是不是有毛病,才刚入秋就穿上了羊皮袄,里面就是光着膀子,头发老长,乱糟糟的。身上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了,一阵阵地散发出酸臭味。脸和手也是黑乎乎的,根本看不出来本色。几只苍蝇饶有兴致地围着他欢快飞舞着,也就这种飞虫喜好这股子“鲜亮味儿”。
看到一个伪军走了过来,乞丐一边用手搓着胸口上的污泥,一边大大咧咧地开口道:“这咋还检查呢,刚才进城都检查过了包,我也没要着钱儿呢。”一口地道的关里唐山口音。
嘴里一股臭韭菜味把刚要凑上来的伪军一连逼退了两步,捂着鼻子大骂:“这股味儿,都馊了,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快滚快滚!”
乞丐点了点头,撒丫子就想溜。
“检查的没有,出去的不行。”一个挺着三八大盖的鬼子兵走了过来,闻到了乞丐身上那生猛的味道,皱着眉头站住了,犹豫了一下,向着刚才的伪军扬了扬下巴:“你的,仔细检查的干活。”
“啊?我啊?”那个倒霉伪军指了指自己,看到那小鬼子坚定的目光,只好憋着气摸向那件羊皮袄,还没有摸几下,那伪军就跳了起来,像踩上了电门一样死命甩着手,嘴上还大喊:“跳蚤,怎么这么多跳蚤!”
旁边的伪军和鬼子幸灾乐祸哈哈大笑起来,废话,乞丐身上要别的没有,就盛产这玩意儿!
倒霉伪军连忙掏出一块手绢狠狠地擦了擦手,然后用力把手绢扔向一边,向乞丐的屁股上踹了一脚,道:“滚,快给我滚,以后你要是再进滨岛,当心大爷我毙了你。”
看着检查站渐渐远了,化装成乞丐的“山兔子”小声嘀咕道:“等着,早晚有一天爷爷把你蹄子砍下来。”
又用同样的办法过了另外两个检查站,正午时分,“山兔子”已经进了山。
他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看看四周无人,脱光了膀子,迅速把身上洗干净,又伸手把皮袄的夹层打开,拿出一把盒子炮别在腰上。拎着破皮袄往前走了几步,伸手从一棵大柳树的树洞里面掏出了一个油布包裹,打开后是几个盒子炮的**和一件半新不旧的褐色短褂。穿戴整齐以后随手把破皮袄塞进树洞里面,向群山的深处走去。
初秋和阳春的季节最适合走山道,既不会冰冷刺骨,也不会大汗淋漓。下午的阳光透过密密匝匝树叶子的缝隙点点照在身上,让“山兔子”感觉很舒服。他顺手在边上的果树上摘下来几个野沙果放在褂子的兜子里面,然后把手里留下的那个在衣襟上擦了擦就咬了起来,酸甜的汁液仿佛顺着嘴角一直流到了心里。连着吃了3个野沙果之后,“山兔子”停下来抬头辨认出太阳的位置,离开了山道向左边的小路拐了进去。
他越往前走,林子就越密实,一层又一层的树叶子把太阳都挡得严严实实的,比刚才在山道上的气温好像还低了几度。可能是不见阳光的关系,树根子底下全是蘑菇。
“咻”的一声,一条花蛇从“山兔子”脚前窜了过去,没命地往旁边的草丛里钻。“沙沙”的声音越来越远,一眨眼的工夫就听不到了。接着又是一只野兔子从身后窜了过去。
“山兔子”心里面“咯噔”一下。能毒死一头牛的被面子蛇都跑得飞快,看来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没准是自己遇到林子里的凶兽了。
他小心地拔出了手枪,拉开保险猫着腰一步一步向老林子深处挪了过去。刚刚挪了没有几步,就听得“轰”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就是“嗷——”的一声长啸,这声音极大,中气十足。
原本肃静的林子这次可热闹起来。原本不知道在哪里猫着的獾子、刺猬、松鼠等小兽全都没命地跑了起来。山鸡、飞龙、串子和一些不知名的野鸟“扑棱棱”乱飞得到处都是。
这家伙挺厉害,不会是东北虎吧!虎王的叫声才有这么大的能耐,吓得鸟兽们清了山。可这声音又不是虎啸,倒是有点像黑瞎子叫唤,不过黑瞎子叫唤一声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邪乎。“山兔子”本想马上绕过去,尽快赶到小黑山,可强烈的好奇心又让他挪不开步。
“时间还来得及,大不了紧走几步天黑前也能赶到,有枪声就有人,救一个人积点德,没准打仗的时候老天爷能让我躲开一颗要命的枪子儿。”“山兔子”迈开两条长腿向着声音的源头奔了过去。在离“山兔子”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林癞子地,就是像人长癞的地方没有头发一样,在密密匝匝的树林子里没有一棵树的地方。刚走到癞子的边缘,“山兔子”就停下了。
就在离“山兔子”50米的地方,一个老人紧紧地握着一杆老洋炮,一条腿血肉模糊,勉勉强强站着和对面的凶兽对峙着。
老人的对面是熊瞎子,足有3米高,一身油亮的皮毛是青色的。
“人熊!”“山兔子”大惊失色。
在东北的老林子里面,熊瞎子很多,人熊却极少。老辈人说大熊瞎子吃过千年人参活过200岁才能变成人熊,离成精就不远了。
在传说里面,人熊是刀枪不入、力大无穷的,一巴掌就能拍断一棵大腿粗的老松树。在东北有“宁碰东北虎,绝不遇人熊”的说法。
“山兔子”仔细一看,发现人熊也受了伤,一个铁的熊套子被扭得七扭八歪,一只熊掌上也是流着血。熊套子的力道足有七八百斤,却被这人熊给弄坏了,这得多大劲儿!
眼见人熊一步一步地向老人挪了过去,“山兔子”也管不了那么多,“啪”、“啪”、“啪”,对着人熊的后脑勺就是几枪。
人熊毫无防备被打得向前踉跄两步,眼见后脑勺流出血来却没有倒,对着上上兔子”转过了身子。“山兔子”这才看清原来人熊的脸上也受了伤,足有十几个伤口在流血,伤口却都不大,看来是刚才老人手中的洋炮也伤了它。
这十几个伤口都分布在眼睛周围,人熊的眼睛却没有事儿。一对细长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山兔子”。那眼神完全就是人的眼神:歹毒、怨恨、愤怒。
死亡的气息,开始在这老林子中弥漫开来……
“吼!吼!”往前一瘸一拐地冲了几步,人熊的身躯就站住了,直直地瞪着“山兔子”。人熊身后的老人一边手忙脚乱地往洋炮里面倒**、压枪砂,一边喊:“小兄弟,人熊是想让你走,你快走吧,别为了我这个糟老头子没了命。”
“山兔子”也是恶狠狠地盯着人熊,手攥着枪把都攥出了汗,喘着粗气:“爷们,我也是汉子,哪能在这个时候跑。”
老人见他没有走的意思,心里面着急,端起了刚压好了的洋炮又轰了一下,同时大喊一声:“过山洞!”人熊的背后升起一道青烟,身子连晃都没晃,脸上愈发狰狞起来,慢慢地回过头去。
“山兔子”心里一苦,“过山洞”在黑话里面就是耳朵眼的意思,老人是在提醒他打耳朵眼,可是这东西的耳朵眼比熊瞎子的小一倍,比子弹口径也大不到哪里去。管不了那么多了,“山兔子”心一横,快速拨动了盒子炮上面的快慢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了一个长点射。
看着人熊脑袋上蹦出点点血花,一梭子打完以后,“山兔子”转身就跑,心里说:要是打死就是救了一条人命,要是打不死我也是尽了江湖道义。没跑出几步就听后面“嗷——”的一声凄厉长啸,震得旁边的大树都嗡嗡地响。然后就是扑通一声重物倒地的声音。
“小兄弟,别跑了,人熊让你打死了。”隐约听到的声音让“山兔子”停下了狂奔的脚步。他换了**,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只见人熊直挺挺倒在了地上,老头蹲在人熊跟前翻看着。
“山兔子”这才重重吐了一口气,把手枪别在腰里走到老人跟前:“老人家,你腿上的伤没事吧?”
老人抬起头来,笑眯眯地看着“山兔子”:“小伙子,多亏了你呀,要不今天这老命就交代在这里了。”
“山兔子”倒不好意思起来:“您可别这么说,我都给吓得快尿裤子了,还把您撇在这儿自个儿跑了。”
“跑?搁我我也跑,要不是腿让这畜生掏了一下,我早就跑了。东北虎比咱爷俩厉害吧,见到人熊跑得比咱们还快。”老人扫了一眼“山兔子”腰里的手枪,“你懂行话,手里又有自来得,是哪个大绺子的吧?”
“山兔子”不知道为什么对眼前这个干瘦干瘦、白须飘飘精神头十足的老头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可能都是吃山饭的缘故,随口就答道:“我是前面老狼营的,就在小黑山上。”
“我这个老头子见过不少绺子,老狼营还真是个奇怪的绺子,每天喊口号,还训练,也不怎么干活,就是不让生人靠近,倒是有点像官军。”老人在怀里摸出烟袋锅子点上,“虽说你打死了这畜生,但我也拖了它半天,还挂了彩,这畜生算咱们爷俩打的怎么样?”
“老人家,我不是猎户,要这东西没有用的。天过会儿就要黑了,我得赶紧走了,老人家,您家在哪儿呀,我送您回去。”“山兔子”一脸关切,把关于老狼营的话题岔开了。
“我家离这里可远着哩,在林子里面都转悠好几天了,你忙你的吧,明天这个时候你带着绺子的大当家过来,咱们爷俩当着你们大当家的面把这畜生身上的宝贝平分了。”老头眯着眼睛贪婪地看着人熊的尸体。
“老人家,看来您也不是空子,你这腿上的伤都露了骨头,我还是把你带回绺子先治伤!”也不管老头同意不同意,背起老头就走。
老头也不反抗,还偶尔指点一下近路。从黑瞎子沟插回山道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刚到小黑山脚下,从山道边的树上突然蹦下一个人来,这人穿着绑满了草叶树枝的衣服,乍一看就以为是一堆树枝草叶子,手里拿着一把长管左轮,冰冷的枪口顶在了“山兔子”的脑袋上。
与此同时,身边的草壳子里面也跳出了两个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山兔子”才知道自己刚才基本上就是擦着人家鼻子尖走过去的,这奇怪的衣服藏在草丛里还真找不出来。后面的两个人端着“奉13年”步枪,逼住了“山兔子”和他背上的老人。
“蘑菇,什么价,这是要往哪儿溜达(你是什么人,哪伙的,要到哪里)?”看自己的同伴已经将两个人控制住,从树上跳出来的大汉问道。
“山兔子”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这是老狼营的暗哨。放下了背上的老头,扶他站住,笑呵呵地说:“太阳大大啦,要啥来啥,想喝奶遇上奶妈,想娘家人,孩子他舅舅到了(就是找你们的,咱们是一伙的)。”
“孩子的舅舅姓啥,叫啥,家住哪嘎达(你怎么证明你是自己人)?”
“孩子舅舅姓杀,管他叫啥不叫啥,家住河边三棵树,背靠一座玲珑塔(你们大当家的姓杀,叫啥有外人不方便说。这人也是道上的,有名气后面还有靠山)。”“山兔子”右手砍向平摊的左手手心,又在手心上比出了一个“八”的手势。
3个人对望了一下,领头的对“山兔子”说:“你和我进去,这个老头在这等一会儿。”说着抽出了“山兔子”腰里的盒子枪,从怀里抽出一条子黑布,准备把“山兔子”的眼睛蒙上。
“等会儿!”已经坐在路边大石头上的老头开了腔,从怀里拿出一个一巴掌大小的扁布包,“这个拿去给你们大当家的看看。”
“山兔子”一直就是把这个老头当成遇上了人熊的老猎手,没想到也是跟营子有关系的人,于是将信将疑地接过了布包揣在怀里,老实地让人将自己的眼睛蒙上,又原地转了几圈,被带上了山。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山兔子”感觉自己的耳边有了人声,敏锐地感觉到自己肯定是进了寨子。
“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山兔子’,怎么在张参议府干不下去了,上山投我当胡子?”“大疤瘌”爽朗的笑声在耳边响了起来。
眼前一亮,“山兔子”看清自己是在一个木头屋子里,“大疤瘌”站在身边,手里拿着遮住他眼睛的布条,槐花、“杀八方”和几个不认识的汉子都坐在屋里的木头椅子上笑呵呵地看着自己。
虽说是熟人,规矩可是不敢乱,“山兔子”站在屋子中央,向四面一拱手:“老狼营的三老四少、四梁八柱,崽子奉东家之命拜山传话,各位给个地方,行个方便。”
“杀八方”端坐在正中间的虎皮椅子上,向前探了探身子:“没想到‘山兔子’也是个里马,东家有吩咐就说,以后就不用这些虚礼了。”
“山兔子”不敢大意,仍旧拱了拱手:“东家原话是,姥姥岭的‘活牲口’可能要投鬼子,要是真是这么回事,‘活牲口’,杀;里面混进的鬼子汉奸,剐。这个绺子倒旗吞枪。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
坐在“杀八方”旁边的柳应元笑了笑说:“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大当家的说句话吧。”
“大疤瘌”站在中间嚷嚷:“对对,大当家的给个话,我‘大疤瘌’第一个冲上姥姥岭,小兔崽子,瞅着汉奸我就憋气。”
“山兔子”知道他们下一步肯定是要商量打姥姥岭的事儿,这要是一说上自己可就没有插话的机会了,连忙往前赶了一步:“大当家的,我在路上救了一个受伤的老头,现在让寨子里面的弟兄拦在山下了,他让我把这个交给大当家的。”说完把老头交给他的小布包递了上去。
“杀八方”疑惑地打开了布包,里面是一块扁扁的碎骨头,这骨头看来是经过了很长时间,都变成了灰色,上面歪歪扭扭地刻了3个字“山神令”!
“杀八方”脸色大变,急急地把那骨头令牌放到身旁插在墙上的照明火把上晃了一下,“吱”的一声响,颜色变深了一些,一股沁人心脾的异香在木头屋子里面飘散开来。
“杀八方”小心地把山神令放在木头桌子上,猛地站了起来:“开中门,叫崽子们列队迎接山里的‘活神仙’。”他对“大疤瘌”说:“我是个不全的人,麻烦兄弟下次山,把‘老神仙’背上来。”
“不就是个受伤的老头吗,弄这么邪乎干吗?”“大疤瘌”嘟囔道。
“叫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看到“杀八方”似乎真的生了气,“大疤瘌”招手过来两个兄弟,一声不吭地走了。
“大当家的,这东西是什么?这么用火一烤就有那么香的味儿。”一直没有出声儿的槐花疑惑地问。“山兔子”也把耳朵竖了起来。
“杀八方”的眼睛眯缝着,讲述了起来。
距今40多年前,现在算起来,那会儿还是光绪年间。
那时候,吃江湖饭的可不像现在这么多,虽然也是拉帮结伙的,但又是马帮又是胡子又是盐帮、金垛的,加起来也就是十几个绺子,这群人可是地道的心黑,啥来钱快就干啥,统称是黑道。
乍一开始的时候,互相之间还有个照应,没事帮一把什么的,可后来就逐渐有了磕碰,关系越闹越僵。
大伙儿琢磨着这么下去可不行,早晚让官军一个绺子一个绺子给剿了,再加上甲午年鬼子打进了关东,就想选个头带着大伙儿一边挣钱一边打鬼子。
可这些人都各自称王称霸惯了,谁都不服谁,事情就这么搁在这了,哄哄了几年没整出个结果来。
说来也巧,那一年帽子山的老林子里面闹虎王,据说是只成精的吊睛大虫,凶狠无比,晚上还总是跑进屯子里面叼小孩,伤了不少人命不说,官军拿洋枪都伤不了。
这些绺子就约定了,谁能杀了虎王谁就是道上的龙头老大。
可闹腾了很久,结果谁也伤不了那虎王一根汗毛,后来一个精壮的汉子,独自上山,生生把刀子插进了虎王的眼睛。
他杀了那祸害人的虎王,自己也受了重伤,连续十几天昏迷不醒。大家都说,这男子就是山神下凡,这会儿除了害又要走了,胡子们便把虎王的肩胛骨做成了这块“山神令”,打算为山神殉葬了,可没想到在下葬的节骨眼,那汉子在鬼门关前面转一圈,自己醒了过来!
故事讲完后,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地愣在了那里。
“山兔子”瞪大了眼睛,吧唧了一下嘴巴子:“这汉子不会就是我救回来的老头吧?他也就60岁的样子,胡子都没有全白,难道他十几岁就杀了虎王?”
听了这话“杀八方”哈哈大笑:“60岁?‘山兔子’你可走眼了呀!告诉你,小鬼子进关东那年,我给‘老神仙’拜的七十大寿。算到今年,应该是75岁高龄了。”
槐花瞪大了眼睛:“那还真是‘老神仙’,只是这‘老神仙’怎么就只身跑到瞎子沟去了?”
“杀八方”叹了口气:“还不都是鬼子闹腾的,老爷子65岁那年就离了道搬到奉天住了,住的房子还是大帅送的。每到过年过节,大帅就打发少帅往老爷子那里送东西。大绺子和数得上的大帮的大当家也是成天往老爷子那里送吃送喝。直到小日本鬼子打进了东北,先是派了个汉奸要老爷子出山当奉天省的省长,被‘老神仙’以年龄大、身体不好顶了回去。后来那个窝囊皇帝身边的日本顾问池田大作老鬼子又亲自上门请‘老神仙’做伪满洲国的参议,还派了两个鬼子给‘老神仙’把门。‘老神仙’看躲不过去了,就把把门的鬼子杀了,回到了老林子里面。这几年不知多少大绺子要接‘老神仙’养老。他却总说世道太乱、忠奸不明,就是自己在林子里面过。好在老爷子从小就是练家子,后来又不知吃了多少千年老参、三腿林蛙什么的好东西,身体硬朗得很。”
“若关东父老,上至古稀、下到弱冠都有老爷子这样的气节,何愁国土不复、中华不兴!”柳应元轻声念叨着。
“我出去迎迎!”槐花一跺脚,走出了木屋。
“杀八方”站起来:“走吧,整队,点香炉,迎接‘老神仙’上山。”
老狼营和别的寨子可是大有不同,用木头围成的围墙里面,整整齐齐地盖着几排木头屋子,有食堂、宿舍、客房、作战室、会议室。大片的操场上有用木头做的单杠、双杠和一个老高的大木头架子,几条掺了人头发的粗麻绳从上面垂了下来,做了一个简易的攀爬训练器。
围墙的四角各有一个岗楼,成对角线布置两挺花机关和两个神枪手。寨子最高的岗楼中间架着一挺马克沁机关枪,一面布满了弹洞的青天白日旗高高飘扬在这个岗楼上空,旗上面3个大字“老虎团”。
这会儿,除去在外边放哨的弟兄,老狼营六十几个人全副武装、刀削斧凿般整齐地列着队,“杀八方”、柳应元和“山兔子”在院子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几个人顺便就把打“活牲口”的事情合计了一下,可是事情都说完了也不见“老神仙”的踪影。
“这咋还不到,不会是‘大疤瘌’犯浑把‘老神仙’给气跑了吧?”“杀八方”着急地说。
“不能吧,再说大小姐不是下山去迎了吗?”柳应元面色平稳地说道。
“山兔子”还在说话,就听“杀八方”说了句:“快点别说了,到了。”
果然看见几个身影从小路走了上来,快到寨子门口的时候,柳应元大喊一声:“立正!”队列马上昂首挺胸起来,六十几人纹丝不动。
奇怪的是,“老神仙”不是“大疤瘌”背上来的,而是槐花!
只见她娇小的身躯背着老人吃力地挪动着,“大疤瘌”在身后黑着脸背着“老神仙”的老洋炮,不知在嘟囔什么。柳应元赶紧迎过去:“大小姐,我来。”
“不用,我自己能行,能背‘老神仙’爷爷是我的福分呢!”槐花脆生生说道,满是汗水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眼看着已经到了山寨大门,“老神仙”一看迎接自己的架势,笑呵呵地说道:“闺女把我放下,别坏了道上的规矩。”
“哎!”槐花答应一声,利落地把“老神仙”放在地上,退一步扶住。
“敬礼!”柳应元大喝一声,队列齐刷刷地举起了步枪,“杀八方”带着“山兔子”、柳应元和回到寨门前的“大疤瘌”单膝跪了下去。
“杀八方”朗声说道:“小崽子‘杀八方’带着老狼营四梁八柱恭迎‘山神’圣驾。”
站在旁边的队列敬着持枪礼齐声说道:“恭迎‘山神’圣驾。”
老山神呵呵一笑,双手虚扶:“起来吧起来吧,乱世当头就别再弄这套虚礼了。我说‘杀八方’啊,是你当了官军了,还是官军靠了绺子啊?你这寨子,就是东北军军营的样子。”
“杀八方”站起来拱了拱手:“‘老神仙’要说我‘杀八方’当了官军也行,说官军投了绺子也行,只要是和小鬼子拼命,怎么说都行。”说着,把身后的柳应元、“大疤瘌”、“山兔子”一一介绍给“老山神”。
当介绍到槐花的时候,“老神仙”眯缝着眼上下打量这个英气逼人、腰间别着一把勃朗宁的小姑娘:“你这倔强性子和你爹一样,非要背我上山,是想求我给你爹报仇吧?”
槐花眨巴眨巴眼睛:“‘老神仙’爷爷,你认识我爹?”
老头笑呵呵地说:“你爹?不止你爹,我还认识你呢!你小时候,我还喝过你的满月酒,看你这眉眼中的英气,和小虎子真是像呀。”这话一说完,槐花的眼睛马上就红了。老狼营的弟兄们也低下了头。
“杀八方”眼看着气氛压抑下来,连忙说:“‘老神仙’腿上有伤,走咱们到屋里面唠去!”槐花马上上前一步扶着老爷子,几人走进了议事厅。
这个季节是不缺野果子的。议事厅正位前的几子上,摆满了野沙果、山里红、山葡萄、沙棘子,都洗得水灵灵的。槐花拿着纱布和金疮药想为老山神包扎伤口,老头一笑:“不用了不用了,明天找两个小崽子跟我下山把那人熊弄回来,人熊油涂在伤口上比什么都好使,今天就别费劲了。”
槐花牙一咬,跪在地上:“请山神爷爷为我爹报仇!”
“快起来快起来!”老山神虚扶了一把搀起槐花,问道:“报仇,你要找谁报仇?林清吗?还是当时围攻你爹的日军指挥官北条云次,还是暗算你爹的伊贺流忍者?退到关内没有支援你爹的少帅算不算?”看着槐花深思的表情,老人缓缓说道:“好闺女,这一路你就和我这个老头子磨叨着报仇。人这一辈子,不能只为报仇两个字活着,要说报仇,全关东的汉奸走狗都是仇人,这几十万日本关东军都是仇人。别想报仇,想杀鬼子汉奸,鬼子汉奸都杀完了,仇不就报了吗?”
槐花脸色一暗:“‘老神仙’爷爷,槐花明白了。我,我以后能叫您爷爷吗?”
“能啊,当初我答应大帅不再当胡子,还是你爹带兵接我下山,那时候他就叫我老爹喽,你可不正好叫我爷爷吗?”“老神仙”爱怜地看着槐花。
“爷爷,爷爷!”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自小失去了母爱,父亲又牺牲在战场上。现在故人如亲人,好不容易见到了,槐花扑到“老山神”的怀里痛哭失声。
“好了,好了,再哭闺女可就不俊了。”“老山神”轻轻拍着槐花的后背,劝着槐花,让依然抽泣着的槐花站到自己的身后,随后缓缓抬起头,“‘杀八方’啊,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要是我这老东西的眼睛还没有花的话,你们绺子里面小崽子的枪都是新擦新上油的吧。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杀八方”心里暗叫一声厉害,连忙不敢隐瞒,把自己要打“活牲口”的绺子的事情报了出来。
“‘活牲口’今年也有50了,怎么还干这种不要脸的事情。你们东家说得好,就是要他倒旗吞枪!这绺子也有六七十人,你们是要全寨开拔吗?”老山神眉头微皱一下问道。
“‘老神仙’,要是我们全去,就太瞧得起他了,20人足够了!”“杀八方”大大咧咧地说。
“20人?你们有点装大了吧?”“老神仙”惊讶地问,“那‘活牲口’的绺子是在姥姥岭半山腰的山洞里,只通一条盘山小道,前几年东北军围剿,300多人也没拿下呀。”
“‘老神仙’,这事我们是这么合计的。”柳应元把作战计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这能成?那你们绺子里的小崽子不都成了神兵了?”“老神仙”疑惑地摇了摇头。
“能成,肯定能成,要不这半个多月可就白折腾了!”“杀八方”有点兴奋地捏了捏腰间的盒子炮,“嘿嘿,‘老神仙’,明天柳应元兄弟看家,您呐,就和您的孙女带着‘山兔子’兄弟弄人熊去。等熊肉炖好了,我们也该回来了。”
“你们的事我可不管,就是一条,你们给我带个活口回来,老头子要练练手艺。”老山神慈爱的目光一扫而空,刹那间变为一脸厉色。
因为明天有行动不能喝酒,晚饭吃得很简单,野鸡丁子酱拌手擀面。吃过饭后,“老神仙”回到给他安排的客房里和槐花唠嗑,关于大帅、关于刘虎,当然槐花的话题更多的是关于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