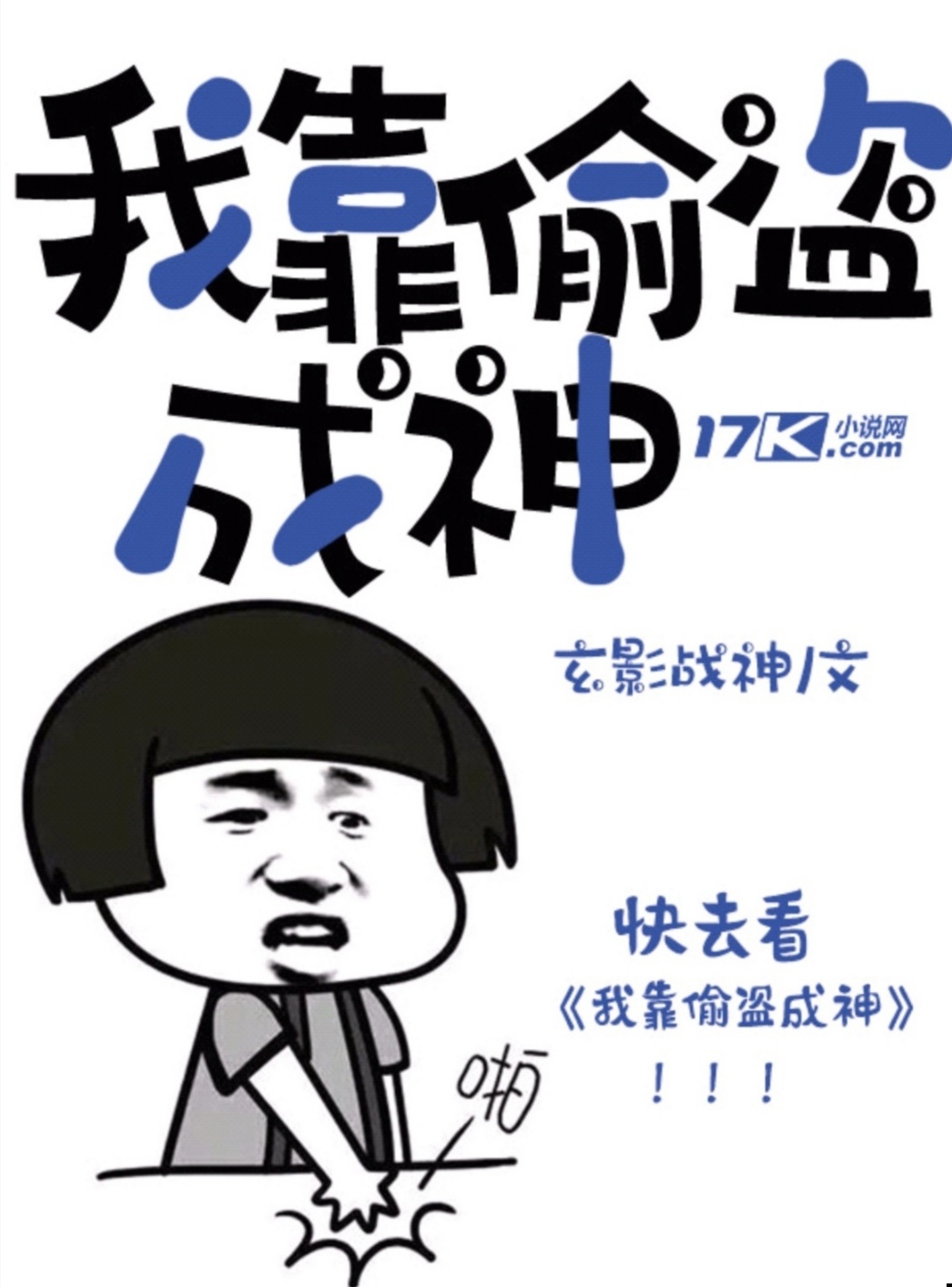千花心下一紧:来干嘛?来整你呀!但是嘴上万万不能这么说,脸上也要堆满楚楚可怜的无辜状,低垂脑袋轻扭腰肢,吞吐的每一个字眼都不得大气粗犷,压抑得委实……肉麻:“想你得紧,身子一好,便急着想来服侍你才好。”
“不用了,自己回去好好歇息罢。”南漓月自行退下黑绒大鳖,回应的语气不似一开始的那般生硬冷绝,只是犹自不肯留千花在此发骚发 浪,卷起千堆雪。
千花不甘心就此离去,总要亲眼看他躺上荆刺床痛上一痛方才爽快,便继续施展狐媚术勾引道:“你为什么迟迟不肯给我机会服侍你?今朝夜已深了,我候你一宿,你好歹圆了我的心意,让我替你掖好被子再走不行?”
眼睛眨巴眨巴,非得挤出些盈盈之光来,小嘴撅呀崛呀,拼命靠近那幽怨之妇去,千花假扮瑶芳主,委实是尽了吃奶的全力,不信他南漓月铁石心肠岿然不动!
果不其然,在眼看着瑶芳主一双倦怠、期待、深深眼袋的眸子即将滚出泪来,南漓月轻叹了口气,伸手轻抚上她苍白面颊,语气比之先前,更加温柔了几分,难得的难得,终于软下心肠答应道:“那便随你吧。”
喜得落千花差点失却形象蹦跳起来,幸而迅速压抑悦色定了定神,又急忙掩去眼底诡笑,然后一把挽住南漓月,便举步往大床奔去,诚然这一拉扯的力道,千花失了算,委实用了大了些,不似瑶芳主的手无缚鸡之力,她落千花分明是在豪扯一条狼,并且事后证明:还是一条色狼!
被落千花大力扯到床边的南漓月终于再也绷不紧一张冷酷到底的脸,俊颜舒展开来,如五月春风拂柳飞絮,委实迷醉人心至死方休,含笑斜睨落千花,笑里竟有三分冷嘲七分戏谑:“蝶儿今朝为何如此性急?本君三月未曾宠幸与你,不过是担心你身子过虚无力承受,并非为了那只刺猬转移了心,你莫须担心。”
这话一出,落千花无端怒从心起,好歹南漓月不似狂泽出语伤人,一开口就是那“该死的刺猬”,但南漓月这句话,却怎么听着怎么不顺耳,比狂泽的咒骂更加不堪入耳,逼得千花五官一皱,再也维持不了瑶芳主的温柔媚波,厉声喝道:“三个月没宠幸了你还好意思说啊!”
咦?不对呀!明明该维护的是南漓月语下不屑的“刺猬”,怎么扯到三个月没行房事的敏感问题上去了?
这惊天动地的一声吼啊,莫说是千花自己吓得不轻,连南漓月都面色微怔地盯着自己好半天没说半句话,深邃狼眸阴晴不定,半晌方恢复云淡风轻,若无其事地问了句:“蝶儿还睡是不睡?”
“睡!”千花下意识狠狠一载头,回得声如洪钟、气势磅礴。
“那本君替蝶儿褪衣。”岂料南漓月压根不管不顾这瑶芳主何以突然转了性,抬手就往千花领口招呼,惊得千花连连后退,一下撞上床头龙凤柱,后脑生疼欲裂,耳畔嗡嗡直响,以至于轻纱外套是如何不见了的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