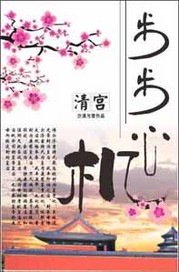秋风飒飒地涌进来,满室的纱帷齐刷刷地飘飞纠缠,混着日光交错在温娘的脸上,看起来是那样的不真切。
温娘咬咬牙,仰头注视着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王妃您。如果不是汉王专宠王妃,我又怎会被赶走,我的孩儿又怎会胎死腹中?我心怀怨忿,特意向汉王求情让我留在你身边当个奶娘,汉王早就忘记曾经临幸于我,所以根本未加防备。我便趁机服食了毒药,我的孩子既然保不住,你的孩子也别想活!”
善儿的哭声更厉,仿佛细小的刀刃在剜着我心中的柔软,不管怎么说,孩子总是无辜的呀!
我一把抓住温娘的手腕,怒火深注于她慌乱的眼眸,正欲说话,那个大夫却摇头道:“你撒谎!你一个下人,如何能弄来这样稀有的毒药?何况,能够使自己日食毒药却并没有毒发,这药的分量则需要拿捏精确。如果没有人指导你,你又怎么会懂得这种玄奥的道理?”
“不,不是!”温娘激动地望着我,热泪翻涌,“没有人指使我,这一切都是我做的!都是我!”
我向后退一步,不,不可能,倘若事实真如她所说的那样,她看向善儿的目光又怎会如此爱怜而慈善。记得谁曾说过,一个人的眼睛是无法诉说出谎言的。
哭声枭叫般回荡在屋子里,我不顾众人的惊呼,蓦地跪下来,抓住温娘的双臂道:“温娘,我不管是谁指使你,我只求求你,告诉我,善儿中的什么毒,解药又是什么?这孩子一出生就由你带着,我看得出来,你也很疼他爱他,你不能害他呀!”
温娘坚定地摇摇头,卧在地上失声痛哭,猛地又通身痉挛起来,咳出一口黑血。
我瞧着不妙,急忙晃着她叫道:“求你,快告诉我!快救救善儿!你有什么为难之处我都可以帮你!求你!”
温娘的身子不受力的委颓下去,她艰难地张开嘴,想说话却说不出,最后无限凄婉地望向啼哭不止善儿,缓缓阖上了眼眸。
大夫慌忙上前,查探她的脉息和口舌,接着失望道:“她在牙里塞了毒药,方才那一瞬,服毒自杀了。”
我呆愣在原地,连哭泣都忘记了,任由鸢儿将我拖起来。
她死了,怎么办,我的善儿怎么办?
康信之面对眼前的突变,也骇得不清,他担忧道:“王妃,属下必须立即启程赶往江州,世子的事……是否要让属下通知汉王?”
“先别说,”我脱口而出,他那边政局更是诡谲,我又怎能让他为此分心,“世子只是中毒,未必有性命之忧,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康信之惶恐道:“这……这恐怕汉王知道了必会怪罪下来。”
我略微思忖后,对他道:“信之,我恐怕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你在王爷身边要提醒他多加小心。至于世子,三日后世子的病若还没有好转,我自会托人修书给王爷。”
“是,属下遵命,”康信之跪地拜礼后,又仰头望着我,踟蹰道,“王妃可有什么话要带给王爷?”
我侧头看了一眼善儿,他服下药后,哭声渐止,粉雕玉琢的面上红彤彤的,眼角还挂着几串清如露水的泪珠,我忍住心中澎湃的酸痛,转向康信之道:“告诉王爷:‘家中安好,勿念’。”
康信之顿了一下,遂即点头,站起来火速去了。
善儿轻轻哭咳了一声,细致、洁白如海贝的指甲深深嵌进肉里,我紧张地抱着他,将脸贴在他吹弹可破的脑袋上。他拿小脚胡乱踢着我,不重却惹人心疼,我抿着唇,泪水夺眶而出。
————————————————————————————————————————————
温娘死后,我命人将她偷偷葬了,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她也是受害者。在她背后,一定有人操纵着一切。那人会是谁呢?
温娘曾经说过,她是徐寿辉送给陈友谅的侍婢,难道那背后之人是徐寿辉?
可如果是徐寿辉,她既然不惜用性命去保护那个人,又怎会一开始就说出自己是徐寿辉的人呢?
这件事情,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我实在是想不通。
除非,有人想要挑拨离间,加速徐寿辉和陈友谅的内讧。
至于那人是谁,我想不出,也不敢想,我现在唯一担忧的就是善儿的病。
一连两天,善儿的病都没有好转,夜里常常失声哭泣。没了温娘,他便失去了母乳,而自从温娘的事情后,我再也不敢让别人给善儿哺乳。偏偏我的身子又弱,奶水不足,根本不足以供给他的需要。
日子过得焦头烂额,直到有一天,一位青衣老先生登门拜访,说是能治好善儿的病。
那老先生目若寒星,眉似漆刷,高瘦潇洒,通身弥漫出一股令人捉摸不透的出尘之气,却又慈善和蔼,让人忍不住与之亲近。
我亲自出府相迎,还不及说什么客套话,他便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入内室。他见到一味痴哭的善儿,先是“咦”了一声,然后面泛红光,眼中也露出几分兴奋的神采。
“还好,脉相未竭。”不容我多说,他迅速从腰间掏出一块沉甸甸的白布铺开,一套二十四支银光闪闪的长针赫然在目。
他凝神静气,双手拈起银针在灯上灵巧地翻淬,片刻后,他转向善儿,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眸却直盯着我。
我瞧得心慌意乱,却不知为何并没有制止他。
他见我默不作声,突然指尖发力,七根寸许长的细针闪电般迅速刺出,无比精准地刺在善儿的头项天柱、承灵、络却、脑空、风池、完骨、头维七大穴,针入盈寸,只露出森寒的针尾,令人看得触目惊心。
几乎是同时,有人惊呼:“这些都是死穴!”
善儿“哇”地一声哭喊起来,嘴角涌出黑紫色、粘稠的血液。
我数次深呼吸后,依旧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怒视着那位老先生:“你做什么!”
他则一脸坦荡地继续施法,用手缓缓捻动银针,调整着针刺入的深度与方位。
王府里的大夫在一旁瞧得目瞪口呆,通通说不出话来,只听那老先生气定神闲地说:“毒已经清得差不多了,等下我再写份药单,你们照单抓药,一日两贴,三日后,这小家伙必会药到病除。”
我将信将疑地看向其他人,他们均诧异地点头,示意他说的没错。
高悬多日的心终于稳当当的落下,泪水却再度充盈在眼眶,我转而感激道:“阿棠多谢老先生救命之恩,敢问老先生高姓大名?”
“阿棠,”他手中的活计未停,眉头却深锁,目光更是深沉,“难得,你还记得自己叫做阿棠。”
我心下骇然,疑惑地看向他若有所思地面庞:“您这是什么意思?”
他突然猛拍善儿的脑袋,只听“哇——”的一声疾哭,七支银针齐刷刷的飞出,相继滚入他的白布中。
我瞧得瞠目结舌,他收起白布,转过身淡淡道:“孩子已经没事了。”
我奔向善儿的摇篮,看着他哭声渐弱,缓缓转入睡眠,瞬间泪眼朦胧。我哑声道:“多谢老先生。”
“不必谢我,”他定定地看着我,炙热而深沉,“孩子的病好了,你的病却还没好。”
我讶然回首,茫然地回视于他:“本宫的病?”
他点点头,抚着胡须叹息道:“你得了离魂症不是吗?”
心神牵动,他怎么会知道我得了离魂症?又为什么总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难道说,他认得我?还是,他也是什么人派来害我们母子的?
想到这里,我警惕地抬起双眸注视着他,一言不发。
“如果你愿意,”他深深望着我,眼里竟有一丝悲悯的意味,“我可以治好你的病。”
不是不心动,但,直觉告诉我,那将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决定。
更何况,我已经答应陈友谅,要忘记过去,与他重新开始。
哎,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本能地畏惧那些虚无缥缈的往事了?莫非春儿的话,到底还是影响了我?
我踟蹰地看向善儿,他脸上因病痛的晕起的红光还未消退,更显其娇弱可人。我蓦地下定决心,冲他摇摇头:“老先生的好意,本宫心领了,但本宫并不觉得自己有病。”
我仰脸示意鸢儿,她会意地进里屋端出一个沉甸甸的盒子,俯首恭谨地递给老先生,我笑道:“还请老先生务必收下。”
他挑开盒子,金灿灿的光芒耀满他古拙的面颊,却像是一种亵渎,这个发现令我蓦然觉得心虚。
他淡淡一笑,吊起一只眼睛觑着我,似是在想一件极遥远的事,继而洒脱地抱起盒子转身阔步而出,我长长嘘一口气。
苍劲豪迈的歌声却又从他清瘦的背影中漫出:“白虎奔原,青龙腾野;朱雀启战,玄武逆世。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世界将一大变,黄天将死,苍生将生。”
朱雀,玄武……
记得那个梦里,我仿佛也听到过类似的话。
我的头突然昏胀起来,身子更是鬼使神差追出去:“老先生,等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