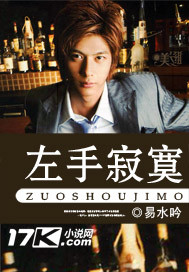渐渐地,箫音由若断欲续化为纠缠不休的云烟,转柔转细,充盈于彼此每一次轻微呼吸中,偏有来自无限远方的缥缈难测。明亮匀称的音符伴着夜风以一种极度内敛的缓缓绽放,我微睁双眸,仿佛看到一只红狐狸在某个神秘孤独的天地间踽踽独行,那种苍茫的触感勾起人深藏的痛苦与欢乐,涌起不堪回首的伤情。
蓦地,箫音倏歇。
我抬头轻声唤他:“阿谅……”
陈友谅挑起床帘,轻轻道:“吵醒你了?”
我摇摇头:“从未听过你吹箫,却觉得熟悉得好似上辈子的召唤,让我忍不住想要抓住那份流水般易逝的感觉。”
我说着,伸手抚上他的眉梢:“告诉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哪样子?”陈友谅闭上眸子,那些难以言道的情绪也一并收敛到眼皮底下。
“蹙着眉,苦大仇深的样子。”我笑了,贴着他的手臂轻声道。
陈友谅轻搂着我的肩,声音清淡而幽远:“小时候,我出身不好,我还有个哥哥,这些你大概都忘记了。原谅我总是不想对你提起以前。这么说吧,你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我和你本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后来你家出了事,唉,说过不提过去的……”
在这个时代,家世和地位往往最直接地左右着一个人的命运。陈友谅出身低微,所以每一步都爬得异常辛苦,即便功高盖主、权倾朝野,也不得不顺应朝臣儒士奉徐寿辉为君。
我点点头,喟叹道:“结果是好的,就足够了。不管以前经历过什么,我拥有你,你拥有我,这一刻我已经知足。”
陈友谅将我搂得更紧,脸颊贴着我的头发:“还有一件事,徐寿辉执意要将沈卿怜留在王府,你知道我,绝不会碰她分毫。但你若不喜欢,我就推脱掉。”
心如针扎,我抿唇片刻,叹气道:“你不能拒绝他,因为你想要更深更高的权利,就必须先顺从他。阿谅,不管怎样,我信你。况且我现在身怀六甲,而你是个男人,更是个王者,即便你真的纳她为侧妃,我也……”
“傻丫头,我说过,你才是我的唯一,”陈友谅点点我的脑袋,意味深长道,“所以我想有个孩子,一个能继承我所有理想和荣耀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会再因为身份而寸步难行,他一生下来就会是摄政王的嫡子,他会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天空。而且我知道,你也想要这个孩子。当然,我绝不会勉强你,一切还都看你,你若是想要这个孩子,就每天乖乖喝药;如果不想,我也不会介意,反正来日方长,咱们还会有孩子的。”
我吐出一口气,将头深埋在怀里:“但愿天遂你我之愿。”
陈友谅沉默,良久将我身上的罗衾盖好,起身道:“睡吧。”
我阖上眼,却在他走出帐外时悄悄打量着他,烬了三更的灯花又被燃起,他垂首伏案,翻看着繁复的军报或是地图。
烛火丛丛跳动在他的背影上,他顿住,翻起,又顿住,如此反反复复的,愈发寂寞而萧然。
我疼惜地注视着他,我是他的妻子,他的王妃,无论今后如何,我都要坚强勇敢地站在他身侧,再不让他蹙眉,再不让他为我而忧心。
——————————————————————————————————————————————
陈友谅日日忙于公务战事,并不能时常陪伴我左右,但只要他人在汉阳,就会呆在我的寝宫中。
这些日子,我有孕不宜外出,便闲来无事从下人口中了解了当下全国的战局。这才知道,如今元朝已是强弩之末,义军三足鼎立,天下隐有三分之势。其中最强的,就是陈友谅的天完军和韩林儿的宋军,而韩林儿的宋军中又以吴国公朱元璋势头最劲。而陈友谅的军队也频频与之交火,自我孕后,赵普胜又前往前线由池州攻打太平,两个月后朱元璋战败,太平沦陷。
恰逢大都地动,人心浮动,地动乃“龙翻”之兆。所谓“龙翻”,就隐隐有天下易主的意思,陈友谅于是在这时将我的孕事昭告汉阳百姓,极力渲染福祚之象。
为了安稳民心,鼓舞士气,我决定上净土寺祈福,祈求“弥勒降世,普度众生”。这也是陈友谅的意思,我现在正怀着孩子,倘若生下的是个男婴,他便是所谓的“在世弥勒”。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初春柳枝新发,傍水长街上全是熙熙攘攘的百姓,有汉阳本地人,也有从附近城镇赶来的。
我忍着身子日渐沉重的痛苦,坐在华贵的车辇上,身上披着云天水漾纱衣,里面是绣有白莲华缎。所到之处,我都让侍女们遍洒钱币,绸缎,并令教士们沿途诵经为天下苍生祈求福祉。
那些屠戮生灵的战争遥远地像夏商时期的故事,人们只是欢喜于眼前天完王妃的恩赐,笑脸洋溢着离散背后的艰辛幸福。
这一刻,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让我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我不觉抚上自己的小腹,因着这个孩子,我不再是刚失忆时那个惶恐无知的女孩子,而是与汉阳、与天完血脉相连的一份子。
原来的我,好像一浮无根的飘萍,而孩子却是最饱满的种子,拉住我在坚实安全的土壤上,破苗而出,生长成参天大树。最后,我们都会盛开出生命中最绚丽的花朵,为自己所挚爱的这片土地,为所有善良的灵魂飘洒出真挚的芳香。
沈卿怜被留在了汉王府,陈友谅给她一应最好的一切,却独独从不踏进她的别苑半步。偌大的王府里,只余我这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妻室,也有坊间传言,说我专宠惑主。对于这些,我只笑笑并不制止,流言止于智者,蜚语向来小人。
鸢儿曾有意无意地暗示我沈卿怜在背后传了我不少风言风语,我在心中暗叹,她也是个不幸的女子。生于乱世,红颜飘零如花,落花虽有意,流水却往往无情。任你风华绝代,任你显赫非常,一旦攀上男人们的权利之争,就只有旋入政治的风波中不能自己。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溺死其中,但好在,我的身畔有陈友谅,有这个未出世的孩子,我已比她幸运太多。都是女人,何必为难彼此?
有一日,陈友谅离汉阳巡视,我坐在蔷薇花架下,凝望着天边疏淡的云朵,出神地想着:我的记忆也恰如这抹云华般飘渺失真,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我能拥有记忆,也就能知道腹中的这个孩子究竟是谁的骨肉了。
但如果他真是那个“朱元璋”的孩子,我又该怎么办呢?
想着想着,忽觉有件轻软的狐裘披风搭上肩头,我侧头,是春儿。
这丫头虽进府时日不长,却极为贴心,简直堪比我肚子里的蛔虫,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还未说出口,她便会及时奉上来。
春儿俯身恭声道:“王妃,这天气乍暖还寒的,您性畏寒,又怀有身孕,还是快些回屋里去吧。”
我搭上她的手,缓缓走入寝殿中,清淡恬静的百合香萦绕在身侧,让人心底说不出的舒心。
我不觉道:“百合香也是你点的吗?你来之前,鸢儿就从不会点这香。”
“是奴婢点的,”春儿的眸子里忽然异彩涟涟,她诚恳道,“这香味道淡雅,静心怡人,奴婢私下以为淡泊如王妃者,必定喜爱这香。”
我听得触动,转向她奇道:“你进府不过两三个月,为什么对我的习惯如此了解呢?”
春儿仰起头,神色复杂地望向我,欲言又止。
瞧着她的模样,我越发好奇,示意左右退下,对着她道:“想说什么就说,不碍事的。”
春儿抿着唇,似是下了很大决心,蓦地凑近我的耳边,轻声道:“王妃还记得朱公子吗?”
“朱公子,”我心头一跳,下意识地问道,“哪个朱公子?”
春儿神色有些急迫,她目光殷殷地望着我道:“王妃,您当真全忘记了?他可是您的夫君呐!”
难道她说的是朱元璋?这个可恶的男人,居然派了探子在我身边!
我脸色煞白,气急地指着她道:“你休得胡说,枉我对你亲睐有加,你居然费尽心机地挑拨我和王爷的关系。你究竟是谁派来的奸细,又有什么图谋?”
我说着,就要喊人,春儿吓了一跳,蓦然跪在地上,脱口而出:“奴婢之所以对王妃如此了解,皆因奴婢本就是王妃身边的丫鬟。王妃若是不信,奴婢现在就可以将您所有的习惯嗜好倒背如流。”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心中翻江倒海,她趁机进言道:“王妃,您知道您在做什么吗?您根本不是什么天完王妃,您是大宋的镇国长公主,是吴国公未过门的妻子啊!”
我猛地后退一步,难以置信道:“你……你休想凭着这些捏造的虚假之事来诓骗我!你再胡说下去,我就将你交到刑慎司手中。”
春儿不依不饶地抓紧我的裙摆,目光焦虑:“王妃,奴婢今日既然说了,就不怕一死。死则死矣,但求王妃不要执迷不悟、为虎作伥,与贼人相伴呐!难道你就不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家人?汉王又从来不提起?奴婢相信您眼明心慧,必定有所察觉的,不要再自欺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