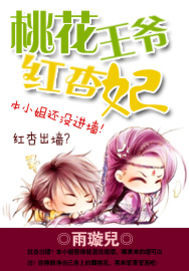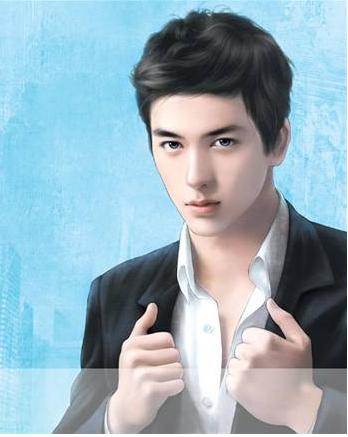温子渥和杨氏面面相觑,底下宫人和太医却早就吓得一溜烟退了出去,温子渥担心地扶着魏帝的胳膊:“父皇,您刚刚吐了那么多血,还是先让太医来——”
“混账!什么时候朕的话要说第二遍了?!滚,全部出去!”
杨氏像是突然回了神一般,赶紧拉着温子渥跪下道:“谨遵皇上旨意,臣妾和太子先行退下!”
说着,她便和侍女一左一右拽着温子渥退了出去。偌大的明殿,虽是半夜亦是灯火辉煌,象征魏国皇室的黑底金色的龙纹图样处处可见,庄严耀目之下,却是一片叫人窒息的冰冷。
“说,你到底是谁!是谁派你来的,说!”
看着魏帝衣襟前的点点血迹,还有他眼中发红的血丝、有些散乱的发髻,姚今想起慕容子华那一闪而过的脆弱和失神,心中不禁有些莫名的快意,刚才被勒得过紧的嗓子不自觉猛烈干咳了几声,她慢慢爬起身来,将那张符纸投入旁边的火盆之中,“魏帝陛下,这个符是假的,厌胜之术也是假的,连我巫女的身份、刚刚我说的那些话,也都是假的!但,有一件事是真的。”
“什么?”
“温承先,你快要死了,你真的快要死了!像你这样满身罪恶的人,白白活了这么多年,真是严重地浪费资源——”姚今哼笑了一声,很轻,却很冷,她重新走到魏帝的床榻前,站着,居高临下地睥睨着魏帝无力地半倚在软枕上,“我是来替你儿子、替雪族结束你的罪孽——噢,或许你还不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儿子,你也不配知道……”
魏帝的脸色惨败突然转为紫红,他瞪大了眼睛,胸口起伏不定,“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什么儿子、什么儿子?甄姬她背叛了朕,她嫁给了小小闽国那个没用的慕容扶苏,她还冒着一尸两命的风险早产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些朕都知道,你是谁?你竟敢胡言乱语!你别妄想骗朕!!”
“她是嫁给了慕容家,可是她为什么不回自己的母族雪族去?她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闽国?她为什么要嫁到那个你的势力永远也不可能触及的遥远之地?你说她为慕容扶苏生孩子?了不起的魏帝陛下,你可知道,慕容子华周岁之后,她才侍寝于慕容扶苏!你说,她这个儿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姚今的句句紧逼,似乎将魏帝整个人都快要击垮了,他茫然地看着四周,双手毫无目的地在床上乱摸,“她有了孩子、她有了我的孩子,她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朕说过会弥补她的!就算她要当皇后,朕也会给她的!她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那样伤了朕的颜面,让朕与她无法相见!”
“皇后?一个虚无缥缈的皇后之位,能抵得了雪族的灭族之恨?抵得了你对她的欺骗、利用再利用?”姚今摇摇头,“你果然是个无情无义的该死之人,若我是慕容子华,早在第一次进长青宫时,就该结果了你的性命!你这样的人,多活一刻、多呼吸一口气,都是罪孽!”
“第一次进长青宫?你是说——他、那个孩子!”魏帝的脸色变了又变,他颤抖着声音道:“他是谁!他在哪?在哪!”
“在这。”不知何时,大殿的一处烛台后走出了一个人,没有太监的衣服,没有人皮面具,他穿着一身白衣,闽国皇室的服制,如清风儒雅,似白云万里。姚今一愣,随即紧张地奔了过去:“你怎么进来的?”
慕容子华没有回答她,他伸出手将姚今拉到了身后,并且还按了按她的肩膀,似乎是示意她不要跟过来。而他的目光直直落在前方——那张很近又很遥远的龙榻上。
“慕容,你不可以!”姚今清楚地知道,她应该离开、应该给这宿命中终要相见的父子二人一点时间了结恩怨,此时任何一个稍稍知晓情理的人都应该静静退出或者守在门外——但是她不可以,她更加清楚地知道,此刻她绝对不可以离开。因为她不敢确保慕容子华会不会上去一剑砍了温承先的脑袋,她更不知道现在这座明殿外是什么情况,杨氏、温子渥,还有慕容子华的那些暗线到底在什么位置,他们会不会突然也冲进来,一剑砍了自己的脑袋。姚今深吸一口气,转身拽住慕容子华的胳膊,一字一句地说:“我说过,你不可以,让我来!”
“姚今,我若要动手,你拦不住。松手吧。”
仿佛他只是轻轻地一拂袖子,姚今整个人已经被震退了几步,然而就在他那轻飘飘的几个字里,在他那似乎很寻常的一个动作里,姚今感受到了巨大的颤抖,以及他深入骨髓的恨意。
“这座长青宫的每一寸砖石、每一扇门窗,日日夜夜都如在我的眼前,就像雪族的每个人、每张脸,时时刻刻都在我母亲的脑中,二十多年来,从未消失过。”慕容子华一步步走上了台阶,走到了那个人的面前,“闽王的太子慕容煦因为贪恋皇位又对父王误会极深,曾在他的病榻前欲行大逆不道之事,最后他失败了,可我不会。今日今时,就是你的死期。”
话音未落,慕容子华的手上不知何时便多了一把明晃晃的短刀,那刀柄两面分别是两朵形态各异的莲花,花瓣之间点点银光闪烁,仿佛是晨露一般栩栩如生,定睛一看,竟是极其精致地镶嵌了许多粒细小的月光石。只见这把短刀紧紧地贴上了魏帝的脖子,贴上了他苍老而松弛的肌肤。魏帝没有抵抗挣扎,他用一种不敢置信又充满怨恨的眼神狠狠盯着眼前的慕容子华,他沙哑着嗓子道:“你真的敢吗?我只要一喊,外面的人一进来,你们都得死!”
“我保证你还没喊出声,这把刀已经切断了你的喉咙。”
“这把刀,是我亲手为你母亲打造,她就是要你用这把刀杀了我,杀了你的亲生父亲?呃?”魏帝微微眯起了眼,他看着这个人,这个人的眼中有和他一样的狠绝,比他年轻时还要难以捉摸的眼神、难以辨别的喜怒、不能分明的爱恨,可他仍然从自己老迈的肌肤上,明明白白感到了来自那把短刀之后的,极其细微的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