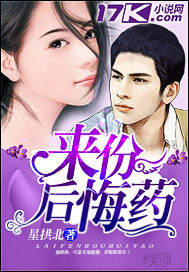我去过很多地方,拍过数不清的照片,也尝试过不同种作品风格。某段时间我的影集相继在不同的展区展览,风格被同龄人赞叹,吸引别人的目光,但是我的导师一致认为我是他带过天赋最差的人,最没有艺术细胞的学生。
在我大四那年,我收到一家旅行社的邀请,去跟拍一期美食周游记。虽然旅行社是在日内瓦,但是拍摄地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另一个小的城市,宣传的也是当地的旅游节的美食文化。我的导师对于我选的这个课题嗤之以鼻,他认为我应该像其他同学一样扎实艺术修为,锻炼自己的审美能力,然后在更高感知力和理解力的水平上去做反省意义的纪实摄影。因为在这个专业中,我算是艺术造诣比较差的学生。
在他看来,拍摄者本身的价值观和艺术修为直接创造作品的传导能力和影响力的高度,一张有水平的拍摄作品,除了能展示作者的高超的艺术技巧之外,同样在它背后有价值的人文因素也能更清楚和直白被表达和理解。我虽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在我看来,一张照片和十几张一系列的照片创造同样的故事,在表达感情的维度和深度上本身就不可比较,再在拍摄艺术上做更多要求也就没有必要了。
在我没毕业前,他一向认为我的摄影作品是快销式的广告产品,虽然能迅速打开知名度,但是并不能帮助我在艺术上走得更远,为此他是坚决不赞同的,也终于承认我的艺术创作还有药石可医。不过我对于摄影作品的认识和观念,同我学习书法绘画一样,我不认为我是能走艺术这条道路的人。导师表达了他的遗憾,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中情感共鸣能力算很强的人,但我的选择,他也尊重。
是为寄托,以前我拍人文静物,后来我拍山川锦绣,在我的所有作品里,我赋予记录的能力远远大于创造的能力。除了拍摄了“我”的作品。
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是在11年,我在Cotswold接到外公生病的消息。
我的外公是在11年冬末过世的,来年春天外婆也病重去了。
外公病重期间,坚持不肯去医院住院,他仍保持了老将军的威严在,因此我们一家没有人再反对他的决定,只好请了军院里的家庭医生就近照看。那一年我刚完成本科生的学业,进入研究生部队,正是课业最忙碌的时候。母亲9月份就提前回了国,等我11月份回去一家团聚。知道我一直挂念外公的情况,母亲就拿我让她带回去的相机记录外公的康复情况,晚上等我下完课,我们通过电脑视频聊天。
外公身体不佳,但在镜头前努力保持精神和微笑,外婆也是。她好像已经对于我外公的病非常看开了,没有我想象中的愁容。我想这个时候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只是需要时间接受。
母亲跟我告状外公在家不肯吃药,说他听我的话才会吃,让我监督,于是早晚我打电话回去。通话接通,还没等母亲说,外公的声音从那边传来。
“我正要吃呢!”
“小曦吃饭了没有?”
“小曦啊,不用你总挂念我,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他的声音中气十足,好像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等他说完之后,母亲才抱着电话默默流泪,跟我说因为吃完药之后对身体产生的副作用会让外公很难受,夜里他睡不着,偷偷起来让外婆陪着在院子里走,花圃里他种的水仙、玫瑰、槐树、桑树、柿子树和石榴树,一砖一瓦一台阶,他都要摸一摸。她看着非常不忍心,也非常难过。
外公的脾气也越发像个老顽童,需要人让着,宠着,哄着,出去哪总要跟他说,不能让他找不到人,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
母亲说,何曦,原来你小时候的脾气是像了你外公,你看你外公现在的样子像不像小时候的你?
她拍家里的照片发给我,有一张照片里是他和外婆两个人躺在躺椅里晒太阳,雪白的雪球安静地伏在他们脚下,院子里水仙花开得正鲜艳。那年家里种了好多的腊梅,一夜接一夜的盛开,还有几株迟迟不开的,母亲说他们护养得很小心,这几日里北方的天气愈发愣了,这花迟迟不开,怕是在等雪,也是在等我。
母亲不懂相机,也不懂拍摄技术和构图艺术,她将院子里的生活记录下来,一张一张地拍,只是想找最好的角度。她说,以前见你在家就常常摆弄,不晓得这玩意用起来怎么难,她说她拍不好,因为我是专业的,一定会嫌丑。可是那些照片,却比我拍过的任何照片都有意义,我最看重也最珍惜。
归家比计划晚了1月,好在花开的时候也回家了,小姨跟母亲来接,说他们一家现在已经搬回来住了,外公和外婆都非常开心,家里人现在都在同一个屋檐下。
在最后那段陪在外公身边的日子里,我们过得很平和也很乐观。外公对生死看得很谈,那段时间他的朋友都过来看他,外公同他们下棋喝茶,大家还跟平常一样,聊着他们关心的家国大事,每个人都不算悲伤。唯有先生来大醉过一场,哭哭啼啼了一夜,像个小孩。
白天他在我家的书房练字,大冬天的解了袄子,一练就是一个上午。
我们好几年没见,先生一点都没变。他看到我第一眼就说:“小曦好久不见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先生练字时地上草纸到处都是,我一边捡起,一边对他:“这些我可要都收藏起来。”
他笑笑,问我:“你外公可醒了?我得找他逗那鸟去。”
外公病得最重的那段时间,已经无力下床自由活动,先生和外婆左右常陪他解闷,读书看戏(戏曲)。先生直接在家里住下了,黄昏里,老日头,陪外公走完了最后的时间。
外公坚强,除了病里这几月,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多药,受过那么多罪。为家里人争取的那么多的时间,我们都很感激,对于他的离开,我们也很坦然。我们一一告别,意识不清时他抓着我的手,低低地唤我小名,不肯睡去。
我想起小时候会经常问他:外公,外公,你爱我吗?你会永远爱我吗?
他永远答,当然,我的囡囡,我永远永远爱你。
这次我低声告诉他,“外公,我相信你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睡了,我在这里陪着你。”
他留恋不舍,依旧是余愿皆成。
外公去世时,父亲也曾赶来,他在屋外站了一夜,外公没有见他,也没有任何话要告诉他。他或许还在怪他,怪他背信弃义负了母亲,惹她伤心了那么久,但是他也知道有我陪在母亲身边,他一定可以放心。对于父亲,他已无愿,也无宽恕,这一面见或不见,没有区别。
拂晓时分,天色冻成灰白色,秋婶惯例第一时间走去厨房,打开窗户,清扫灶台。张婶去抱雪球,给它放到院子里,让它去撒欢。外婆和小姨呆在各自的房间,打电话通知挂念外公的人关于外公离开的消息。我打开外公房间的门窗,院子里水仙花的清香飘来,仔细一闻,还有几树腊梅今夜悄悄开了。家里人一夜都没有睡,脸上只有平静和疲惫,谁都没有再管院子里站的那个男人。
我看到母亲叹了气,看向屋檐下他的背影,也没有说话,也没有留恋。这一声叹气,这一个背影,这一眼便也记了下来。
我想在那一刻,我对他的埋怨又少了几分,因为已经不需要我的怨恨,压在他心里的罪与悔,惩罚他,已足够沉重。
又是一年,三月底,外婆离世,她走的很安祥也很宁静。我们哭得很厉害,一是不舍,二是为她高兴。
外公送给她的弹壳和他的马甲衫她带走了,就像她的针线盒和珍珠耳环外公也带走了一样。年轻时他为她差点丢了命,这一世他们终于相守了要一生在一起的约定。
院子留给了小姨和姨父一家,家里少了人,但是秋婶、张婶和司机都在。小姨说,等他们都老了,这里就是他们的养老院,只要院子还在,一家人就都在。母亲和她将家里外公和外婆的遗物收整了起来,锁在房间里,又种了一片他们最爱的水仙花。落日余晖里,她们姐妹俩相视而哭,哭到最后又笑了起来,这思念已经深深放进心里。
四月,日暖花稀。我和母亲告别家乡返回牛津,父亲来送。姜离匆匆从医院赶来,樱花落至头上,未及拂扫,见到我灿然一笑,我却没有办法回他一样的笑容。
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早已终结,他们之间的愧疚,怨恨和恩爱早就说完,一笔勾销,只有目送的距离。火车站台,他送我母亲上车,没有话别,也没有保重,我和姜离一左一右,终是分道扬镳。
这一年开头,都是告别和离别,母亲心情低落,等我返回学校之后,她就报了旅行团去南非周边散心去了。我回到校园,一切照常。
四月底,从宿管阿姨那收到一份来信,打开来看,只有我的名字和一个干草标本类的书签,没有署名,也没有寄信地址。我以为是粉丝寄过来的,没有在意。其后每年生日,元旦和新年,也有在粉丝寄过来的来信中发现类似的书签,依旧没有在意,以为是国内的狂热粉丝遥寄过来的祝福。直到那次我和安先生闹了别扭,冷静中,在斯普林斯收到他的书信,才知道原来一直寄信的人是安先生。
从出生到我的成长,到我这几年的经历,我一直都认为我是一个比大多数人都幸运的人。但因为年少的时候经历过那次家庭的突变,所以对每段感情特别珍惜和小心。我也知道,人生要足够有福气才能稀罕到温柔和爱,我已经在太多人那里得到过太多,所以我想纯粹的,温柔的去爱人,包括对伴侣终身的爱慕。
我从来没问过安先生,你会永远爱我吗,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早已盖棺定论,安先生早就给了我答案。而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温柔坚定,重守承诺的人,我相信他,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