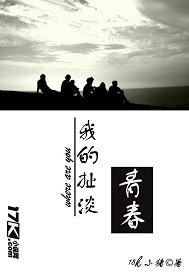汉北大学校园外, 一群大学生正在一家餐厅举办一场聚会。
十几个年轻的面孔围着一男一女拍手鼓掌,唱着轻快而富有朝气的歌。一个圆形的大桌子上,摆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和几束鲜花。今天的女主角是赵泱,这是她二十三岁的生日宴,她旁边的那个年轻男生正是王权。
餐厅老板把最后一个菜拿上来,看着桌上密密麻麻的大碟小盘,说:“赵小姐,你们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赵泱拉开随身的手包,掏出一沓浅蓝色的钞票,往那餐厅老板端菜的托盘上一放,说:“不用找了。”
餐厅老板数了数,装进了荷包。他知道,一向大方的赵小姐这次更加大方,多出来的钱自然是给他的小费。
今天没有其他的客人,这一群青年无所顾忌地饮酒高歌,愉快热烈。
“阿泱,你的命真好,出生在这么富贵的人家,天生小姐命”。
一个女同学艳羡地说道。
赵泱说:“喝酒喝酒,别说那些扫兴事,我那个老爸,顽固派!”
“你还不以为然,别人哪里羡慕得了?”另一个人说道,又把目光转向王权,“你小子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祝你们两个早日结成正果,比翼双飞!”
在他的带头下,其他的年轻人们都举起了酒杯,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过,气氛已经沸腾起来。
赵泱双颊潮红,打了一个酒嗝,说:“你们知道吗?我爸爸想把我许配给一个土包子。这什么年代了,还许配?你们说可笑不可笑?”
大家一阵附和,嘻嘻哈哈地笑着。
赵泱又说:“更可笑的是,他瞧不上我。呸!我还瞧不起他呢!谁知道是从哪个山沟里冒出来的,一身的土气。”
王权轻轻地推了一下她的胳膊肘,示意她不要再说。赵泱转过脸,在王权斯文秀气的脸上亲了一口,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又聪明又好看。”
王权极端不自在,轻轻推开了她,说:“你喝醉了,有点失态了。”
赵泱嘟着嘴巴,说:“来,来,来!今天本小姐生日,大家尽情吃喝玩乐。”
吃完饭后,一群人又来到一间歌厅唱歌,一直狂欢到深夜,才回到校园。而今天的男女主角,在大家都各自回到宿舍之后,难舍难分,又悄悄折身出来,买通了看门的大爷,在外面度过了一夜……
……
盛夏已至,天气一天比一天更热了,栾岗镇的武术比赛复赛如期进行。
雷雄提前两天来到振飞武馆,在和白方平切磋武功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功底已经远远在他之上了。不到十招,白方平已经不敌。如果不是雷雄及时收手,险些一掌拍中他胸口。
白玉在旁观战,吓得脸上一片煞白。
白方平略一站稳,说:“你这一年来,长进竟然这么大,真是神速啊!”
雷雄看了看自己发红的双掌,说:“我总觉得有一种力量随时都要奔跑出来,只有发掌运功的时候,才会畅快一点。”
白玉瞪了他一眼,说:“你倒是畅快,差点一掌把我爸爸打死了。”
雷雄说:“对不起!主要是慧参大师传了我罗汉掌,而我的六曾祖又把他一身的内力修为全部传给了我,我还吃了清霞山水潭里的一种鱼,才有这些变化的。”
白方平释然地说:“你天生是练武奇才啊,又有这些奇遇,这也是老天爷在助你成就武术大事业。”
两天之后,天虽然下雨了,但是观看比赛的人丝毫没有比初赛的时候少。台上撑着高高的一块遮雨布,台下除了评委席上搭了临时的雨棚,后面没有任何东西遮挡。人们或穿了雨衣,或撑着雨伞,都看得十分入迷。
当白玉的最后一声铜锣响起时,人们似乎从梦里醒来,只听这姑娘清脆的声音报着本次入选决赛的名单,成人杰和王振依然在列,还有其他的四人,决赛在半月之后进行。
雨越下越大,人们意犹未尽地散去。胜出的人们依然在星月楼赴宴。这一场大雨让连日来的高温下降了不少,凉风裹挟着雨丝,从窗户里吹进来,使得这些获胜者们更感舒畅。
……
千里之外的云舞崖上,金圣帮总堂,金石和他的徒弟们每天勤加练习,一根长棍已经使得出神入化。武馆整洁有序,纪律严明,已经渐渐有了些名声,时不时有山下的少年想要来拜师学艺,但金石都拒之门外。
这一天正午,树林里的知了呱噪地叫着,太阳毒辣。从山下往总堂来的小路上,有一个年轻人正戴着草帽,个子不高,清清瘦瘦,步态稳健端正,往山上一步步走上来。
金圣帮三师徒正在午休,一声清亮的叫声把他们唤醒。
谷海山起身开门,嘴巴张大了,把来人让进屋里,同时唤了金石出来。
金石见了这人,呆了一下,说:“儿,你终于来了。”说罢声音哽咽。
来人正是金标,面容庄重,眼神平静清澈,虽然穿一身便衫,但是风采样貌跟以前却大不相同。
金石暗自欢喜,这个心里日夜思念的亲生骨肉到底还是来找自己这个父亲来了,看来,他终于回心转意,愿意回到自己身边,那和尚庙的日子他怎么过得习惯。心里喜悦无比,让徒弟给他端了茶水和午餐过来。
不料,金标脱掉了草帽,一个光光的脑袋剃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些极短的乌青的发茬,头顶上九个戒点香疤。
“儿,你这是?”金石声音颤抖地问。
金标跪下地来,说:“爸爸,我这两天向师父请了假,专门来看你。”
“好!怎么,你还要回去那和尚庙?”
金石说着就去扶他,可是金标却跪着不起,说:“我已经剃度为僧,持五戒。余生,就在少林寺度过了。我今天来,是想了结我们父子之间的这一世缘份。”
金石怒说:“既然这样,你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就当没我这个老子算了!”
金标突然清泪长流,说:“在寺里的这段日子,我终于觉察和悔悟到我以前是多么混账,多么自私,浑浑噩噩。你和娘生养我一场谈何容易,我却始终活在埋怨和责怪当中。”说着摇摇头,“只顾自己利益,不体谅父母艰辛,还贻害他人,导致别人重伤、丧命,佛祖肯收留我,已经是给我最大的宽恕。”
金石倍感慰藉,这个儿子终于通了人性,知道世道艰辛,说:“这些都不要再说了,已经过去了。你就此还俗,也让我感受一下儿孙绕膝的乐趣。”
金标摇了摇头,不语。
金石还存了万一的指望,说:“那个少林寺也不要再去了,要练功夫,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不用去做什么和尚。”
不料金标说:“爸爸,对不起!我今天来,是想再称呼你一声爸爸,感念你的生养之恩,表述我的亏欠之情。儿子以前欠你的,以后也不能给你养老送终,这些都只有等来世再报了。这个世道,我真的已经看破了,不想再贪恋。生生死死,富贵贫贱,又有什么区别?”
金石心如寒冰,说:“你今天来,就是说,我们父子今生缘尽。”
金标大放悲声,朝着父亲连连磕头,说:“儿子不肖,来世再报你的恩情。”
金石胸口发堵,说:“你去吧!我不要你假惺惺地说这些漂亮话。”
金标眼泪未干,起身戴了草帽,头也不回,出门就走。
谷海山和田安想挽留他,却被金石一声厉喝制止了。
田安拿了干粮和水,从后门偷偷出来,追上了金标,说:“你放心,师父就由我来给他养老送终。师娘,她去年年底就已经去世了。”
金标抹干了眼泪,说:“有劳你们了。潘二当家,不,度远师兄他在寺里修行很好,你们都不要再问。我走了,保重!”
田安叹了口气,返回到屋里,看到师父一动不动地坐在宽厚的圆大的椅子里,眼神空洞悲凉。
谷海山说:“师父,你不要悲伤,他即使不来这一回,你也没什么指望。他来了,而且他说的那些话,都证明他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糊里糊涂的小子了?”
“可是这有什么区别?”
谷海山说:“不一样,他之前就没叫过你一声老子,对你充满了怨恨,活在自己狭隘的阴影中。现在他走出来了,知道自己的过错,因而对你感恩又愧疚,但他心里又长出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也是他的新生,由不得他自己。”
金石似乎豁然开朗,说:“徒弟,你说得有些道理,人之一生,哪能全凭自己意愿生活?”
田安说:“师父,你应该为他的新生感到慰藉,而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他是你的儿子,他就得在你身边生活。”
金石哈哈一笑,说:“是这么回事啊,他终究是肯叫我一声爸爸了,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混小子。现在,心里有了更大的想法。这个问题,我们不再研究了。徒弟们,练功!”
看着徒弟们潜心投入,一招一势完全延续了自己的风格,金石忍不住说:“我们虽然是在深山练武修心,强身健体,但是师父怕你们枯燥无聊,一直想带你们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等你们再长进一些之后,去找雷雄,他一定会给你们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