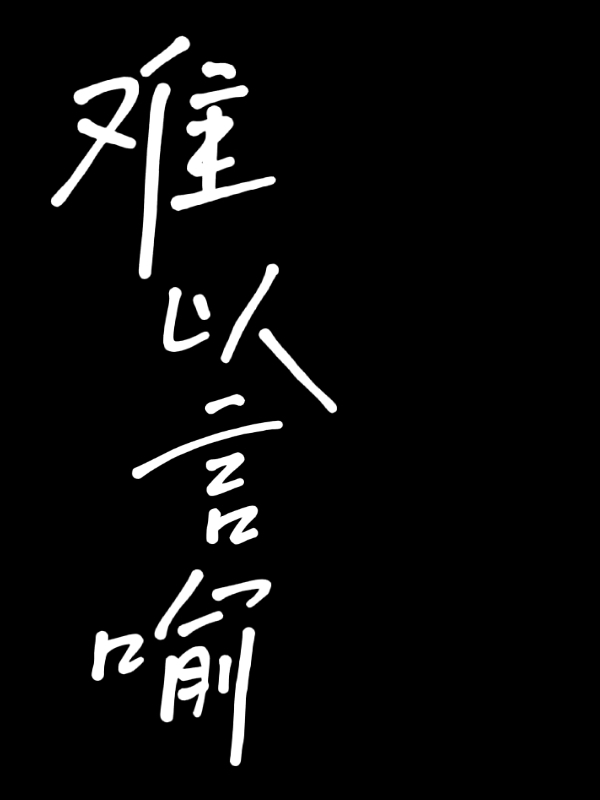因为元宵节闹得有些晚了,回到叶府已是戌时三刻,流云照例坐在二门耳房里与一个婆子说闲话等我,听到前院的妈妈通报我回了,便一路寻了过来。
“小姐回来了?今儿个灯会肯定很热闹吧?”流云见我神态开怀,也是跟着满脸喜色,边随口问着边将一个滚烫的暖炉塞到我的手中。虽然已是开了春,但还是见天的冷,晚上尤是寒凉刺骨,马车上的那手炉早已经凉了,如今这暖融融的感觉直流到心里。
我舒服地喟叹出声,“难为你了,这么热闹的日子,也不出去跟着她们转转,偏要在府里等我。”
流云无所谓地摇了摇头:“她们年纪小,正是爱玩的年纪,一年一回,也该出去乐一乐,再说小姐回来了要人服侍的。”
她们年纪小,流云也不过十六,却这般老成持重,我心疼地捏了捏她的手背,又问:“她们可回来了?”
“回来了,快活着呢。都是小姐体恤我们做下人的,求了夫人,给大家都放了假,大家伙儿出去玩的可开心了。”流云扶着我慢慢往回走。
这样就好,我也是特地与她们分开走,免得跟着我,还要受拘束,玩的不尽心,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开心就好。
入了凌菡苑的院子,流云直接将院门落了匙,又小心翼翼地左右看了看,“小姐,你走后,金妈妈送了东西过来。”
“金妈妈?什么东西?”我糊涂地皱了皱眉,金妈妈送东西过来,她有必要这么神神秘秘的吗?
“小姐进去看到就明白了。”说着她小巧精致的眉眼甜甜地漾开来,又想笑,又憋着似的。这下我更糊涂了,被她轻轻推着入了内室,猛一入内,便看到几上放了一盏栩栩如生的兔子灯,漂亮可爱的鼻子,嘴巴,一看便是刘老伯的手艺。
“呀,好漂亮啊。”我几乎惊喜地蹦了过去,欢天喜地地拿在手中,左摸摸,又瞅瞅,激动地对流云嚷着,“你别说,金妈妈怎么能找到刘老伯,做了这兔子灯的呀。”
流云却不答,噗嗤一声咯咯咯地笑了,我一愣,仿佛明白了什么,金妈妈怎么会知道刘老伯住哪儿呢,知道的该是墨誉啊,对,墨誉,那这灯是墨誉送的了,可是,不对呀,墨誉不在京中啊,难不成,他早些时候就备好了?
流云看我狐惑不解地抿唇不语,大概也明白了,忍不住打趣道:“是的,是小靖王殿下派人送到金妈妈那里的,也是有心了,听那小厮说,他们主子刚接到跟定远伯入西北的消息后,便紧赶慢赶地去了刘老伯的家乡做了这灯笼回来,说是可惜不能陪小姐过节了。”说到这,流云也止不住的款款笑意:“说起来,这小靖王殿下是真的待小姐极好,只是天意弄人,偏偏冒出来一个雅达小姐,还好小靖王殿下的心是在小姐这里的,小姐勿作担心了。”
是啊,有这样一个全心全意待我的人,这是何等的福气啊。哆嗦着抚了抚洁白的兔子耳朵,鼻子酸溜溜的,眼前已然雾气朦胧,他这么好,好到我都狠不下心了。
元宵节过后便是惊蛰了,春雷响,万物长,我朝向来是比较重视这个节气的,视作农耕开始的日子。所以,这日,宫里皇上照例是要祭祀的,以期待今年能够风调雨顺。皇后娘娘也让内务府为宫里的各个宫人,主子都准备了药草香包,春雷惊百虫,能够驱虫辟邪。这一日,向来是会在飞羽殿设宴庆贺的,我自然也是要参加的。
这种宴会最是沉闷,宴请的人大多是皇亲世家及家眷,所以周围皆是不熟悉的人,互相虚伪地说话假笑,别提多别扭了。我自顾自地坐在末座,时而低头吃上几口时而佯装认真地看着眼前的歌舞表演,两耳不闻周围事,只想着大家不要注意我,快点吃完,快点回去。
余光瞥到二皇子那桌,果真是春风得意,频频有高官站起,觥筹交错,络绎不绝,连带着怡贵妃那儿也是娇语盈盈,不时有嫔妃过去说话,好不热闹。想来也是,二皇子如今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也是今后太子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要知道,一来,二皇子与同为皇亲世家的安平侯府三小姐将联姻,二来,就是论靖王府的面子上,这些皇亲世家也会大力支持二皇子。这也就大大分薄了皇后和墨漓一方的势力。毕竟,从前,皇亲世家可是一边倒全都是皇后一方的追随者。
正远远带过一眼,我就感觉有一股子视线紧紧落在我身上,我警惕地回视过去,居然是那位雅达小姐。她正遥遥向我举杯,嘴里默念着什么,语笑带嫣然。
这种场合失礼总不合适,我狠狠吐出一口浊气,也是绽放出绚烂容姿,冲着她点头示意,干脆利落地饮尽杯中果酒,然后二话不说佯装被歌舞吸引了过去,开始凝神看起来。
不知前头皇后娘娘对皇上说了句什么,正扭捏作态的舞娘一个个停下了动作,安然有序地退下去了,转而迎上来的也是几位舞娘,只是,这穿着打扮就有些与众不同了,确切的说,他们一个个都是少数民族的装束,随着热情奔放的节奏打起一种双面鼓来,这倒有点看头了。我跟着其他人的目光一样津津乐道的欣赏起来,舞姿唯美中带着坚韧,又是大家伙儿从未看过的舞种,随着鼓声余音绕梁。
就在渐渐沉迷之时,突然,那鼓面发出一声巨响,还没来得及看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立在最前头的一位舞娘从鼓中摸出一把软剑,只见着她脚尖略一点地,整个人猛的朝着皇上的方向扑了过去。
事发突然,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也是这般,望着眼前这危急的一幕,仿佛自己被定住了一样,双拳紧握,只能任凭自己一动不动地盯着。
“啊,护驾护驾,快,护驾。”慌乱中,不知谁率先反应过来,疾声喊了出来。紧接着,大家才渐渐醒神过来,也跟着惊恐地喊了起来,大多都是东奔西跑,彻底乱了。
说时迟,那时快,眼见着那剑尖就要刺向皇上的脑门,原本立在皇后身前说话的墨漓,此时此刻,只有他离皇上最近,只瞧着他一个挺身,抄起桌上的酒壶朝着刺客狠狠砸了过去,刺客受痛,退后了几步,墨漓自然而然地就挡在了皇上的面前,与刺客打了起来,刺客手中有剑,墨漓却是赤手空拳,渐渐不敌,眼见着侍卫已经冲了进来,朝着刺客的方向蜂拥而至,那刺客竟然不要命地挽出一个剑花,直直朝墨漓胸膛刺过去。
我心中狠狠一抽,瞬间,冷汗层层浮上来,脚下软绵绵地朝着那个方向迈了几步,却只见一个黑影迅速飘过,生生挡在了墨誉的身前,是咏莲,这么快的速度,她,她居然会拳脚功夫,紧接着那把剑便直接插进了咏莲的胸膛,血光四射。我讶异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望着咏莲脆弱地一点点滑下,落入墨誉的怀里。我不得不感叹,这个女人为了墨誉真的连命都不要了。
最后,刺客在侍卫的包围中自尽了,我眼中只看得到墨誉抱着咏莲坐在地上面色狰狞,双目赤红。皇上下旨太医院一定要尽力救治咏莲,至于咏莲伤势如何,不得而知,只怕凶险。我望着眼前杯盘狼藉的场面,心情久久无法平复,一切真的好似就是一瞬间,一瞬间即是天翻地覆。
“皇上,出了这档子事,臣妾有罪。”突然,皇后娘娘跪倒在皇上脚下,神色憔悴骇怕。皇上肃穆宁静地扫了一眼底下的皇亲世家和我们,刹那间,大家纷纷匍匐在地,排山倒海的请罪声此起彼伏,我一愣神,也跟着跪了下来,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这场宴会由皇后筹备,舞女之中出现刺客,她责无旁贷,军中侍卫没有及时发现假扮舞女的刺客,他们也活罪难逃。
貌似听到皇上将皇后慢慢扶了起来,柔声安抚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刚刚多亏了墨漓,救驾有功,你这个母亲教子有方,也有功。”
“臣妾不敢,只要皇上安然,臣妾就知足了。”只听得皇后沉沉落下一口气。
“说来也惊险,皇宫守卫森严,这刺客好大的胆子,居然能混入舞女之中!”闻得皇后娘娘狐惑不解地呢喃出声。
“对了。”她似是骤然想起了什么,迫不及待地唤了一句,“雅达小姐。”
好巧不巧,雅达就跪在离我不远的斜前方,她身子猛然一哆嗦,声线略带僵硬,“在。”
“这支舞是你排的,人也是你找的,这舞女你可认得,平日里可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皇后正襟关切地问,语气很是柔婉,可这问题就很是尖锐了,皇后这是想将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推到雅达的身上了。
我本能地蹙眉抿唇,稍稍抬眼看看过去,她摆在身侧的双手死死攒着裙摆,还算镇静,“是雅达失职,请皇上皇后娘娘恕罪。这舞女雅达见过,正是排练时的舞女,这些舞女皆是从前宫中舞女中挑选而来,平日里,大家谨言慎行,除了练舞雅达与他们并无交集,是雅达愚笨,并未看出什么!”
这话虽然说的有理有据,条理清晰,但依照当今皇上的性格,恐怕心底总会留下猜疑。
“不是你的错,这些舞女从前倒真没看出什么,偏偏今儿个就莫名成了刺客了,看来是刺客太狡猾了。”皇后娘娘无声叹息,嘴上徐徐安抚,弦外之音却让人心惊。从前舞女都很好,到你手里就成了刺客了,你说这还能不是你的问题吗?
“这件事朕自有主张,都起来吧。”皇上不阴不阳地提了一句,看着好像并没有把皇后的话放在心上,可到底怎么想谁又知道呢。
我跟着大家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退到一边,尽量隐没在人群中。脑子里混混沌沌地思忖起来,皇后明显一直将矛头对准雅达小姐,她父亲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为什么皇后要公然得罪这位新贵呢,除非与争储之事有关。不过,怪只怪这位新贵是中途叛变投靠的我朝,皇上心里有些不信任也是人之常情,这也就是皇后能紧握在手的点。她堵的就是皇上的不信任。与争储之事有关,我这般想着,再次将目光移向了二皇子,脑中似乎有了答案,她忌惮的归根结底还是墨誉,墨誉与雅达联姻,阿尔琪将军便站到了二皇子阵营之中,她不想看到这种场面,她不能让阿尔琪雅达嫁给墨誉,是的。皇上没有弄清楚这件事之前绝不会再提婚事的。
回到叶府已是傍晚,我在母亲的碧霄院用的晚膳,父亲着身边的小厮回来报了信儿,并没有回来用晚膳。
“八公主是二十三的满月礼吧。”母亲正缝着手中的百家被,忽然想起来问我。
我点了点头,用银针挑了挑逐渐暗淡的灯芯,顿时一室生辉,但烛光闪烁不停,终究看的吃力,我急忙劝道:“母亲明儿个再缝吧,我瞧着也差不多了,仔细伤眼睛。”
母亲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唉声叹气着将物件儿递给红袖收起来:“宫里的孩子长大不容易,云妃千辛万苦生下来的,母亲想着这百家被能给她添些福气,无病无灾地好好长大。”
“八公主不会有事儿的,毕竟只是公主。”我拉住母亲的手塞我的手炉里面暖着,嘻嘻笑了起来。
“唉。”母亲冰凉的指尖爱怜地抚过我的面容,愁眉紧锁道,“今日这事儿实在凶险,如今,每次你入宫母亲总是心惊胆战的,尤其这段日子,听你父亲的口气,恐怕更加不太平。”
“母亲。”我撒娇似的钻到母亲的怀里,“无须担心,有了今日这事儿,墨誉和雅达小姐的婚事恐怕要拖些日子了,岂不是好事?”
母亲哭笑不得地点了点我的额头,“你呀,还有这心思,这几日,小靖王那里也没有什么消息,不知如何了!”
这恐怕才是最让人担心的了,其他宫里的是是非非于我们不过浮云,正嗟叹着,外面黄英通报父亲回来了。
我瞧了瞧外面黑沉沉的天,北风呼啸吹的窗棱咯咯响,不满地朝着父亲噘嘴,“父亲回来的也忒晚了,天又冷,可别冻着了。”
母亲无可奈何瞪了我一眼,手上仍旧麻利地给父亲脱下大氅,心疼道,“快到暖炉这里捂捂身子,怪冷的。”
我与父亲母亲撒娇惯了,父亲每次都会借此乐呵呵地调笑我几句,今儿个却是自始至终地板着脸,双目忧容,正襟危坐地兀自思索着什么。
“父亲,发生什么事了了吗?”我与母亲对视一眼,边疑惑地问出了口,边斟了一盏滚烫的清茶递过去。
父亲似乎这才醒过神来,接我的茶就要往嘴里送。
“小心烫,怎么了这是,魂不守舍的。”母亲嘴上数落着,也是急了。
父亲这才扫了我们两眼,轻声道,“皇上病了,所以今日我才回的晚了些,想着听信儿方便些,只是也不敢在宫中久呆,越是这个时候,越容易惹火上身。”
皇上病了倒不稀奇,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只是怎么听父亲的口吻,这是病的不轻啊,甚至有危险?否则父亲不会说不敢久留宫中啊,那是怕别人怀疑他参与在争储的队列中啊!
“怎么会?子衿今日还见着皇上了呀。”母亲倒吸一口冷气,不可置信地看我。
父亲神情凝重地,心事重重,“可不是嘛,就是宴席散了以后,听闻在回天禄殿路上就晕过去了,到我出宫都还未醒。”
“啊呀,这,看来很严重?”母亲颓然坐下,犹豫着打量父亲的神色,又自言自语地起身踱了几步,“如若真有个万一,这太子之位未立,那前朝后宫怕是又要有一场腥风血雨了。”母亲说到此处,猛的打了个哆嗦,慈瑞目光满是骇然与唏嘘。
我自然明白母亲的顾虑,她是想起了当今皇上与当初其他几位皇子争储时的往事,我们叶府大起大落不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嘛!再看到父亲浓眉刚正紧锁,不发一言,完全没有反驳母亲的意思,我的心瞬间就慌了,颤颤巍巍地笑着问父亲,“应该不会吧,皇上正值壮年,身子一向没有听说犯过什么病啊,怎么可能……”
“是啊,皇上一向身体康健,怎么可能出事,莫不是我们想多了吧。”母亲琢磨着睨向我俩,最后越说越肯定,几乎是信誓旦旦。
我立在父亲身边,焦躁地咽了咽口水,突然想起来,急忙问,“对了,父亲,太医怎么说?”
父亲却背手摇了摇头,嘴角苦闷地扯了一下,最后几乎是嘲笑起来,“不得而知,太医被要求守在天禄殿,就是守着的太监宫女也是只有最亲近的两个,除却皇后娘娘,其他妃嫔在外面哭了许久,连进都进不去,天禄殿此刻就是只蚊子也难飞进去,皇上的病情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居然一无所知!”我攒着裙摆的指尖因为用力过猛而愈加惨白,断断续续地呢喃这这句话。
父亲攒眉盯我一眼,继续道,“我思忖着,皇后娘娘这是有意封锁消息,所以我猜测,只怕不妙啊!”
的确,这太简单了,如若只是小毛小病,何惧人知晓,除非皇上的病危险至极,皇后娘娘怕朝局动荡,所以故意封锁消息。
“老爷,无论如何,我们叶府不能再陷入这漩涡之中了,老爷万万保重啊。”母亲一把抓住父亲的手,几乎带了哭腔说出这几句话。公公,也就是我的爷爷就是那时就是争储失败而亡。所以她怕啊,怕父亲在宫中有个三长两短的。
父亲安抚地拍了拍母亲的背脊,眼底一片坚韧。我知道父亲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我们除了等待,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