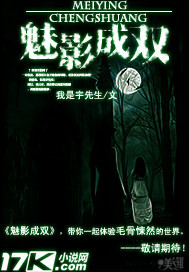纪挽月看着白寒烟看过来的一张小脸上,全是悲戚,栗瞳也是无法言喻的悲凉哀凄,他低低叹息,苦涩一直从舌根蔓延到唇角,他勾了勾唇道:“段长歌究竟哪里好,竟值得你这般托付?”
白寒烟从他身上收回目光,敛下所有了神色,低垂眉目淡淡的道:“纪大哥,你深夜来此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些吗?”
纪挽月瞧着她冷淡的神色,轻轻的笑了下,带了些自嘲的意味,叹了一口气,他似乎是想起什么她,急着道:“烟儿,我将常凤轩和绿绮收监了。”
也许,这件事会让她感兴趣,纪挽月想着。
“昨夜,面对刘胭的指证常凤轩说绿绮受了风寒,并不能刺杀刘胭和那仵作,我便叫大夫来替绿绮诊脉,可大夫得出的结果她确实是得了风寒。”
白寒烟闻言眉头只是微微皱了皱,平静的脸上再无任何波澜。纪挽月的眸子绞的一丝痛楚,须臾便隐下,又继续说着案情,好像他们之间除了爱情,再无可说,他并不想那样。
“只是绿绮这种小伎俩瞒得了大夫,却瞒不了我,在绿绮的颈肩穴上,我发现竟然刺了一根寸许长的银针,将足底少阳穴到头顶的经络全部堵塞住,而产生的瞬间寒热之症,用来以假乱真,那个叫做绿绮的女人心机深沉,决计不可小觑,只怕她的身份也未必是真。”
顿了顿,纪挽月见她神色没有波澜,又接着道:“刘胭的证词加上那仵作的指控,不怕常凤轩不承认罪行,如此更是一鼓作气将常府隐藏的秘密全部挖出来。”
白寒烟目光定在一处,却空寂荒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就好像一潭死水,再泛不起一丝一毫的波澜,良久,她回过神来道:“纪大哥,这些事你不要和我说了,……我并不感兴趣。”
纪挽月着实被她这种死寂的神色惹怒了,两步蹿到她面前,抬手捏住她的肩头,咬牙道:“白寒烟,你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离了段长歌你就活不了了,你知不知道段长歌杀了江无极,这可是死罪!”
白寒烟猛然挣脱他的束缚,眸如寒雪睨着纪挽月道:“他是为了我才动手的!江无极要将我抓进诏狱,长歌是为了保护我,这世上再没有像他一样,为了我可以不惜性命!”
纪挽月身子一顿,喃喃道:“烟儿,我也能……”
白寒烟美目迷离,泪眼朦胧,哭泣着向后退了两步:“纪大哥,可我爱的人是他。”
纪挽月心口剧烈的绞痛,他猛然上前拉着她的手臂就往怀里带,白寒烟拼命的挥舞着手臂挣扎,纪挽月死活不肯松手,他束缚住她,呼吸沉沉的喷在她的颈间:“烟儿,你不明白,这京城中风云诡谲,你……一直都是别人的眼中钉!”
白寒烟一怔,在他怀里僵直的身子,不再挣扎缓缓抬头看他,眼中绞着不可置信:“纪大哥,你说什么?”
纪挽月轻轻叹气,忽然抬头问道:“烟儿,你知道皇上为何忽然要杀你吗?”
白寒烟眼神呆滞的摇了摇头,昨夜她欲想问,可段长歌却三言两语的带过,并没有多说一句,她心里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白寒烟艰难嗫嚅着唇道:“为什么,之前在御书房他分明答应过我……”
纪挽月凝视她,低叹一声道:“那是你不明白这世间的人心险恶,你父亲白镜悬贪污赋税一案,本就是这大明朝的一块逆鳞,满朝上下何人敢提,赋税是国之根本,万民供奉,皇上最初提及,也不过是想找到那千万两的赋税银子,如此既可以给百姓一个交代,又在史册上划去他此番污名,可现下,整个时局都变了,有人为了那得到笔钱,有人想趁机祸乱朝纲,京城之下暗流漩涡,一时皆起,烟儿,你知道为何皇上让我在此时去查常德吗?”
白寒烟被他的话激震住,禁不住发抖,粉唇抖了两下,只能任由他捏着自己的肩头,听纪挽月这一问,她不敢想其中深浅,只能摇头。
纪挽月黑眸里淹了一滩浓墨,绞着像天边黑云一般汹涌的戾气:“因为圣上认为常德有不臣之心,私通外族,更是以你父亲白镜悬留下的银子为饵,挑起京城之内一些贪心之人的贪婪,比如王昕,从而来动摇江山,而这笔赋税银子一旦被人找到,那就是意味着是陛下的无能!他竟然有眼无珠的宠信了一个奸臣数年,这赋税的贪污是由皇帝一手纵容的,恐那时,圣上便无法向万明交代。”
“可我父亲是无辜的!”白含烟忍不住哭着向他喊道。
“你觉得一个冤枉忠良和宠信奸臣对于帝王的名声来,说有区别吗?”纪挽月幽幽的开口,他在皇上身边伴君数十年,最能揣测他的心思,从将圣上调去常府密查,又将江无极密诏入宫,下了这一道旨意,他就知道皇上的杀心已起。
“你还活在这世上,就意味着白镜悬一案始终存在,而这些心怀不轨的人,就会一直蠢蠢欲动。只有你死了,这件事才会平息。”纪挽月眼中蒙上阴鸷,只觉得心里难受的紧,帝王无情,杀伐果断,这一旨下去,白寒烟必须死。
白寒烟身子一软,缓缓的从他怀里跌落在地上,好像跌落了万丈深渊,浮尘入海,再无生机,她噙着泪,无迷茫与恐慌交织成最大的梦魇,忽然,白寒烟似乎想到什么,瞳孔猛的一缩,忽然伸手抓住纪挽月的手臂,不住的乞求道:“纪大哥,我求你,带我入宫,让我见圣上,我甘愿赴死,甘愿赴死!”
白寒烟泪流满面抓着纪挽月的手臂,犹如在浮海中的一根救命稻草,纪挽月闭着眼睛,只觉得心中似酸似苦,那点苦浸入内脏来,那样复杂的滋味他不想深尝,一把推开白寒烟的手,痛苦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段长歌,你现在就算是死,也不可能了,段长歌此番若想护住你的命,只有起兵造反,可如此一来生灵涂炭,才是大明朝眼前最大的一番祸乱,他是想以此要挟圣上,更是隐晦的告诉陛下,谁才是他现下最大的隐患!”
纪挽月话好似一个晴天霹雳在她的头顶响起,她只觉眼前一片空白,眼前一黑,直直地向后倒了过去,她又听见纪挽月接着道:“你以为我是如何知晓你的藏身之处?以段长歌心思缜密的程度,必将派出暗卫将此山团团围住,而护你周全,岂会让我如此轻易的闯了进来?”
白寒烟只觉得心头的血涌在一处,崩塌了心里唯一的那根玄:“是,是他告诉你的。”
“不错!今夜他这一去便是用自己的命来换你的命,他手有重兵皇帝必定忌惮,陛下不得不答应他放过你,段长歌无野心,更不忍生灵涂炭,目的达到自然向圣上俯首,可皇帝又岂会容他,今夜他段长歌绝无生路!”纪挽月一席话又在白寒烟心头捅了一把刀子,痛得她伏在地上,弓起腰嚎啕大哭,泪水倾肆如涌,纪挽月满面痛楚的抬手拽起她,又握紧她的肩头,道:“我之所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便是想让你对他死心,你和段长歌今生再无半分缘分可言!”
“不,不,我不让他死,我不让她死……”白寒烟抬起一双泪眼,低低的喃着,忽然她像疯了一样,一口咬在纪挽月的胳膊上,猝不及防,他略一吃痛,微松下手,白寒烟登时挑了一个空子,一把抽出他腰间的虎头刀,便向脖子抹去,这一刀她用全力,刀刃深深的割入皮肉,当即划破了她的咽喉,汩汩的血迹登时洇了出来,可她最终还是没有死成,纪挽月猛然抬掌握住了刀锋,硬是以血肉阻了她的刀势,两个人的血流在刀片之上,溶在了一处。
“纪挽月,我若是想死,你以为你能挡得住我!”白寒烟两只眼寒气慑人,冷冷的瞪着他,纪挽月淡然的看着她,平静道:“当然,我说过我会护你周全。”
白寒烟闻言轻笑一声,脸上全是讥讽,道:“你口中的周全,便是将我囚禁起来吧。”
纪挽月胸膛剧烈起伏,一把扯出她手中的刀,随手扔在地上,砰的一声,绝了她的死路,他疾步上前伸手捂住白寒烟脖子上的伤口,怒气从丹田冲了上来,咬牙道:“可最起码,我能护住你的命!”
“命?”白寒烟似乎嗤笑一声,低眉缓缓看着手腕上那淡绿莹润的玉镯,任由眼中的泪水裹挟着脖子上嫣红的血一起浸湿了她的衣襟:“没了他,这条命我要它做什么?”
纪挽月浑身一僵,黑眸射出悲痛,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看着她,鹰眸里有几丝晕红,衬着微红的眼圈,眼底流出莫名的哀伤:“烟儿,忘了他吧。”
说罢,他一抬手以掌做刀,敲在她脖颈之上,白寒烟意识渐渐涣散,在她倒下去之前,她知道,这一生,再也难了。
纪挽月将白寒烟缓缓倒下去的身子抱在怀里,抬起手一点一点的拭去她脸上的泪痕,眼中全是痛楚,他俯身在她耳旁轻声道:“烟儿,为了你,我纪挽月也可以舍出这条命来,可到底,你心中终究是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