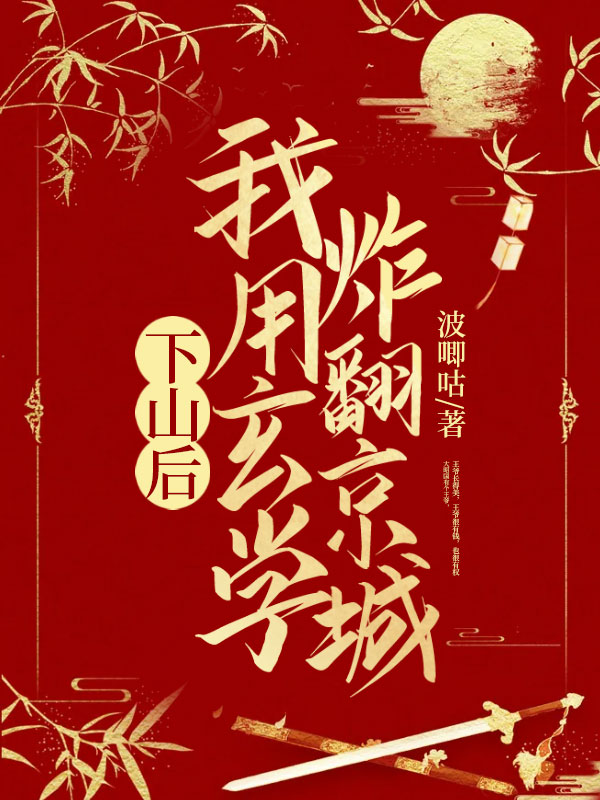白寒烟不由得神色一顿,因段长歌的话而皱眉,两日之内吗?
她不着痕迹的瞥了一眼软榻上男人,原来段长歌竟然将一切都计划好了。
坐在一旁的纪挽月也抬眼扫了一眼白寒烟,一抹沉色暗藏于深瞳中,薄唇成线:“常府里危险至极,这么危险的事,你竟然让她一人孤身去做,段长歌你究竟安了什么心思?”
白寒烟更是因他的话心口漏跳一拍,纪挽月的话无疑是已经知晓她此刻的身份了,她低叹一声,不由得将头埋得更低。
段长歌眼梢一扬,语气阴沉:“不让她去,那你去寻。”
纪挽月登时站起身,砰的一声,他抬掌击在桌子上,起身就往外走。
段长歌睨着他的背影嗤笑一声,行至门口,纪挽月却忽然顿了顿,偏头看着段长歌身下的那一方软榻,又略过一旁低头的白寒烟,声音极其阴寒:“段长歌,有些事你最好别做的太过分!”
段长歌扯唇轻笑,又看了一眼白寒烟,潋滟的凤目闪过一丝笑意,温软异常,并不理会纪挽月。
纪挽月一甩袖子推门而走,待他的身影尽消。白寒烟凑到段长歌身旁,好奇的拧眉:“什么过分的事让他这么这么生气?”
二更天,无月,伸手不见五指,树影随风摇晃,远看着竟如恶鬼一样狰狞。
白寒烟隐在廊下阴暗处,一瞬不瞬的盯着常凤轩的房间,喜庆的窗纸红烛还未褪去,无处不彰显着他方新婚的喜气,白寒烟心里满是不屑,花心的男人又会得到几分真情
二更时分刚过,常凤轩屋内的红烛瞬间熄灭,白寒烟双眸收缩,紧紧的盯着那紧闭的屋门,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一阵细微的颤动,门被悄然开出一条缝隙,一个人影在房门前一闪,便不见了踪影。
白寒烟冷哼了一声,看来段长歌料想的不错,常凤轩他果然是按耐不住了。
夜色里,万籁俱寂。只余风声凄厉,没命的摇晃着树梢,在黑暗里仿佛是张牙舞爪的影子。
白寒烟悄无声息的跟在那人影之后,今夜天上无月,她瞧着的不处的那团黑影,穿过几道街角,一闪身便钻进一条偏僻的小巷里。
白寒烟侧身贴在巷口,,探身瞧去只见巷子里有几户人家门檐上挂着几盏红灯笼,昏暗的灯光有些血红,让人头晕目眩,却映出巷子里如鬼魅穿行的一团黑色的影子。
常凤轩穿着夜行衣,在巷子最深处,有一间破败的老旧的作坊门口停下,他四处张望了几眼,身影一闪便不见了。
白寒烟疾步走到那作坊门口,借着血红的灯笼仔细看去,那作坊原是用青石砌成的几间石屋,只是房顶的瓦片破碎的不成样子,东西两边的厢房是普通的稻草土屋,窗户和门在秋风中被吹得摇摇欲坠呼呼作响,院子里都布满了寸高的的杂草,看来,此处应是经久未有人来过,只是,常凤轩深夜来此想要做什么?
白寒烟星眸幽深,当下纵身一跃,轻巧的落在那坊院之内,轻手轻脚的两步跨到一处正房门口,此刻,原本漆黑一团的破屋里竟隐隐的亮起了昏暗的光。
白寒烟急忙将身子隐在窗侧,眼角瞥去,但见那窗上投出两个人的影子来,白寒烟皱眉惊疑,警觉的望着窗上的影子,屋内另一个人会是谁?
正惊异间,屋内传来声音让白寒烟柳眉微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只是她似乎对这声音有些印象,只是一时竟想不起来在何处听过。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那男人似乎对常凤轩此时的出现而不满,语气充满怨愤:“都是因为你,现下不仅锦衣卫,还有不知道哪儿来的暗卫都在四下寻我,我像个过街老鼠一样,四处逃窜,你竟然还敢来找我,就不怕泄露了我的行踪?若是我被人抓到,我可是叫你们父子一起陪葬!”
白寒烟猛然收紧手掌,怪不得这个男的声音会让她感到有些熟悉,竟然是辛桃死的那日,刘景唤来验尸的仵作!
看来他的确是被常凤轩给收买了,验尸时说的全是假话!
白寒烟心里冷笑一声,一丘之貉,竟然内斗起来,而此刻,屋内竟陷入一片寂静,白寒烟看见常凤轩的影子站在窗子附近,背对的那个仵作却始终未言一语。
“你到底想怎么样!”那仵作见他不语,似乎有些动怒。
常凤轩露在蒙面巾外的面色如纸,眉宇间寒光一振,忽然现身从袖中翻出一柄柳刀,寒光一闪,对着那仵作的咽喉切了上去!
那仵作登时脸色一变,悚然一惊,却似乎早就有准备,身子向后一滚,利落的便退到了墙角。
白寒烟面色悚动,看来常凤轩竟然想要杀人灭口了,紧接着她不禁瞪大了双眼,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屋内竟然出现了第3个人影,瞧着窗上那窈窕的身形,竟是个女子!
那女子站在那仵作身旁,盯着握着湛湛寒刀的常凤轩,冷笑出声,似乎对那仵作不屑的嗤笑:“我说过,他一定会来杀你灭口的。”
白寒烟不由得深看那女子的影子一眼,她的确没想到,这个忽然出现的人竟然是刘胭!
“你现在可看清楚了,你若是随我去段大人那里首告,兴许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否则以我对常凤轩的了解,他是不会放过你的。”刘胭偏头看着那仵作,目光寒冷,冷声道。
那仵作瞧着常凤轩手中的刀,恨得咬牙切齿:“真没想到,你竟这般狠毒,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
他的话音一落,常凤轩面无表情,屋内又是一片沉寂。
刘胭盯着眼前蒙面的男人有些惊疑,他二人如此咄咄逼人,常凤轩为何不肯言语,屋外的白寒嫣也觉得有些奇怪,今夜的常风轩怎么会有些反常。
刘胭微眯起的双眸从眼前蒙面的常凤轩的眼滑向他的手指,忽然她惊骇的睁圆了双眼,惊呼道:“你不是常凤轩,你究竟是何人?”
白寒烟也是一惊,那人竟然不是常凤轩!
那会是谁?
只听那人忽然抬头阴恻恻的笑了一声,狠戾的双眸中有暗沉的血丝浮出,那人冷笑着:“真不愧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竟然这么快就被你给瞧出端倪来了。”
常府客房内,一灯如豆,映在窗纸上,摇动竹影森森,窗外树叶相撞的淅淅沥沥,更觉夜寒侵骨。
一身绯衣的段长歌执了白玉杯,懒懒靠坐在外厅的椅子上,微仰头,俊美的脸庞披了层暗黄的银辉,显得面色尤为冷淡,而手边桌旁也落着一盏白玉杯,不知会是谁的。
大约过了半刻钟,秋夜的寒凉使段长歌有些身子微凉,他眼角一挑,睨了一眼甘醇的酒水,不动声色的勾了勾唇,轻笑道:“秋叶太过寒冷清冽,不喝酒暖身,真是浪费了。”
段长歌的话浅淡绕耳,消散在房内,悄无声息。
没一会儿,一双白底蓝面的毡靴率先从屏风后面漏了出来,然后,一张俊逸的脸隐在烛光的暗影里,显得那人竟有几分阴森诡谲。
“几月未见,你还是那么喜欢藏在屏风后面。”段长歌眼皮未抬,慢悠悠的喝着酒,似乎是随意的道。
“几个月未见,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乔初缓缓的从屏风后走向他,一撩衣袍坐在段长歌身旁的椅子上,瞥了一眼白玉杯中的酒水,缓缓抬手执杯淡淡的啜饮一口后,接着又道:“自以为可以看透人心。”
段长歌闻言低低的笑起来,满面春风,抬手放下茶杯,黑瞳流转如冷淡的满月荧光:“你就不怕,我在那酒水里下毒,此刻就要了你的命……”
乔初闻言也笑了起来,唇角微勾出一抹嘲笑的弧度,讥唇道:“你以为我乔初就这般无用么,段长歌你也未免小瞧了我。”
段长歌挑了挑眉,似乎对他的话特别赞同,旋即自顾的又仰头满饮了一杯,才轻笑道:“所以你才诈死躲在暗中操纵这一切,你想隐瞒的人是谁?”
”我知道瞒不过你,能瞒的过她就行了。毕竟我若不死,白寒烟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此事若是闹大可就不好办了,毕竟我现在还不能这么快就暴露在别人眼下。”乔初淡淡的道。
段长歌低笑一声,并没有言语。
乔初偏头看着他,忽然冷声道:“你既然知道常德灵堂里藏着那个人就是我,为什么不告诉她?”
段长歌邪肆嗤笑一声,语气全是不屑:“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得了你,何必又要扯上她来参合。”
乔初听了他的话,倒是笑得很是开心,眉眼微弯道:“看来,我当初把她安排到你身边,这一步棋局算是下对了,你当真是爱极了她,你可要小心,别把这条命丢了。”
“这倒不需要你操心。”段长歌笑的温柔,满眼柔情:“我还是要多谢你,将她送到我身旁。“
“说吧,你将白寒烟支走,是想从我这知道些什么?”乔初一摆手,似乎是耐心被磨尽了,伸手落下白玉杯,一脸不耐的问着。
段长歌转眸盯着他,眸底陡然生寒,凌厉得仿若蕴了冬日冰寒,全无方才的温文贵气,开门见山的道:“乔初,我只问你一句,白静悬一案背后的主使……可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