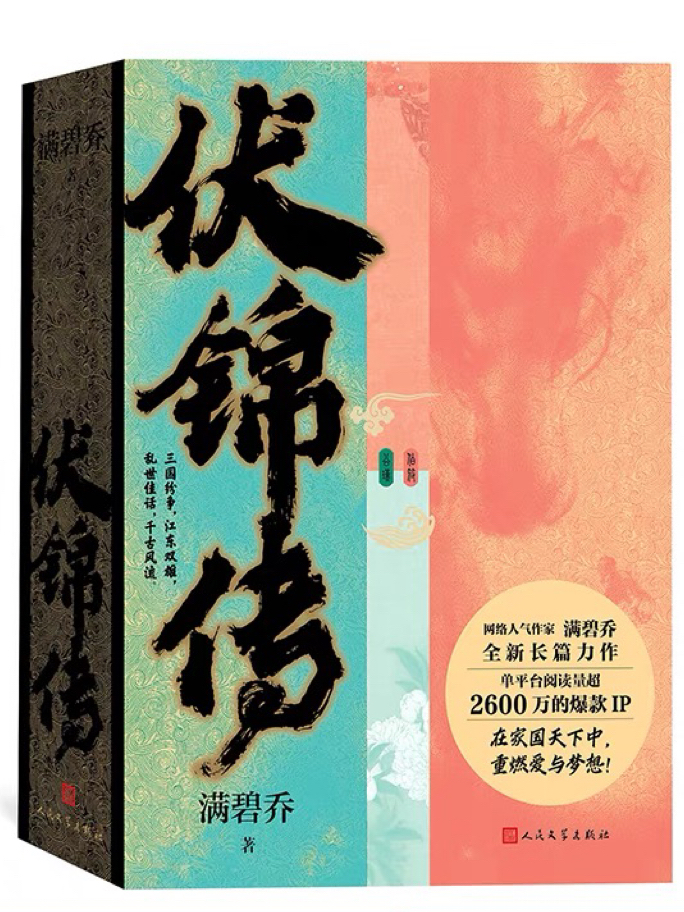自有孕后,一日里十二个时辰,我近乎八九个时辰都在犯晕犯困,总是睡着的时候比醒着的时候多,往往是长极上朝我在睡,他下了朝,我仍旧在睡。孕妇虽多眠,却也不似我这般嗜睡成疾。
太医署的人频繁来清乐宫问诊,没少给我针灸灌药。可气的是每次问他们我究竟什么病,他们都支支吾吾不肯告知,只将病因说给长极听。
长极素来拿我当孩子看待,总捡着好话哄我开心,又怎会将实情告知我呢。我思量再三,想着他既然不说,定然有不说的道理,索性不去追问,安心养病便是。
我以为只是寻常小病,但我大概是低估了自己的病情。
有次我在夜里醒来,迷迷糊糊间感觉到脸上湿漉漉的,一睁眼,竟看到长极正泪眼朦胧的注视着我。伸手一摸,才惊觉脸上湿漉漉的东西原是他的泪水。他看我的眼神是那么哀痛,仿佛一只受了伤的狸奴。我吓了一跳,哑声询问他怎么了,他摇头不语,俯身将我抱得紧紧的。从那以后我便知道,我的病,不容乐观。
怀孕到五个月时,我开始出现厌食气虚的症状,时而还会突然咯血晕厥。若说从前我只是虚弱,如今竟是形如枯槁,真正的缠绵病榻。我因体弱,一度险些小产,幸得众御医竭力挽救,才勉强保留住。
我开始害怕,怕自己挺不下去,怕保不住肚子里的孩子,怕将长极孤孤单单的留在这世上。他那么辛苦的找到我,我们就只有这一世可活,他说他鳏寡孤独了几世,不想再经离别苦,若是我和孩子都走了,那他该怎么办。
长极因为我的病三天两头罢朝,惹得朝中大臣颇为不满,纷纷进谏说勿要误了国事。
我也极力劝他莫耽搁政务,我自有安平娘娘看顾,教他安心临朝。他不应允,仍旧衣不解带的守在我病榻,事事亲力亲为,后来更是直接不上朝,整日整夜的守着我。
群臣被逼急,日日跪在养心殿前请命,他气狠了,当着我的面痛斥了几个老臣,不仅罢了几人的官职,甚至还要仗杀为首的中书令孙贤。我急忙将他劝下,保住了这位忠良之士。
长极非是正统,即位本就勉强,朝中党派林立,旧臣又多是不服他的,难得有这些个忠心为国的臣工,万不能因为我而寒了人心。
在我病稍好后,长极终于亲务,但仍为了看顾我隔三差五的辍朝。我百般规劝无效,只得由着他去。
又一次久眠醒来,睁眼看到的是长极一双红肿不堪的眼睛。他满脸哀切看着我,大颗大颗的眼泪打在我脸上,灼热滚烫,犹如红烛滴泪。
我都记不得这是他第几次哭了,好像每次醒来见他,他的眼睛都是肿的。
我十二岁来南瞻,彼此相伴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他这样爱哭。
我抬手抚上他的脸庞,努力咧嘴挤出来一个笑容,我说:“长极,我又做梦了。”
他拍着我的背,笑着问道:“有梦到我吗?”
我摇了摇头,说梦见的都是故人,并没有梦见他。他有些失落,捧着我的脸说道:“你是太思念他们才会夜有所梦,那你不想我吗?”??我靠在他身上,枕着他有力的臂膀,故意说着反话:“一点都不想。我日日见你,早就看烦了,有什么好想的。”
他默了片刻才笑道:“这么快就烦了?那往后这几十年,可怎么过哟。”
我暗暗念了一遍“几十年”三个字,心底没来由泛起一阵酸楚。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活几十年。
夜风吹得帘栊微微晃动,室内忽而寂静下来,烛芯发出滋滋的声音,烛焰随风轻轻摇曳。我睨着眼前的吐烟香尊发起了呆,忽而心血来潮念了一句口渴,想吃葡萄了。长极一听犯起了愁,眉头紧皱。要知道这个时节南瞻是没有葡萄的,除了千里外的北邱。
可北邱那样远,这葡萄又这般易坏,要送到南瞻谈何容易。
这要求着实是为难人,但长极还是应承下来。
他宠溺的捏着我的鼻子,喃喃低语道:“给我些时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找来。”
我噗嗤笑出了声,只当他又在哄我,却也顺着他的意说好。我本是一句笑谈,谁知一月后的某日,他果然为我寻来了葡萄,大大小小几十箩箕摆满盝顶。
我心里疑惑,这样的时令,他是去哪里找来这么多新鲜葡萄。问后才知,他一年前便派人去了北邱,专门去寻不按节气培植的葡萄。趁果子将熟未熟之际,快马加鞭送回建康。
这样艰难的运送过程,不知要苦了多少人。我含泪吃着金罍里的葡萄,心中五味杂陈,亦十分自责。
当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魇在梦里总也醒不过来。我胸闷得厉害,头也痛得快裂开,迷迷糊糊间听见有人在不停的呼唤我,仔细辨认才听出来是长极。?好不容易挣扎着醒来,想开口说话,但好像有烙铁堵在了喉间,咽痛得紧。双手死死的抓着罗衾,头上的汗如雨似的落下来。
长极搂着我坐起,喂我喝下一盏温水,又连忙宣来御医。一番折腾至天明,才算是退了烧。
这一夜后,我病得更严重了。太医署的人来得更勤,我喝的药也越来越多,身体却每况愈下。如此这般熬着,我俨然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
宫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的术士、沙弥、道人,每日里不是在做法事,就是占卜、炼丹,将清乐宫弄得烟雾缭绕,香烛味堪比大相国寺的祈福坛。他们同太医署的人各持己见,争吵不休,可对我的病又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烦得不行,看见他们就头疼、但我知道这是长极为了给我治病,从列国重金聘募来的能人异士,我就是再烦也极力忍着,只在私下里把他们进献的丹药偷偷埋进花盆中。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月我的病情仍旧没有起色,身体越发孱弱,直至后来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长极一怒之下,想将这一百余人直接诛杀,但思及孩子不可杀生,转而将其全都下了狱。
眼看产期将近,孟节自百越被召回建康,以医正的身份进了宫。
若说这世上还有谁可能医治我,恐怕也只有在孟节这里还能看到一点希望。
孟节是在暝昏时分来的清乐宫,彼时,我刚昏睡醒来,愣怔间听到他和长极在屏风后说话。他们的声音时远时近,压得很低,我什么也听不清。
“长极……”
我勉力轻唤,屏风后的人闻声赶来。
长极握着我的手柔声询问我饿否冷否,可还难受,我一一摇头,侧目睇向金屏风。他会意,稍作迟疑后,还是命人撤去。
我抬眼,正好与孟节四目相对。
他的眼睛看着我,又仿佛没在看我,目光清冷,在我脸上停留短短一瞬后便收回。他低垂着眼帘,步履从容的走上前来,庄重缓慢的屈膝低头,对我行以臣子大礼。
“微臣,拜见皇后殿下。”
不知为何,听他这样称呼我,我会那样难过。心中怅然若失,好像打失了什么东西。
我久久没有应语,由着长极开口免去他的叩拜。他退到一侧,不紧不慢的陈述着他为我制拟的调理良策。我漫不经心的听着,不回应,只一味的盯着他看。
我与他,算来已有三四年未见。他还是那样飘逸出尘,俊朗耀眼。反观于我,病容憔悴,不忍细看。
我毫无顾忌的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他像没有察觉到我的目光,始终埋头在胸,直至请退出门,他都不肯再看我。
我目送孟节的背影远去,尚在黯然感叹与他竟生分至此,便听长极沉着声酸酸说道:“差不多得了,人都走远了还看。他还能有我好看?”
我白他一眼,侧过身没理他。
他不满的哼了一声,随后俯首帖着我的脸,在我额角落下一吻,又抚着我高高耸起的肚子问道:“今日他可安分些?”
我道:“睡着的时候,这孩子一点都不乖,狠狠踢了我一脚,将我给踢醒了。”
长极朗声笑道:“皇儿定然是嫌弃他的娘亲太贪睡了,想将她踢醒,好让她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呢。”
这次换我不满的哼了一声,我噘着嘴佯装生气道:“我看是他爹爹嫌弃了才对。嫌他孩儿的娘懒惰,不思进取,贪吃贪睡。”
他被我的话逗笑,捏着我算不得丰腴的腰身道:“我哪里敢嫌弃,我都恨不得将你捧在手心,揣进怀里,时时刻刻带在身边才好!倒是有些人,一点不在意我,当着我的面窥视其他的男子。”
我翻身环抱住他的腰,哭笑不得道:“陛下是吃醋了吗?”
“当然吃醋,我都吃了好多年的醋了!”
我愣了愣,没想到他会这样说。
他的手扶着我的后背,让我靠着软枕坐起来。顿了顿,他继续说道:“他对你的心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遑论是我。若不是他还有点医术,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他再见你。”
我听着他这般孩子气的话,实在忍俊不禁,讪笑说道:“且不说我向来非殊色,除了你没人会稀罕我,何况我如今还是一个病恹恹的孕妇。我这张脸又肿又丑,人家对我能有什么心思?你也忒小气了些。”
他眼神忽而一黯,右手抚上我的脸颊,柔声说道:“一点都不丑。在我眼中,缺缺是这世间最美最好的女子。”
我听出他语气里的爱怜,也知道他断然不会嫌弃我的病容,不过是担心我会多做乱想,才特意说这些话来宽慰我罢了。
我俯首枕在他膝上,他的大手有一下没一下的拍着我的后背,似在哄我入睡,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我早已熟悉。
我惬然道:“拍背的有了,就差一个捶腿的了。等孩子长到两岁,应该就可以使唤了吧。”
长极的笑声自头顶传来:“这孩子真是不容易啊,这么小就得被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