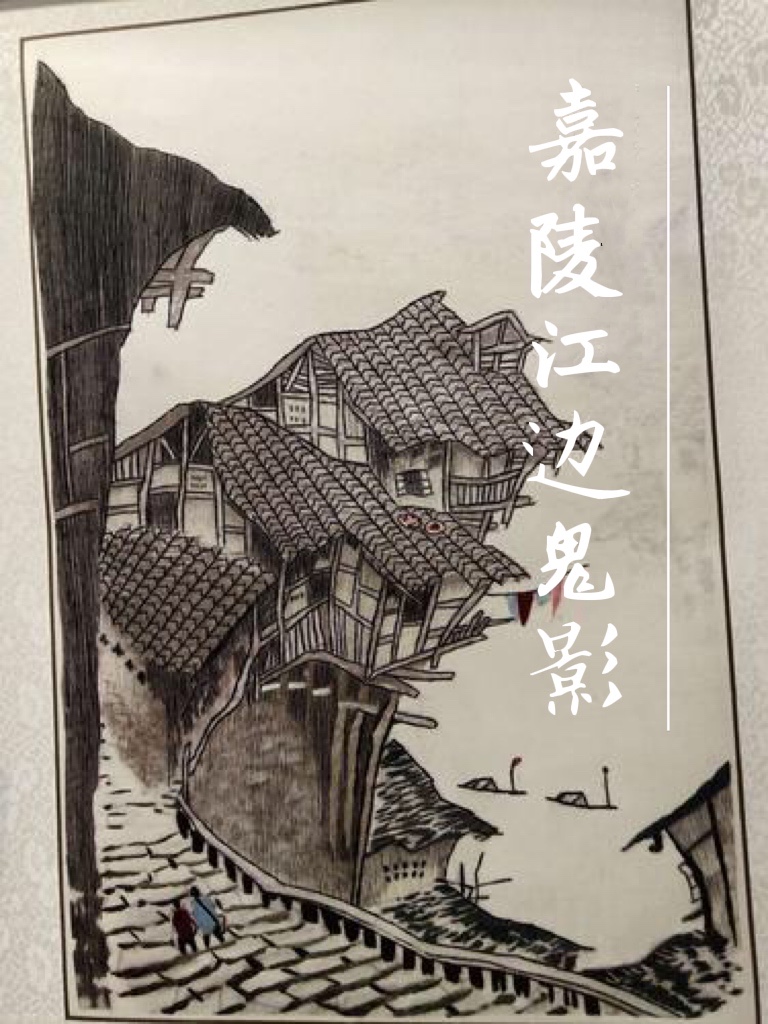长极身后自有数百精兵跟随,但他冲在最前,杀得最猛。
“拦住他!!”
冬嘉一壁厉声吩咐台下的死侍将长极困住,一壁催促稍歇的巫师继续祈神。
但为时已晚。
随着长极掷出一支长矛击毙了那为首的僧人,一切都戛然而止。
又一阵大风呼啸而过,所有幻影顷刻都失了颜色,只剩一片鸦青,叫残风一卷,尽数散去。
“不!不要——”
眼看着日晷上的光影将散,冬嘉已然疯癫,哭喊着奔向日晷,双手不停摸索晷面,妄图留住那最后一抹流光幻影。
白光散去,拖住我的那股风力也顷刻退涣,身体迅速的往下坠。
就在我即将砸向地面的那一刻,一双有力的手将我牢牢拖住,然后圈揽入怀。
“长极,你怎么才来啊——”
我死死抱住他的腰,将头埋进他的怀里嘶声恸哭,势必要将积压两年的思念和这几日受的委屈都倾泻出来。
“我好怕,我真的好怕!”
头顶传来他沙哑低沉的声音,仔细分辨还有一丝哭腔,“不怕,我来了,我来带你回家。缺缺不怕,我回来了。”
“长极,长极,”
“我在,我在的。”
我反复念着他的名字,埋首贪婪的吸着这久违且熟悉的气息。环住他腰际的双手久久不肯松去,我生怕一松手,他又不见了。
“不怕,没事了,没事了。”
他的掌心缓而轻的拍着我的背脊,下巴杵在我的头顶,低声呢喃宽慰,一句一句,不厌其烦。
我抽噎道:“长极,贺格死了,于归死了,我的月食也死了,我也差点就死了……”
这些名字提一遍心痛一遍。
“对不起缺缺,是我不好,是我没保护好你,我应该再快些回来的。”
我听见他哽咽的自责,遂竭力止住哭泣,缓缓抬头看他。
他眼底青黑一片,眼眶红肿湿润,下巴上的胡须未曾剃去,鬓角还有凌乱的碎发垂下,原本美若冠玉的脸,此刻血迹斑斑,极显疲态。
他从前那样清雅,何曾像今天这样邋遢过。
我心下一疼,眼泪再次大颗大颗的往下掉,小心翼翼的去擦拭他脸上的血迹。
他握住我的手,吻了吻我的指尖,又吻了吻我的额头,然后回我一个温柔的笑,:“别担心,这血不是我的。我答应过你,不留疤,不流血的回来。你看,我说到做到,不伤不残,你还要我对吧。”
闻言,我哭的一塌糊涂。
边哭边闹:“你这个骗子,你明明说过杏花开的时候就回来的!还让我等了那么久。”
“是我不好,我不该骗你的。以后我再不食言,再不骗你了。”
“长极,我们回家,我想回家。”
他用手指将我脸颊的泪珠悉数抹去,珍而重之地吻了吻我的眉眼,柔声道:“好,我们回家。”
话落,他解下他的素色罗袍为我罩上,又将我揽在背上,背着我起身欲往台下走去。
还未行几步,平端一把长剑又横在我们面前。
冬嘉鹰瞵鹗视,目光凶狠到了极点,紧盯着长极,一字一句凌厉道:“把她留下!”
似命令,又似警告,握剑的手臂青筋暴起,指尖在微微颤抖,不知是怒还是怕。
“让开!”
长极冷漠的直视着她,语气极不耐烦。
“我说了,把她留下。你难道连我的话也不听了吗?”
冬嘉震怒,手中的剑又往前递进一分,直逼长极咽喉。
长极无惧,提步继续向前,我却被吓得不行,圈住他脖子的手不由一紧。
他侧过头,低声安慰我道:“不怕,没事的。”
“嗯,我不怕。”
只要有他在,我又有什么好怕的。
我将脸贴紧他的后颈,铠甲冰凉,却让人十分安心。
冬嘉音量提高,又尖又刺耳,“你别以为我真舍不得伤你,逆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毁了我精心策划的一切!你忘了你的身份,忘了你惨死的父王吗!”
长极没有回应,任由冬嘉百般唾骂。
“你这混账,竟为了这个女人违背你的生母!你忘记身上的血海深仇,不思为父报仇,沉迷儿女情长,连人伦亲情都不顾了?”
长极嗤笑出声,后又冷冷回她,“逆子?确实是逆子。你还记得你是我的生母啊,我以为你忘了。你让我别忘了自己的身份,那你告诉我,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出生,原就是你为了争宠夺爱,设计为之。后来,又作为复仇的棋子利用。你说你是我的生母,可你不曾养过我一日,所谓的母慈子孝,人伦天乐,没有一样是你给我的。你逼着我向各家复仇,逼着我夺皇位,逼着我联盟鲁国,逼着我发动兵变,逼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凡此种种,我从未怪过你。可你不该,你不该伤害她!!我几世为人才找到她,你怎么敢!”
心下有一股热流涌动,感动之际不禁鼻尖泛酸,几欲落泪。
他说几世为人才找到我,难道他也记起了我们的前世?!
冬嘉怒吼:“我有何不敢,我要做成的事没有人能拦我,谁也不行,包括你。”
我抬起头恨恨的看着她,万分责怪她给长极施压,但这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事,应由他们自己解决。
冬嘉垂眸,继而又沉声道:“若有其他可能我也不想伤她让你难过,可她是用《蓬山录》换回来的人,唯有拿她才能做生祭,我是别无选择。”
长极冷笑:“我也是《蓬山录》换回来的,那你为何不拿我去献祭呢?”
冬嘉闻言一怔,脸色阵青阵白,惊诧的看向长极,眼神变得狠戾又疏远:“你是我的骨血,我怎会用你献祭?长极,我才是与你血脉相连的人,她只是一个外人,还是敌国的公主,她于你而言百害无一利,你孰轻孰重拎不清吗?”
长极不语,冬嘉神色柔缓,语气也随之温和下去:“你把她留下,趁天未大明,万人祭仍能继续,咱们就还有希望。我把她生祭了,我就能回到过去救回你的父王。到时候,你还是会出生,我们一家就能团聚,这多好啊。听话,你把她留下,用她换回你的父王。”
长极不为所动,冬嘉耐心哄骗,说得潸然泪下极为恳切:“念在我们母子一场,我对你父王又是一片痴心,你就成全母亲好不好。”
我听见长极咬牙的声音,额间青筋微凸,似在极力忍让。
“我说了,让开!”
长极一声怒喝,然后攘开她大步走开。
冬嘉怒不可遏,提剑就要来刺我,剑尖离我尚远,就被长极闪身避开。
“你竟如此对我,你这不孝孽障!”
冬嘉栽倒在地,面目狰狞,声泪俱下的指着长极破口大骂。
长极侧目睨着她,语气淡然道:“你若再敢伤她,再不孝的事我都做得出来。”
“难道你还能为了这个女人弑母不成。”
冬嘉怒目圆睁,厉声斥问。
长极向她走近两步,居高临下,漠然道:“上一世,我弑父杀兄,唯独没有弑母。您觉得,我这一世可做得出来?”
此话一出,我和冬嘉皆是惊愕,我心弦都在颤抖。
相比于我,冬嘉更是如遭雷殛,跌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的瞪着长极,错愕良久。
如此大不孝的话,谁闻之不是大骇,就算是为我,我也不愿长极为我背上这样大的罪过。我伸手拽了拽长极的衣服,对他郑重其事的摇摇头。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示意我安分待着。
此时,高台之下的厮杀已经暂停,长极带来的精兵未用多久便平息了方才撕咬的双方。跳舞祈神的巫师,提线木偶一般的死侍,还有那群不知哪来的流兵叛军,或被斩于剑下,或被生擒捉拿。
明明已是白昼,但天空灰蒙蒙一片,黑云压城,如在瞑昏。此间光亮皆源于地上那堆未熄的火堆。
火光斜影里,是尸骸遍地,血汇成河。令人望而生畏。
长极看了看台下惨景,回首低声斥道:“为你的疯狂执念,无端赔上这么多人命,是时候该结束了。”
冬嘉不屑道:“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你手上的人命可不比我少。你说我疯狂执念,你又何尝没疯过?梁国九皇子尹朝,弑父杀兄,踏着万人尸骸夺位。后又灭了齐国,遣术士为你筑转生台,以一国百姓为祭。你我是一类人,何必五十步笑百步?”
“是啊,不管我手上那些人命无不无辜,我都是个大奸大恶之人。我做了恶事,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鳏寡孤独,我受了几世。”
长极声音低沉,难掩悲切。若不是我趴在背上,都没有发现他的肩头在颤。
我只有两世记忆,而他却找了我几世?
此刻,我原先仅有的一点怨念也驱散了,我不在意他前世对我做了什么,也不在意他是不是同我一样都记起来那些事,如果可以,我宁愿他没有忆起。
一想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便抑制不住的心酸,眼泪连续不断地流下来。鳏寡孤独?前几世,他过得一定很苦。
正伤怀,又听冬嘉拂袖冷哼:“所以说我们是母子,为了心中所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
长极怒极反笑,试问道:“心中所爱?那他也爱你?”
“那是自然!”冬嘉坚定答之。
长极喟然长叹,正色道:“我与你不一样!你所谓的为了心中所爱,原本就是一个笑话,你是一厢情愿罢了!你以为你深爱着父王,他也同样深爱你,其实是你在自欺欺人!你当初能嫁给他,并不是他有多爱你,是你设计让自己有了身孕,才得以成为他的太子良娣,他深爱的人原本就是太子妃于氏。你憎恨太子妃,觉得是她抢了你的一切,所以在那场宫变中趁乱杀了她。可你不知的是,你费尽心思想要再续前缘的人,根本丝毫不在意你。”
“住口,你住口,你住口!!他是爱我的,他爱的人是我,才不是那个贱人!”
她右手仍握着剑,左手手背挡住半张脸,指缝间的眉头一阵抽动,好像在拼命的压抑着悲伤,泪水无声地从她眼角溢出来,打湿了整张脸。
“父王不在意你,一点也不在意!从他有心发动宫变起,他就为太子妃安排好了一切退路,唯独没有考虑你。”
“撒谎,撒谎,你们都在撒谎!他怎会如此对我?他怎会如此对我!”
她仍旧不信,却又撕心裂肺的发出质问。死寂寥寥,无人应语。
“曾经的东宫,后来更名成了展华宫。展华宫后庭植了一院子的栀子花,那里面的每一株花,都是父王亲手所植,每一株,皆是为了太子妃于氏。书房里有一个金丝楠木箱子,里面装满了于氏的画像和父王写给她的书信,他所爱是谁,还用多说吗?你蒙蔽自己二十几载,如今,也该醒了。”
长极不疾不徐的说着话,每一个字都像在剜人心,冬嘉脸色惨白得不见一丝血色,死死咬着嘴唇,没有言语。
她哭得肝肠寸断,顿了顿,又喃喃自语:“我做了这么多,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心里那个人竟不是我?怎么可能不是我?”
“你做的这些,他未必会承情,反而觉得你可怖。你可知当年宫变失败,皇祖父本不会杀他,只是打算将他软禁,是因为你杀了太子妃,他无心求生方才自刎的!他是殉情!”
长极这番话让她彻底崩溃,她就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目光呆滞,神情木然。
四下静谧,唯听寒风萧萧,战马嘶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心生一股悲凉的情绪。
“那我做的这些,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义......”
忽而,她抬头看着天,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终于嚎啕痛哭。
“多年痴心,原是个笑话,多年情衷,竟是错付,叫人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从前我说冬嘉疯,她也只是行为疯,而如今,她是真的疯了。
杀人不敌诛心,情之一字,最是伤人。
为那人精心谋划了这么多年,原以为是两情相悦,到最后,却发现是自己在一厢情愿,何其残忍。
我本该同情她的,但她为了一己私欲,挑起战火,枉送那么多无辜性命,迫使万人献祭,她便不值得去同情。
她的爱太可怕了。
她突然又哭又笑,提着剑慢慢往后退,步履踉跄,数次跌倒。最后一次跌倒爬起后,她看着长极释然一笑。
我见她笑过不下百次,唯独这次感受到真切,对比以前要么狰狞要么虚伪的笑容,这一笑,竟还能从中看出一点温情。
她脸上清泪蜿蜒,柔声道:“长极,我还未曾听你唤我一声母亲,你唤我一声可好?”
长极略略迟疑,终是开口唤道:“母亲——”
冬嘉闻言,瞬间眉眼舒展,笑得更欢。
短暂的安宁后,她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那十几个躲在一旁瑟瑟发抖的僧人方士傍,不眨眼的抹断了他们的脖子,随即捡起阳鱼眼里的蟒袍和黄布,转身一跃,坠入熊熊火堆中。
“母亲!!”
长极试图拉住她,但还是慢了一步。
那火原就烧得古怪,活人一入,如添干柴,越发燃得异常。
火舌一卷,冬嘉便悄无声息的化成了灰烬。她带着满腔的恨意和《蓬山录》跳进火海,从此世间再无冬嘉,也再无《蓬山录》秘术。
她的举止真是一如既往的疯狂。
那么决绝的一跃,定是绝望到了极点。或许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也算是彻底解脱了,可她做下的孽却仍在继续。
满目疮痍,山河失色。我闭上眼,不忍细看。
“长极,我们回家。”
“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