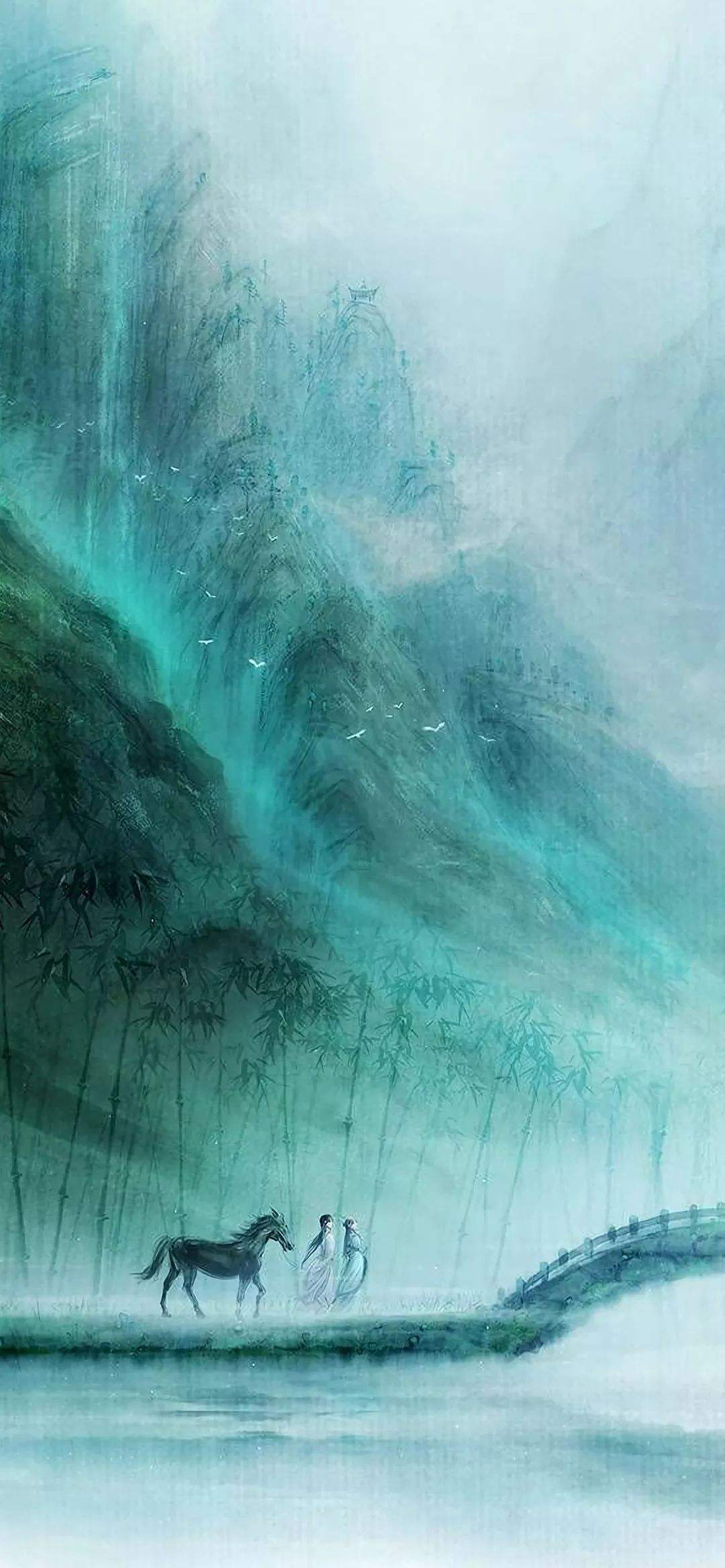贺平这边准备等那个衙役从房里出来再打一场的,这些人就是冲着粮食来的,房子里的东西就是罪证,与其成为阶下囚,不如搏一场。
与之相反,衙役那边等着同伴说出客房内有粮食他们就可以给外面的人发信号,收工了。大家开始撕着衣服包扎伤口,手里的刀也握得随意,一副打完清场的架势。
“看完了吗?你还要看多久?”有衙役骂:“老子是不是得在这里吃早饭?”
“里面......”年轻的衙役结巴着,不知道怎么说。
“里面有鬼是不是?你个怂货!”骂人的衙役跑过来,推开门口的人,自己进去。
“不可能!不可能啊!”进去的衙役连声呼喊,两方人都被吸引过去。
“看过了?各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们一定配合。”莫远山笑着问。
房子里空荡荡,除了年轻衙役看见的东西,谁也没看到别人的东西,成堆的粮食更是无稽之谈。
“怎么可能?”衙役中有人喊。
段岑他们也愣住了,要不是粮食是自己搬进来的,他们会觉得衙役是讲笑话,但现在,怎么可能呢?满客房的粮食呢,凭空消失了?就是被运走人手和时间也不够啊!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莫远山身上,等待他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莫远山神色如常,说:“各位都在这里,好好看看,这里哪有什么粮食,你们肯定是被人骗了,我们就是来探亲,不是坏人。都是平头百姓,哪里来的钱买粮食,现在这粮价都贵成金价了。”
“不可能!”衙役们还是这句话。除了这句话好像也说不出别的,消息肯定是真的,哪里出错了呢?
“怎么不可能?你们不是要搜吗,现在让你们进来了,搜吧,搜不出来是不是也得给我们个说法,口口声声说律法,律法里有随便闯民宅这一条吗?”贺平说,不论怎样,先把这些人打发走。
“官爷,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天都快亮了,不如您带各位官爷回去休整一下,今日大家也辛苦了。”段岑看贺平的态度,往衙役头头手里又塞了个钱袋,拍了拍。“粮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要是有谁也不能把它装衣袋里,官爷回去再问问举报人,看他是不是记错了。”
“头儿,咱们就这么被白打了?”有衙役问。
“不然你们想怎么样,你们也打了我们,难道让我们站着挨打吗?”贺平说:“穿身官服就能为所欲为?”
“你.....”衙役怒了,打你们怎么了,想打就打,随便找个罪名弄死你们信不信。
“走吧。”衙役头头转身出客房,往大门外走去。这些人敢动手,说明不怕官府,起码不怕当地官府。衙役头头经的事多,对这些有背景的人物离得远远的,本能地觉得贺平这帮人不是自己惹得起的,他们还是走为上计。
上面大人物的心思谁能知道,粮食没有搜到是这么多人看见的,又不是作假,他们打也打了,搜也搜了,该尽的职责尽到了,回去顶多落个办事不利,总比惹了不该惹的人,给自己埋下祸根好。
皇帝还有几个穷亲戚,干公家事,没必要结私仇。
最后一个衙役的身影离开门内视野一会儿,段岑几个人才神情放松下来。关上大门,几个人才感觉到伤口的疼,一时间龇牙咧嘴,呼声不停。
陈庚伤的最重,他的左臂被拉了一到很深的口子,血顺着胳膊往下滴,半侧腰身和袖子都被血浸透了,褐色的面料变成黑色。阿荷睫毛眨啊眨,眼泪比陈庚的血掉的还快。
打斗中有人被踢飞到阿荷身上,段岑右手拿刀正接了对方一招,看见阿荷被砸倒,急忙用左手把她拉到自己身后,被踢倒的人在空中乱扑腾,陈庚的手伸过来,他本想拉住陈庚的袖子,忘了自己手中的利刃,唰一声就在陈庚的胳膊上来了一刀。
刀的力度带着人从上落下来的重量,入肉很深,陈庚的左手提溜着,疼得满头大汗,问阿荷道:“你没事吧?”
阿荷盯着陈庚的胳膊不说话,眼泪不停流。
“你哭什么,受伤的是我不是你,要哭也是我哭。”陈庚说。
“神经病,你有病是不是?”阿荷骂陈庚。
嫁人后阿荷没和陈庚说过话,这几天两人刻意装作点头之交,李大牛在的时候阿荷和别的妻子一样给丈夫端饭,打水洗漱,有时当着陈庚的面,阿荷故意对李大牛显出不同于其他人的亲昵,同乡们打趣她,李大牛也更开心。
所以阿荷说身上不舒服,分开被子睡的时候,李大牛没有疑心。他每天赶活乏人得很,挨着床就睡着了,呼噜声震天响,没留意身边的阿荷夜夜流泪,早上眼睛肿成一条缝,他只当是白天累了没休息好。
阿荷做饭的时候,习惯性地给陈庚的碗底卧上个荷包蛋,面上不放香菜,多放辣椒和醋。端着一大盘碗上桌,阿荷随意地把陈庚的碗递过去,接着摆其他人的碗,等到李大牛接过碗,阿荷才反应过来。
陈庚的筷子戳到碗底,就知道自己的面和其他人的不一样了。担心段岑他们说闲话,陈庚把位子让给来迟的小贺,自己蹲到门外吃。老蔫起哄说陈庚这是吃独食,要看看他的碗,被段岑喝住。
阿荷的荷包蛋煮的很好,白白胖胖,鼓鼓地卧在碗里。阿荷讨厌吃荷包蛋,她不喜欢里面的蛋黄,吃鸡蛋只吃鸡蛋羹,滴几滴香油和黑醋,兑点凉开水,温度正好,出锅就能吃。
陈庚喜欢吃荷包蛋。陈庚娘不会做饭,经常就是煮面条,下点白菜梆子,放上酱油搅和一下就吃,逢到陈庚生日或者过年,就给面里打个鸡蛋。
煮面的火大,鸡蛋进去就被冲散,陈庚从来就没吃过完整的荷包蛋。看着别家孩子过生日,碗里都是细细的长面,上面卧着整齐的荷包蛋,陈庚很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