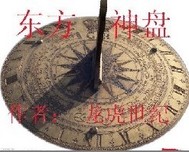天亮了。
“将军,恕我多嘴,您觉得我们有几成把握?”阿图尔斯骑在马背上,身后只跟了一小部分随从。
“百分之百。”叶世国没有回头,“你记住,藏狼之子,从来没有几成把握这一说。要打,就必须赢,并且要让对手一辈子对我们产生阴影,懂了吗?”
叶文拓穿了件黑色的羽衣,与两人并肩而行,他听到了两人的对话,但他什么也不想说。
“拓儿,等会与长安城统帅公良大人见面时,可不能再由着自己性子想说什么说什么。”叶世国略带疲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没有回应,咬着草根想事情。
最初的自己,似乎也并不是那么讨厌战争与父亲的,最初的自己,似乎也狂欢着躁动着藏狼的血液,沉溺于一次次胜利与荣耀带来的快感中,遥远的记忆中,自己日复一日地接受着藏狼族最古老纯正的训练,近身格斗、箭术、骑马、统领军队、战术推演、兵器使用……
那时候的自己,完完全全被当成一件兵器。
为了确保自己的潜力最大化,父亲常常狠心做出一些他一生也难以忘记的举动。他曾经被迫以一己之力赤手空拳与一百位全副武装的藏狼将士近身格斗,那一天,他一次次将眼前人高马大的兵士打倒在地,也一次次被踢飞出去,撞到墙上;被一拳打翻,血在空中降落;被冷冰冰的匕首划开皮肤,再咬着牙一脚把它从袭击者的手里踢飞;被人用穿着战甲的膝盖顶在下巴,碎裂的牙齿被打向头顶,转身自己就像条狼一般扑了上去。
给自己的最后一击,是腹部承受的真正的一道刀锋,只记得自己被狠狠甩向天空,又重重砸到地面。巨大的口子里,鲜血源源不断向外流,砍了这一刀的士兵吓得跪在地上像父亲求饶,可是父亲只是挥挥手,看都没有看自己一眼就带着士兵们离开了,只剩下捂着伤口跪倒在地上的自己,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
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么,对父亲的极度厌恶。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这样的日子,一遍又一遍,几乎布满了自己的前十八年。
不过,真正让自己对战争和这个民族绝望的,似乎还是应该追溯到那一天吧。
“求你了,救救,救救我们……”
“拓儿,身为军人,绝不能手软!对敌人手软,就是对自己残忍!来人,把他们处理掉,向皇宫进发!”
叶文拓没有说话,离开了回忆,这样的回忆,几乎出现在他的每个夜,每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每一个噩梦。他已经习惯了,一开始他还会吼叫着,但现在他不会了。
自己只是一遍遍灌下列图,在夜里一次次静静醒来,忍着头痛走到窗前,等到睡意再度袭来,再回到床上。
有些事,习惯了也就那么回事,是么。
叶文拓笑了笑,袖口的羽毛乱了,他吹了吹,一阵风悄然而至,将这片羽毛带至半空,摇摇晃晃,踉踉跄跄。
看这片羽毛,像不像夜晚的自己?像不像,自己的摇摇欲坠的人生和未来?
他停下了手,竟然笑了起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去查岗,然后这两个人主动袭击你,你干掉了他们之后,又有一个身手能对你造成威胁的神秘人袭击了你,并且对你说这两个人是藏狼的,然后他们还要对长安下手?”萧荣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整理着刚刚江长安说过的话。
江长安没理他,蹲在地上仔细地查看着两个人的衣服口袋,可惜里面什么也没有,不过之前掉出的那块牌子他已经捡起来了,也看过的确是藏狼族的,毕竟自己和皇帝的关系不错,有一次为了奖励自己找到了一个旧朝的支持者,公良负天给了自己一块牌子说是藏狼族的统帅叶世国给他的,现在他已经把两块放在桌上对比过了,的确一模一样,但是他还是心存疑虑,毕竟眼下藏狼族没有什么挑起战争的理由,万一是有人借刀杀人,那结果更加糟糕。在确定真相以前,江长安决定不禀告公良负天。
“你说什么,你不告诉皇上?”萧荣一口水喷出来。
“你慌什么?我有自己的考虑。”江长安在脑中计算着接下来的计划。
“你该不会,想自己解决吧?”萧荣躺在江长安的床上,玩着匕首。
“差不多吧。”江长安观察着两具尸体。
“带上我吧。”萧荣收起了匕首。
“我怕你感情用事。”江长安看了看他,喝了口茶。
“放心,我知道什么重要,分得清。”萧荣拍拍他的肩。
“对了,今天就要迎接藏狼的使者团了,你就别去了。”江长安一边想着事一边说。
“听你的。”萧荣推开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