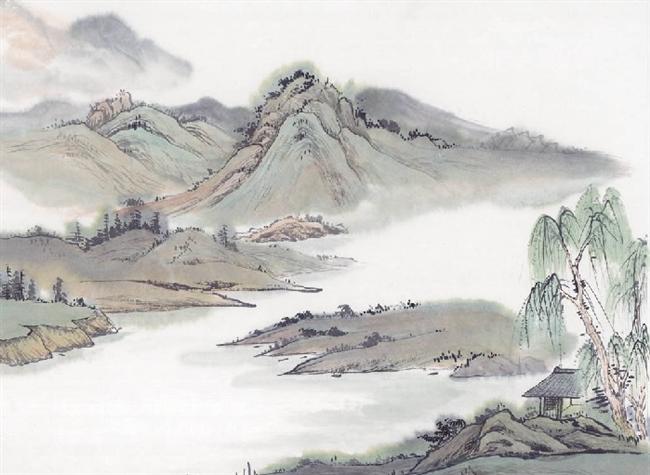翌日清晨,仇徒想叫越宁多睡一会儿,可越宁却偏要起来送他,他只好叫人做了早饭,和越宁一同用过后,两个人一个拄着拐,一个捂着后腰,身边围着几个人小心翼翼地盯着,唯恐这二人哪个不慎摔一跤。
及至东城门下,越宁已是腰酸背痛,不禁停了一步,仇徒看向她,“累了吗?别撑着,送到这里就行了。”
越宁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气喘道:“你要走,我不拦着,我送你,你,也不要劝。”
仇徒见她眸中坚定,叹口气,叫背着椅子的虞信过来,让越宁歇歇。
越宁却摆摆手,说:“好了。我没事了,走吧,快到了,不是吗?”
“还能走吗?身体要紧。”仇徒又不放心地叮咛道。
越宁冲他一笑,说:“这点路,什么时候能难倒我越宁。”
继续前行,及至一线天前,越宁的腿肚子都在打颤,仇徒虽然看不见,但越宁渐白的脸色他还是注意到的,他勉强站立,把拐给了童行,搂住越宁,耳语道:“等我回来。”
“嗯。”越宁哽咽道。
仇徒知道再等下去,越宁只怕会撑不住,所以连忙站直身子,说:“虞信,把马车叫过来,送夫人回去。路上慢点。”
原来一路上他们身后都有个大马车跟着。
越宁依依不舍地看着他,本想再叙话几句,可也知道自己身子受不了,便顺着女兵的搀扶上了马车。
“将军,你保重。”虞信望着仇徒的眼睛。
仇徒点点头,目送着他们远去。
童行叹口气,说:“将军,你一直想要来看夫人,怎么才一天就要走。”
仇徒眸子一凛,“夜长梦多,我必须尽快到龙首关。”
这时候,龙首关上飞过一只灰鸽,眼圈殷红,嘴角雪白,机灵地在空中兜了个圈子,飞进一顶帐中,乖巧地落在桌案上,目若无人般抖着一只细腿。
案前坐着一个消瘦的男子,窄额长脸,发髻高束,两片嘴唇上下是稀疏的灰白胡茬,显然新长不久。
他一瞧见鸽子腿上绑着的竹筒上三角鱼的标志,身子一颤,条件反射般抬头,才想起自己早已把底下人打发下去收拾东西,准备随时班师回朝,不由呼了一口气,怪自己大惊小怪。
旋即目光又落在那在桌上啄自己腋下的灰鸽,双手一伸,将它抓了过来,腾出一只手拍在它光滑的后脑勺上,说:“吓我一跳!这要是被人看见,你和我都得被砍头!”
鸽子却听不懂,只知道脑袋上一痛,就啄起男人的手指。
男人立即取了信,将它丢了出去,“烦人的畜牲!”
话音未落,鸽子呼啦啦地扇着翅膀飞走了。
男人打开信条,眉头一跳,匆匆取出火折子,将信点了。直看着信烧成灰烬,这才捂着自己砰砰乱跳的心,瞪着一双眼睛,自语道:“太子啊太子,你这是要玩火自焚哪!”
这男人是广和军府的都尉雷邦,此次出征编制时给了他一个将军的名号,统管两个军府的人,约莫五六千。一听广和二字,人就知道他和太子广和王是一伙的。其实早些年被分到广和军府时他也是个清清白白的人……
他揉揉眉心,想起自己一家老小还在广和,而且这些年太子也没亏待自己,自己也有意无意地为他做了些事情,早已和太子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纵然他起先多么不愿淌这淌浑水,别人也始终看他为太子的走狗。
后来怎么就和太子绑到一起了呢……
哦对,帮着太子隐瞒了他羞辱广和军府的一个女兵的事情,后来那女兵自尽了,太子怕东窗事发,用老母亲的性命威胁自己找个由头杀了那女兵的丈夫。
呵,怎么想起这些了呢。
雷邦拍拍脑门,撑着双膝站起身,伫立了半天,才抬起沉重的脚往主帐走去。
原来前几日他将边关的消息告诉了太子,太子听说战事指日可息,立即修书一封与他,说纵然通敌,也要把仇徒留在边关,拖到皇帝咽气,最好能杀之。
本来各家心腹给各自主子寄消息也是军营里常有的事,除非那种特别要封锁消息的军令外,其余通风报信的事情,旁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走到他们这个地位,谁背后还能没有个靠山,或者说,谁还没欠过几个人情?
总不能别人都知道边关的消息,堂堂一国太子不知道吧?雷邦也只是依样画葫芦,简单说明下情况给太子而已,叫他在朝堂上不至于被别人摆一道。
但谁想太子会给他这样一个棘手的任务。
眼看着两国停战在即,竟然叫自己搅动战局!还——还让自己杀害大元帅……
关于西凉退兵的事,他隐约从蒙勒的反应里看出这是仇徒的功劳,可见这个元帅比传闻中还要有本事。这样一个人才,自己怎么下得去手。
可,偏偏这个元帅是长平王的人!
唉,谁都知道太子和皇上都畏惧长平王,生怕他强取,所以借着这次出征瓜分长平王的势力。
罢了罢了,总之谁当皇帝都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那老母能安度晚年,两个孩子能平安长大, 别的什么人,什么事,他一概不想!
心思敲定,他冲主帐外的守卫打了招呼,便进了帐中。
“蒙将军。”
蒙勒的目光从宝刀上收起,看向来人,不禁皱起眉头。他惯来不站队,什么太子、长平王,他都不管,谁拿着虎符、谁有圣召,他就听谁的。所以他对仇徒和面前这个雷邦,都有点反感。
不过仇徒有本事,他不服也得服。这个雷邦嘛,也没见什么成绩,这个位子指不定怎么来的呢。哼。
“不张罗着收拾,跑本将这里做什么。”蒙勒端着架子坐到几案边,慢条斯理地给自己倒了碗茶水。
边关条件差,但他本身也是大老粗一个,所以也不用茶具,纯粹的大碗,倒一碗就仰头豪饮,叫雷邦站在那里,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便搓着手,说:“将军,我今天来,是想说…”
雷邦记得蒙勒前几天看见西凉撤兵,收到仇徒的信时还怒气冲冲地要做点什么,但紧跟着没几天听说仇徒要赶来龙首关的消息后,他又下令让全军整顿,随时准备拔营返程。
摆明这个蒙将军不想就此撤兵,他这个年纪早就看淡生死了,还要出征,为的就是多存些军功,换个高点的爵位,可以给子孙留些东西。
然而他们那个大元帅只想着用最快的办法停战,把损失降到最小,至于那些功名利禄反而不看重。不过话也说回来,不管这仗打得快慢与否,只要胜了,他这个元帅都是有功劳的,所以也不必在乎其他人想要拿军功的心情。
想明这一点,雷邦继续道:“这个兵不能撤,要打!”
蒙勒眼皮一跳,他想打仗,比任何人都想,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活脱脱一个败家货,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整日游手好闲,喝酒发疯,打妻打子,自己这一辈子攒下的积蓄和名声都叫他败坏完了。可不管怎样,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就算不为他想,也要为自己那宝贝孙子多做些打算。
只是虽然心中想战,奈何大元帅说动了西凉撤兵,两国停战在即,他能有什么办法。如今听道雷邦的话,他固然想附和,却不知道雷邦有什么说法,只能冷淡地挑起眉头,道:“打?你没瞧见西凉撤兵了吗?怎么打?还能追到人家地盘上去?你有名头吗!天真!”
闻言,雷邦倒没在意蒙勒的讥讽,反而心中更加肯定这老将军的想法和自己猜想的不错,抱拳道:“雷邦有三点战由。”
蒙勒一怔,这话可正中他心头,下意识身子往前倾了一些,说:“说来听听。”
雷邦暗暗一笑,面上矜持道:“一,出征前分明接到线报说西凉不是简单骚扰,而是要举国之力灭我孱国。从他们边关陈兵就可见起野心。只是不知他们内部出了什么乱子,两万兵临境数月,也不见增援。两边交手了十几次,但都小打小闹,连三千人的战役都没上过。”
蒙勒点点头。他何尝不是气这个,你说西凉这群蛮子,要打你就痛痛快快打,总是打一打,跑一跑,跟苍蝇似的,烦人得很,打半天还不见血,显得自己多没本事似的。
“他们那是胡言乱语,灭我孱国,把牙笑掉!”蒙勒冷笑道。
雷邦见蒙勒听进去了,便更真切道:“灭孱国单凭西凉自然是不行,可这消息总不会是捕风捉影,将军应该想,是谁一开始给了西凉底气,叫他有胆子说这话?”
蒙勒心脏停跳半拍,“你是说……西夏?”
雷邦不置可否,只是道:“将军,不管是谁给了西凉底气,后来这里都出了岔子,以至于他们不敢真的和咱们撕破脸皮。那边大元帅一给他们台阶,他们自然就乖乖撤兵了。呵,不得不说元帅这步棋也讨巧了。”
蒙勒眼珠一转,原来这里还有这层关系。就说仇徒那小子凭什么说退西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