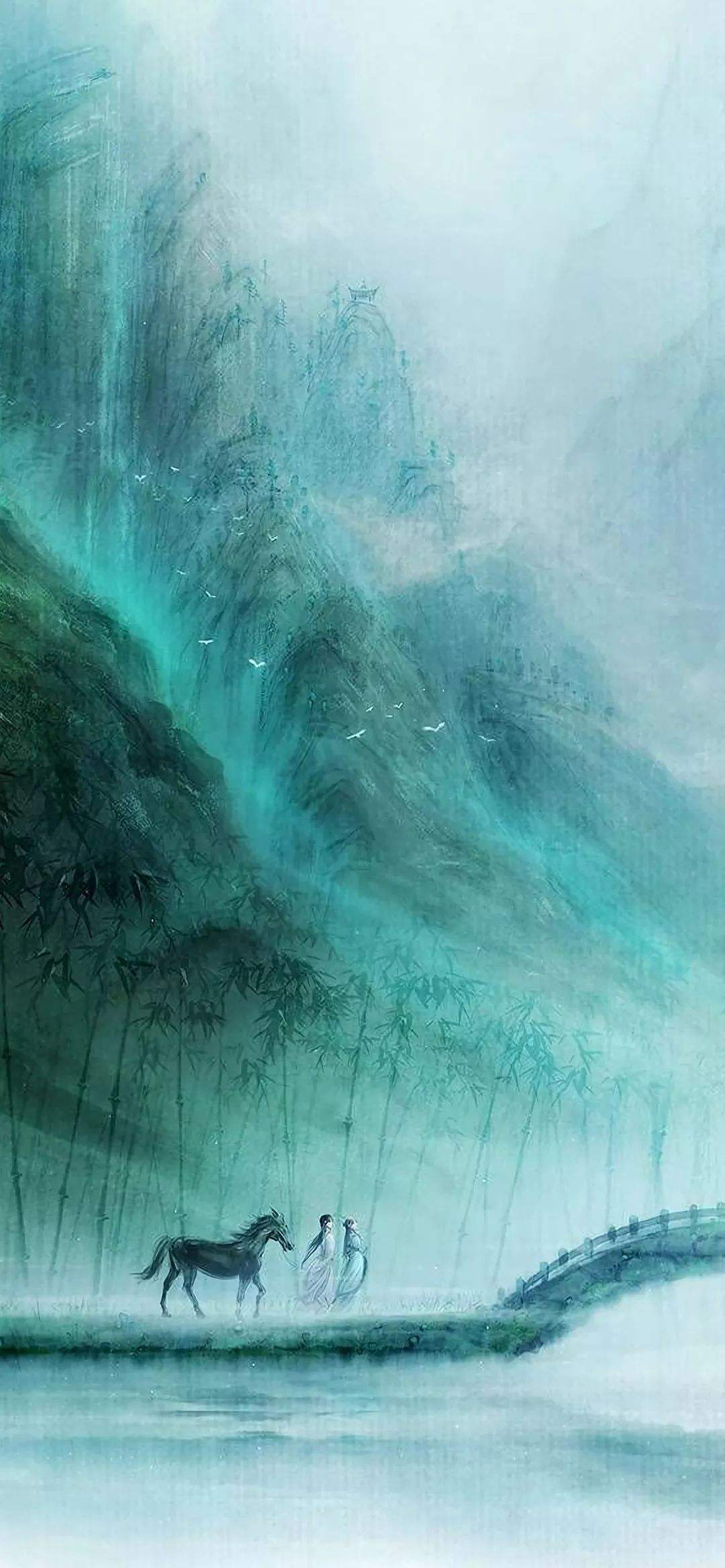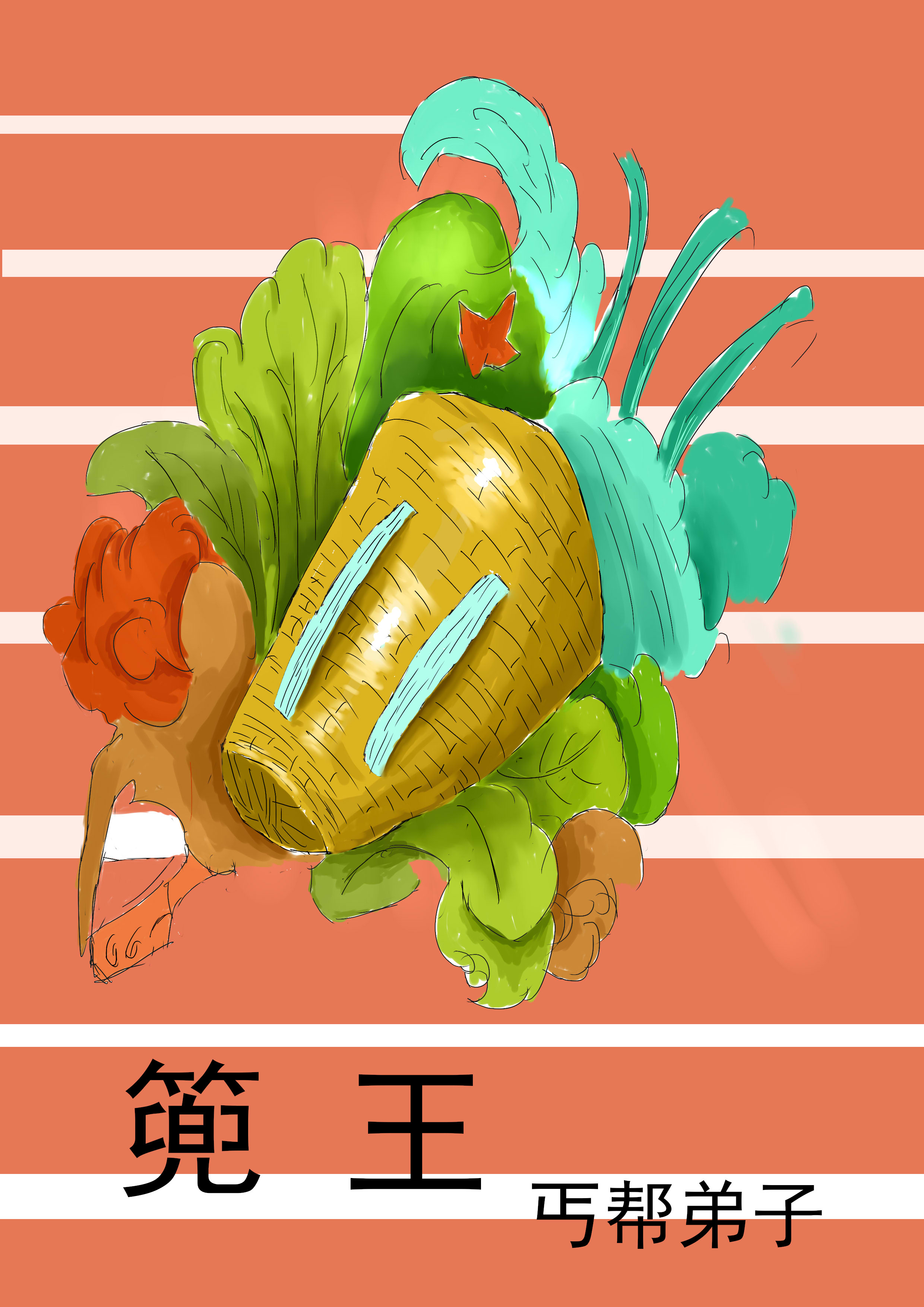越宁盯着地板,不看仇徒,问:“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是,我骗了你,我该受什么是我自己的事。那个丹丹…我也对不起她。如果你们要在一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你走吧,我不想再说了。”
仇徒痛苦地攥在空拳,“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让我明白什么,”越宁红着眼眶,“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哪怕你要娶她,我也要大度地说去吧,我理解你,因为这都是我的错?”越宁忽地笑道:“是啊,都是我,我怎么能怪你呢…对不起,我真的太乱了。求你了,让我自己静静吧。”
仇徒本还想再说什么,越宁却已经扶住额头挡着视线,不愿再交谈。他斟酌许久,却也没有想到什么可说的,只得憋着一肚子话离开房间。
那一晚自己被暗器所伤,倒在街头,是丹丹救了自己。看见她住的简陋的房屋,瞧见她身上斑驳的伤口,询问起来才知道她是孤儿,早些年出现在泰山是因为养父上山采药,救他纯属偶然。至于他所说的以身相许,她不过当做童言无忌。却不想有一天果真看见举国贴满了找她的告示。当时她正在孱国边界的小城住着,养父染上赌博恶习,要将她卖了抵债,她为了改变命运,一路走到京城找仇徒。却不想仇徒已然成亲。听说仇徒找到了画中女子,她想,或许那画像与经历不过是巧合,又或者仇徒根本只是戏言而已,她怎会如此好运?于是她在京城做工一年,返乡寻找养父,报他养育之恩,却不想养父已经死了,留下义兄义嫂二人。
那二人见她有几分姿色,便也要卖她。她一路逃入西夏,竟然被人当做奴隶抓去,给人做了婢女。那主母脾气不好,整日打她。若不是那日夜半主母还让她去街上带吃食,她是不会遇到仇徒的,更别说救他。她说这是缘分,她无论如何也不愿再继续现在的生活,她求着自己,说带她走,哪怕不能入庙堂,做个妾侍也比如今风光……
然而这一切,如何能告诉长安?尤其是在长安为自己承受这一切之后……更何况,他对丹丹不过是年少时不懂情事的一句感激的承诺,对长安,却是全然不同的感情。如果从未见过长安,便不会如此心痛。
房内,越宁呆坐在地上,蜷缩着,从未如此寒冷。
腊月十日,泉君不得不去参加围猎,越宁执意留在府中,不愿见旁人。仇徒因在府上诸多尴尬,便搬到附近的客栈居住。他身上还有皇上的嘱托,虽然心烦与越宁的事,却仍要替皇上探查西夏国的虚实。他是想去围猎的,按道理,他此次来西夏,虽然是以西夏将军的家属身份探亲来的,但自己毕竟是孱国的大将军,总是应该和越宁一起去拜见西夏皇上的。只是越宁身子如此,自己又遭人暗算,总是耽搁了。他想着等越宁冷静下来,与她心平气和地聊一次,将这件事说清楚,然后与她一同去拜见皇帝。
他是如何也舍不得越宁离开自己的。只是丹丹……
他索性不再去想,也顺从自然地等着。
泉君不在府上,府中只剩下了越宁和越危夫妇。越危去给越宁打了一支新笛子,与她一道奏乐和声,让她心绪安宁。戚氏也为她烙饼,与她一同做饭,闲话家常,让她不要思虑太深。
这一日,在灶房里,戚氏打发走了下人,和越宁一起做饭。忽地见外面飘起了雪花,她笑着说:“宁儿,你看外面。”
越宁正蹲在地上摘菜,抬头看去,北风夹带着雪花卷入门下,她扬起视线,只见白光下黑色的雪正飘摇直下。她不禁想起上次看见雪,还是在边关的时候,忽地心头一紧,立即摘起菜来。
戚氏却没有瞧见她的不自在,温情道:“记得从前在山上的时候,你和泉君最喜欢下雪了。今天泉君就该回来了,等雪停了你们又可以比试雪中弄剑了。”
随着母亲的话音,她想起从前在山中的岁月,那时候与泉君纯真无邪,每每落雪,总要比比谁能踏雪无痕,谁能剑扫漫雪纷飞之景。却如今,她根本提不起剑来。只是她不想让爹娘担心,所以并未告诉他们。
“嗯。”她心不在焉地答应着,目光再一次被风雪吸引。
客栈中,仇徒望着窗外的飞雪,一片凄然。
近黄昏的时候,泉君顶着毛皮帽子,夹带着雪花进了门。他一进膳堂,就嘿嘿地笑着将帽子摘下,把大氅解开,趁爹娘与他问候时他一个调皮将大氅一抖,顿时膳堂雪花乱舞,甚至落入饭中。
“你这孩子!”戚氏嗔他。
他嘿嘿一笑,将大氅交给下人,紧贴着越宁坐下,“阿姐,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他一面说一面从怀里掏出一把黑豆子来给越宁看。
“什么呀?”越老爷和戚氏问着。
越宁瞧见那黑豆子,惊奇道:“从哪里得来的?”
泉君一笑,哗啦啦将黑豆子放在越宁前的桌上,说:“我围猎时候瞧见的。就知道你喜欢,嘿嘿。”
“你们俩神神秘秘的,那是什么东西。”二老盯着那黑乎乎的豆子问着。
泉君吐着舌头,“我和阿姐的秘密。”
越宁正高兴,却又怅然道:“可惜老胡不在,也不知它如何了。”老胡是越宁救的小黑豹,除了食肉之外,最喜欢吃这种脆脆的小黑豆。泉君总是见越宁在山上找豆子,所以有时候越宁不高兴了,他就会捡豆子哄越宁开心。不过他并不认识老胡,也不知道越宁此刻为何高兴又不高兴了。
“阿姐,你就别不高兴了。唉,我都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了。”泉君无奈道。
越宁闻言拍了他一下后脑,“我哪有不高兴,赶紧吃饭!”
一家人闻言对视一眼,都笑了。
没有下人,他们一家四口仿佛又像从前一样,只是不用担心屋顶漏雨雪,不用担心西风吹坏了门窗,不用担心有野兽进来躲避风雪而惊吓。
正吃得高兴,戚氏迟疑许久终于开口道:“这…也快过年了,他一个人在外面住,不太好吧。”
越宁一怔,她自然知道娘口里说的“他”是谁。只是,她还没有想好怎么面对仇徒。这几日她也想了很多,这件事到底是谁的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开始对仇徒说了谎。现在他想必也很为难,只是自己能如何决断?若是自己身子还好,便狠了心不让仇徒纳妾。可自己终究是没了延续香火的能力,正如娘所说,以后自己定是要受着一些言语叨扰,甚至与人共侍一夫的事。但这种事,想明白了又如何?难道真能说接受了,就接受了?仇徒怕是也还没有接受他自己被骗的事实吧?
瞧越宁不语,越老爷急忙打圆场,说:“哎呀,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吗,到时候再说,吃、吃。”
越宁回过神来,继续拒绝起食物,却心中暗暗决定,是时候和仇徒好好聊一聊了。
那些伺候她的下人她已经指给仇徒了,只留了扇萍一个。等用过膳,回到房中,她便让扇萍替她打扮一番,取了冬衣,便要去仇徒落脚的客栈去。本来也是可以叫他来府中的,但这毕竟是泉君的地方,爹娘也在,太多人,万一谈得不愉快,有些场面还是有避忌一下的。
越宁走的很快,寒风刺骨,她体温始终没有上来,一直哆嗦。
扇萍用身子替她挡着一半风,道:“夫人,这西夏的冬天太冷了。您身子受不住,一会儿到了客栈,您用公子的大氅再裹一层吧。”
越宁忍者哆嗦说:“扇萍,你是她们中最心细的,所以我才留你。我和你们公子的事,你们不知道原委,等会儿进去了,你就张罗着下人去楼下喝茶喝酒,钱我来出,我要和你们公子单独待会。”
“行。”扇萍搂着她,“但您也要紧张着自己的身子。”
“我知道。”
说话间,她们就走到了客栈。顾不得小二招呼,她俩就上了二楼。
扇萍敲了两声门,门便开了,是松子。扇萍因为常来送东西,松子也见怪不怪,但是一晃眼瞧见越宁,他嗓子眼忽然堵了一口气,激动地回头胡言乱语:“公子,夫人,公子,夫人。”
仇徒正在窗边读书,淡淡地抬起头来,瞧见越宁已经拨开松子走了进来,他四肢百骸都仿佛僵硬了一般,有些出神。
越宁给扇萍了一个眼神,扇萍知趣地将松子带走,从外面关了门。她又问了松子其他下人的去处,确保无人会来叨扰,这才放心地在听不见却看得见房门的地方听了步子。
屋里,越宁自己找了个座位坐下,仇徒放下书,取了一方手炉来递给越宁,“先暖着吧。”
越宁确实冷得厉害,也就不推辞,拿过来捧在腹前,抬头看他,说:“我们该聊聊了。”
仇徒点点头,在距离她一米处坐下,望着她,“你身子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