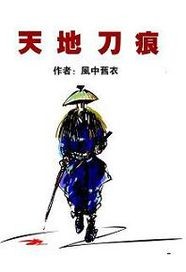西门东石双掌互击,方才的素衣小婢又托着两杯酒款款行出,将酒放在桌上,欠了欠身,又款款退下。
西门东石举杯道:“宣掌门远来是客,在下谨以水酒一杯相敬。请!”举杯饮干。宣明宇也举起了杯子。
凌剑云在旁边看得暗暗焦急,心知那杯酒定有古怪,偏又不便出言提醒。
宣明宇酒杯到了嘴边,忽然定住,又放下了。
西门东石眉毛一扬,道:“宣掌门,有什么不妥吗?”
宣明宇神色淡淡,道:“恕宣某失礼,只是事情未曾谈拢,宣某实无喝酒的兴致。”抬眼看着西门东石,“阁下还是先明白说出有何条件吧。”
西门东石直视着宣明宇,哈哈笑道:“既然宣掌门如此爽快,那在下便直说了。”顿了顿,道:“敝帮希望能与宣家携手合作。”
宣明宇也回视着西门东石,道:“怎么个合作法?”
“宣家在嘉定势力庞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宣家与敝帮合作,敝帮在嘉定行事之时,宣家须助敝帮一力。”
宣明宇默然半晌,道:“阁下的意思,是要宣家听从虬龙帮之令,随时应命行事?”
西门东石淡淡一笑,却不回答。
宣明宇长长吸一口气,忍耐着道:“贵帮如此手段,不怕让天下英雄耻笑吗?”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下认为,若然事事缚手缚脚,如何成事?”西门东石倒是振振有词,毫不在意。
宣明宇眉头深皱,显是心中有着激烈的冲突。
西门东石等了一会儿,语气忽转严肃:“宣掌门固然可以慢慢考虑,但在下却不免担心,秦姑娘可是正受着毒伤折磨……”
宣明宇猛觉一股热血上冲头脑,大声道:“贵帮如此手段实在是太卑鄙了!宣家世代,虽不说绝不违侠义之道,可也绝不能与邪魔外道同流合污,助纣为虐!”
“宣掌门的意思,可是不答应在下的条件吗?”西门东石冷冷问道,“那宣掌门可是准备让秦姑娘香消玉殒了吗?”
宣明宇眉宇中掠过一丝苦痛,但仍旧道:“宣某决不可败坏宣家家声清誉。至于秦姑娘,若然真有什么不幸,宣某自当向秦老英雄谢罪!”言罢,拂袖而起,转身待走。
西门东石忽然站起,冷冷道:“宣掌门说走就走,岂不是太不给敝帮面子了?”宣明宇冷哼一声,脚下未停,径直前行。
岂料,宣明宇刚到门口,门口就忽然出现了十几个身着灰衣,灰巾包头的蒙面人,长剑出鞘,挡住宣明宇去路。
宣明宇暗中运气戒备,回头对西门东石道:“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西门东石淡淡道:“敝帮虽非铜墙铁壁,但也不是任人来去自如之地。宣掌门想离开,便请先打发了这几人吧。”
“好,既然贵帮如此横蛮,在下只好得罪了!”话音刚落,宣明宇已拔剑出鞘,疾向一个灰衣人攻去。灰衣人反应极快,一剑格开宣明宇剑势,反击而上,余下灰衣人也各展长剑,齐向宣明宇攻去,宣明宇顿时陷入混战中。那些灰衣人似是训练有素,虽在混战中,出手仍是有条不紊,时而一人出手,时而数人合攻,但脚下奔走不停,绕着圈子将宣明宇围在中间。宣明宇家学了得,虽被困在中间,但手上剑势丝毫不乱,长剑舞得密不透风,护住了全身,不时看准机会刺出伤敌。然而,灰衣人的车轮战法,还是让宣明宇一时无法脱身。
凌剑云站在庄子奇身后,眼睛却一直看着宣明宇和灰衣人的打斗,心里不禁为宣明宇担忧。他明白宣明宇此刻看来虽是仍旧毫无破绽,但这等车轮战法,极耗功力,宣明宇内力再强,也迟早会有耗尽之时,这么打下去对宣明宇极为不利。
凌剑云想了想,悄悄拉了拉庄子奇的衣服。庄子奇回过头,凌剑云示意地看看宣明宇,又看看西门东石。
庄子奇会意,上前对西门东石低声道:“军师如此缠住宣掌门,不知有何用意?”
西门东石神色平淡道:“庄寨主看下去不就知道了。”
庄子奇碰了个软钉子,心里不禁有些生气,但忍耐下去没再说话。
凌剑云在一边看见,心里也对西门东石反感得很。
忽听宣明宇长啸一声,剑势忽然加快,长剑疾刺面前正中的一个灰衣人,待那灰衣人疾退避开,右侧一个灰衣人长剑疾刺过来之时,竟收回长剑,抢入剑光,一掌拍在灰衣人胸口要害上,显是他也觉出继续被围困下去非长久之计,冒险近身抢攻。那灰衣人要害上中了宣明宇一记重掌,哪能有幸,当场气绝倒下。灰衣人中倒下了一人,严密的圈子立现缺口。宣明宇抓紧时机,一提气,手中剑护住身子,疾冲出了灰衣人的围困圈子。
西门东石脸色微微一变,口中却道:“宣掌门果然好武功,令在下好生佩服。”
宣明宇横剑当胸,道:“阁下还有什么指教吗?宣某在此恭候!”
西门东石淡淡一笑,道:“其实敝帮也只是希望与宣家和平共处罢了,这般说僵了动起手来,实在大违敝帮本意。”
“道不同不相为谋,宣某与贵帮,可没什么好说的了!”
西门东石眼中凶光一闪,道:“宣掌门的意思,可是决心和敝帮作对到底了?”
宣明宇正色道:“既难为友,为敌那也是在所难免。”
西门东石冷笑道:“既是如此,敝帮也不厚颜攀交了。”
宣明宇冷哼一声,并不置答,挺剑往门口闯去。忽然白影一闪,“白无常”任长江飞身挡住了宣明宇,嘿嘿笑道:“宣掌门好武功,老夫也很想领教一下。”
宣明宇举起长剑,道:“当得奉陪,阁下亮兵刃吧!”
任长江傲然道:“不劳宣掌门费心,当用兵刃时老夫自会动用。”言下之意是毫不将宣明宇放在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