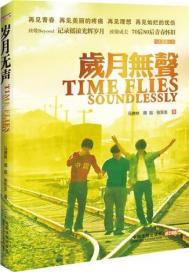章立早随剧组一从外景地回来,脸没洗便骑上自行车往幼儿园赶,他怕去晚了,黑子被接走。
赶到幼儿园时,幼儿园的铁门已经开了,等在铁门外的爸爸妈妈们迫不及待地拥了进去。他一眼就看见了黑子,黑子正孤单地站在一棵树下背着手仰着头朝树上望。树上正有一只蝉寂寞地叫着。章立早叫了一声:黑子。黑子很慢地转过头朝他望了一眼,终于发现了他。黑子的眼里有很亮的东西一闪,很快又不见了。黑子仍背着手冲走过来的他说:你好。他听了黑子的话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悲哀,这种悲哀像洗淋浴一样很快涌遍了全身。他蹲下身看着黑子的眼睛,黑子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看着一个又一个小朋友被爸爸妈妈接走。他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小塑料袋五彩石递到黑子面前:看,黑子喜欢么?这是爸爸从南京给你带回来的。黑子犹豫地伸出手接过那一袋五彩石小心地装进口袋里,瞅着他说:妈妈一会儿就来了。
他叹了口气,想冲儿子说点什么。这时他看见小葱阿姨朝这边走过来。小葱阿姨笑着冲他说:章导演怎么好久不见了?他站起来,手抚着黑子那颗毛茸茸的头说:去南京拍片子去了。小葱阿姨就很媚地冲他笑,他就想起以前小葱阿姨对他说要当演员的话。他忙说:小葱你的事我记住了,一有合适的机会我就让你上。小葱阿姨就很甜地说:黑子顶聪明了,没事他就像大人似的爱琢磨点事。
孩子们都被接走了,一时间幼儿园里的一切很空荡。黑子朝门口看了一眼,回过头冲小葱说:阿姨再见。又看了一眼他嗫嚅一下说:爸爸再见。黑子说完再见时,他分明听见黑子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他的心又紧抽了一下。回过身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肖南芳。肖南芳没有看他,一把把黑子抱起来,声音有些哽咽地说:想妈妈了吗?一边把黑子放在车后座上,黑子嘀咕一句:妈妈你就不能问点别的。好啦好啦,妈妈不问了。肖南芳一边说一边推起车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小葱阿姨很快地脱去了白大褂,露出一双穿紧身裤的大腿,那双优美的腿向前移了两步,用一种很热情的声音说:章导演不到屋里坐一会儿?别的老师都下班就我一个人呢。然后带着一种暗示地望着他。他突然想呕吐,白着脸望了一眼刚才儿子看的那棵树,此时树上的蝉不叫了,世界一下子变得很空旷。
他离开幼儿园,很没滋味地在街上走。正是下班的时候,车流人流汇在一起让人想大喊大叫几句什么。他有些茫然地走在人行路上,看着眼前的一切觉得既熟悉又陌生。他在人群中艰难地走着,不知要走向哪里——他又想起了不知在他幻觉里出现过多少次的场景——
大漠。落日。一支驼队悠然地走在戈壁上,无风。画面半明半暗。西坠的落日拉长驼队的影子,影子像一座座山向前移着。
戈壁空旷如野。一个孤独的旅人走在驼队后面,一件老板羊皮袄,头发零乱,胡须不长却坚挺。大漠空寂无声。驼队滞重单调的声音像一串杂乱的音乐,河水一样向前流淌。旅人的目光望穿大漠,空旷渺远。
很长时间了,他一次又一次温习着这样一组单调的画面。这一组画面他曾经历过,就在他的一部影片里。此时,这部影片的所有情节他早就淡忘了,惟有这一组画面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看报睐,看报睐,《古都晚报》,花边新闻,导演离婚,另有所爱,快来看,快来买呀——一个小伙子站在报摊前起劲地吆喝着。
他一激灵,从远古的画面中回到了现实。小伙子仍在喊——导演离婚,另有所爱,。快来看,快来买呀——
一个少女手捧着一份报纸边看边冲同伴说:我要是那个女主角就好了,潇洒爱一回。
女伴说:人家导演能看上你?听说人家又拍完了一部片子,题目就叫《爱不回头》。
章立早立住脚,一直看着两个少女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他想报纸上一定又编排了他什么,他从卖报的小伙手里买了一份《古都晚报》,他在二版上很快找到了自己那条花边新闻,题目就叫《爱不回头,潇洒一回》。还配有一幅他和某女演员的工作照。正文他看都没看,便几把撕了那份晚报,他找了半晌也没有找到垃圾箱,便一扬手把碎纸片扔在了街上,随后仰起头冲天空骂了句:日你们母亲——行人立住脚惊惧地望他,他的耳畔响过几声惊惊诧诧的声音:一个疯子,这人准是疯子。他没有理会那些声音,跳上自行车疯了似的向前骑去。他认识乔虹是在电影学院的宿舍里。那时他准备投拍一部电影,剧本已经写好,是一部城市爱情题材的片子,剧本从主题到立意都很新颖,他不想把片子拍俗了,因此他不想用那些观众都熟悉的演员。他想用一些新面孔来完成他的再度创作。他想到了电影学院这些本科班的学生。一星期前他就带着剧本来到电影学院,让她们先读读本子,然后再听昕她们的想法。他读剧本时其实女主人公的形象已经在他脑子里活了,长得不一定漂亮,但一定得有气质有个性,敢说敢爱敢恨的那一种。他一走进电影学院的大门,眼前陡然就亮了一下,他想起摄像李以前说的一句话:电影学院是美女国。他一想到这话心里就笑了一下。他看见树荫下有几个姑娘在练形体,她们的确是无可挑剔的。
那一天晚上他坐在她们的宿舍里,刚开始还很振奋,觉得眼前任何一个姑娘都可以演这部戏的主人公。可听了她们说完了对剧本的理解,刚进门憋着的那股劲便一点点地消失了。他看着眼前这些漂亮的一群,心想,这些姑娘其实也挺可怜的,除了爹妈给了她们一张好看的脸蛋外,似乎脑子里还缺点什么。他听着她们一个个地发言,他开始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没有礼貌地征求一下她们的意见,便点着了烟,她们似乎并不计较这些,有个女孩还自己动手从他烟盒里抽出支烟,熟练地点燃,他冲那女孩笑一笑,发现她正很媚地冲自己眨眼睛,他佯装没见。他长吁一口气,准备一走了之时,突然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姑娘说:能再坐一会吗?我想说两句。他听见她这么说,便把要立起的姿势又收了回去。他盯着她问,你叫什么?她说:乔虹。他冲她点点头。
乔虹坐直身子不动声色地说:我觉得剧本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很普通的姑娘,正因为她的普通,才有了她恋爱以后极不普通的心理,她怕失去那份得到的爱,更怕对方瞧不起她,于是才有了她剧本中的矛盾纠葛,最后悲剧的结尾,也完全是她的普通命运造成的,如果她潇洒一些就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正因为她的普通,没那份洒脱,才有了现在这样的结尾……
她说这些的时候,他一直注视着她。她的确在这些漂亮的姑娘中算不上漂亮,可她对剧本主人公命运的把握已经吸引了他。她还没有说完,他就想,就是她了。她一直说下去,说得很激动也很动情,脸涨得通红,由此他断定眼前的乔虹在平时场合下绝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一等她说完,他就说:明天你能找我一下么?说完他掏出名片递给乔虹。乔虹接过名片并没有看,而是冲他点点头。
那部片子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一切都挺顺,乔虹自然也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乔虹也因此而崭露头角。那时乔虹还没有毕业,她还是一个学生。
那部片子一拍完,到后期制作,到公演,直到获奖,一路绿灯。可他心里仍怅怅的,似乎少了什么。他就想:是不是已经爱上了乔虹。但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想法。那时他还没有和肖南芳离婚,和肖南芳离婚是以后的事。
他在电影厂招待所里见到乔虹是转天早晨。他见到乔虹,乔虹刚起床脸还没洗,他看见乔虹两眼有些红肿,他似乎猜到了什么,没说什么,把食品袋里的两根油条放到茶几上说:还没吃早饭吧?乔虹从床下拖出脸盆走出去。他点燃支烟坐在沙发上,他的目光定在被角压的报纸上,他伸手拿过那张报纸,正是昨天晚上他撕过的那张晚报,他一眼就看见了他和乔虹坐在树下谈剧本的那张照片。他松开手那张报纸落在地上,他深吸口烟,把头靠在沙发上。有关他和乔虹的花边新闻他听到的太多了。无论他走到哪里,也无论是剧组里有没有乔虹,他和乔虹都会作为一种当地的新闻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些照片和这些新闻是哪些无聊的人编排出来的。他不想兴师动众起诉那家报纸,这样的报纸多得让他起诉不过来,他也没有那个心思起诉,他觉得这一切都无聊极了。他和乔虹一直都用沉默看待这件事的。
乔虹洗漱完进来的时候,他已经把那张报纸重新拾起来放到原来的地方了。他站起来说:先吃点东西,然后去录音棚,今天开始录音。乔虹点点头。他站了一会儿,把半截烟扔到门口的痰盂里,走了。
:
录音的时候,乔虹莫名其妙地走神,声音总是和画面上的口型对不上。章立早一次次喊停,他瞅着乔虹说:你不应该这样。乔虹勉强地冲他笑了一下,接下来,乔虹的嘴型是对上了,可声音就像不是从乔虹嘴里发出的。他叹口气。“啪”地一声把机器关上了,挥了一下手,冲着一些等待录音的演员说:今天就到这里吧。乔虹走的时候,回了一次头,声音很轻地说了句:对不起。乔虹在那一刹那,眼圈里漾了一层很晶莹的东西。他沮丧地坐在监控台上,恨不能一拳把眼前的机器砸个粉碎。
李摄像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扔给他一支烟,他瞅也没瞅便把烟点燃了,他闭上眼靠在椅子上。李摄像把衣服往肩上一搭瞅着他说:走,到我那去解解闷。章立早睁开眼看了眼李摄像,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可他并不想动身。李摄像不由分说拉起他就走。他只好不情愿地跟上。
他坐在李摄像的摩托车上,李摄像像个骑士在马路上左冲右杀。摩托车带起一股风掀开一位骑自行车女孩的裙子,女孩在那一瞬间露出两条光洁的大腿。他看见李摄像在反光镜里的一张笑脸,同时听到李摄像嘀咕句:她没有穿内裤。他心里笑了一下。
摩托车离开了北三环,再往前走行人就少了。他知道李摄像前两年在郊区新建的那个小区里买了一套公寓。李摄像以前并不在电影厂搞摄像,而是搞广告,那几年李摄像扛着一架破机器几乎跑遍了全城所有的公司,每天晚上电视里的广告差不多都是他拍下的。几年下来便有了一些积蓄,买了这套公寓后,他就找到他说:不搞广告了,那玩意没蚯毬意思,我要搞艺术。章立早拍了一下李摄像的肩膀没说什么,两人是中学时同学,后来上大学时,章立早学的是导演,李摄像学的是摄像。一个摄像半个导演,章立早早就想拉他一起干了。李摄像笑着说:就算我重新归队吧。
看见一片菜地的时候,摩托车减慢了速度,公寓盖起来时间不长,周围的配套工程还没有完全建成,一条马路坑坑洼洼的,终于摩托车在颠簸中停了下来,这是一套七层楼房,奶白色,看上去很干净也很舒服。李摄像就住在最顶层,他说顶层清净。
客厅很大,直通阳台。阳台和客厅间拉了一道门帘。章立早坐在沙发上点燃支烟,他以前曾无数次地来过这里,刚离婚时没地方住,他一直住这里,每天出门都是李摄像用摩托车把他送出去。李摄像一闪身钻进帘子后,兴奋地隔着帘子冲他说:哥们儿一会儿让你开开眼。你别神神鬼鬼的,章立早心不在焉地说。他知道李摄像以前也曾结过婚,后来离了。以前李摄像的妻子他见过一两次,长得还算好看的那一种,后来拍过两部戏,也属于在剧中友情客串的那一种,后来认识了**一个音像老板,后来和那个老板去了**,再后来就和李摄像离了。听说一到**就红了,随便看一部**拍的三级片都可以看到她在床上卖力的镜头,据说已经挣了一笔可以买下大陆任何一家饭店的钱了,前一段时间听说,她不想在**拍床上的戏了,准备回大陆搞房地产,这玩意弄好了更来钱。
李摄像自从离了婚便再也没有结婚,从前章立早曾经劝过他,每次和他说,他总是不屑地笑一笑说:何苦受那份折磨呢,一个人不也挺好。他这么说,章立早便不好再说什么。
哥们儿快来,戏开始了。李摄像亢奋地在阳台上叫着。
章立早不明真相地走过去,他一拉开通往阳台的门帘,就看见宽大的阳台上摆了一架坐式摄像机。这东西摆这干什么?李摄像说着:一会让你过把眼瘾。你看,戏快开始了。章立早在监视器里看到对面公寓客厅里一个只穿三角裤的洋人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黑色的酒;从里间走出一个女人,也只穿了件三角裤。女人坐在洋人的大腿上,端起一杯和洋人手里一样的酒喝了一口。李摄像说:今天将会又有一个女孩变成了女人!他听了李摄像的话,觉得似乎有些悼念的味道。接下来的画面他便不想再看了,他调整了一下镜头,只看见跌在地毯上的两个酒杯,酒杯在红色地毯上翻滚着,黑色的酒液慢慢地在红色的地毯上扩散着。他心里有些堵得慌,不知怎么他就想起了前妻肖南芳,还有乔虹,幼儿园的小葱阿姨以及他认识的所有女人。此时他想摔点什么东西。
他觉得李摄像搞这种游戏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起身走回客厅,长长地打了个哈欠,顺手把空调打开了。室内的温度一点点地下降着。
李摄像也随身跟了进来,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酒,倒了两杯,酒是白色的,很清纯的样子。他喝了一口,却没品出什么味。李摄像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无聊或性压抑什么的?他仍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
其实我也是偶然发现的,那天我想拍日出,结果就发现了这种秘密,挺有意思的,有些戏,没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李摄像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酒。他看见李摄像的眼圈红了一下。他想起了李摄像的妻子,那个长得挺不错的女人。
你想她么?他这么问,话一出口便有些后悔。
李摄像又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酒,喝了一大口,喷着酒气说:人呢活这一辈子就他妈那么回事,一切都跟演戏似的。
他听了李摄像的话,眼前又一次闪现出:大漠。落日。驼队……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在他周身蔓延着。
太阳在西边朦胧起来,有两条斜阳透过玻璃照在他的脸上,此时这里很静,只有空调冒出的冷气“嗞,嗞”地响着。他伸手关掉了空调,把阳台的窗子打开,一股菜地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他打了一个喷嚏。他看见菜地里一个小男孩赤着背在追一只蜻蜓,那只蜻蜓忽高忽低地飞着,男孩蹦蹦跳跳地在田埂上奔跑着,他想起了黑子。
他不明白黑子才五岁的孩子竟有时成熟得像个小老头似的。以前他和肖南芳没离婚时接送黑子总是肖南芳一个人的事。离婚时肖南芳执意要黑子,他没太坚持,他不是不喜欢黑子,而是怕黑子跟了自己吃苦。他经常不在家,有时拍部片子一跑就是半年不着家。孩子虽然给了肖南芳,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孩子,每次从外地拍片回来,他总是要给黑子带回点礼物。有时回来住一段时间,他也总是想方设法去看看黑子。有时他为了能和黑子多呆一会儿,还没有到接孩子时间他便去了。小葱阿姨一看见他,便让黑子跟他走了。每次,他又准时在接孩子时间把黑子送回去,他躲在暗处,一直看着肖南芳把黑子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