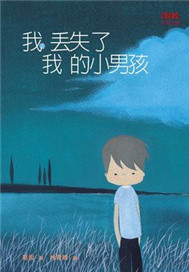盛夏,傍晚的夕阳斜斜地挂在西方,但仍然光吗四射,让人人睁不开眼睛。树上不知名的小鸟,偶然昏昏欲睡的发出几声沙哑嘶鸣,证实这世界还有一个叫鸟的动物。
蔚蓝色的水池 里宁静的没有一丝波纹,仿佛动一下都邑被烧成滚烫的开水。怒摆着娇艳欲滴的荷花,也一样懒洋洋的垂着头,惟恐他们的娇颜会被灼伤。几只蜜蜂嘤嘤嗡嗡地在草丛里嘈杂着,一群蝴蝶正躲在花朵上慵懒地晒着翅膀。
哗~~
两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纤细的小腿忽然打破了平静的画面。
两只小腿缓缓地伸进了水里,原本平静的水池忽然荡起了涟漪,一条条的波纹来回荡漾着,反射着夕阳的余晖,犹如一条条红色的彩带。
立足休憩的蜻蜓,频繁的绕在穿着虽俭朴却又非常洁净的少女身旁,仿佛是在怪她扰了本人的清梦。
那女孩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若有所思地坐着,她的心根本没在这里,不由地哀叹了一声:“哎……牧白慈啊牧白慈今日让你平时不努力,净做些穿越的梦,找工作的时候傻眼了吧。”
牧白慈刚刚大学毕业,可惜现在大学生满大街都是,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她端过盘子,站过柜台,当过迎宾……牧白慈这两年的务工血泪史都可以排成一部超级电视巨著了。
在这硕士博士泛滥的时代里,一个小小的大学生,简直就和农民工一样,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比登天还难,这一点甚至连农民工都不如。
想到这里,牧白慈不由感觉本人的出路一片灰暗。。
牧白慈朝周围观望了一下,现下是中午,公园里空无一个人。
她将双手扩成喇叭状放到嘴边,对着水池大呼道:“牧白慈--你是最棒的--加油加油加油--”
给本人打完气,牧白慈将手里那个水分已然蒸发的干巴面包吃完后,就把脚从水池里拿了出来,在地上晾干后就预备穿起来鞋子接着去找差事。
“站住--别跑啊--抢包啦--”
正当牧白慈背起挎包预备离去时,远远瞥见有两个人一前一后朝她的偏向跑过来。
前面那个年青须眉怀里牢牢抱着一个绛紫色的密斯挎包。后面的中年妇女牢牢地跟在汉子后面,方才那个声音便是中年妇女喊出来的。
掠夺!
牧白慈的第一反馈便是掠夺。
眼看两人朝她越跑越近,后面的中年妇女对牧白慈高声喊道:“姑娘!帮我拦住他!”
事实上不必中年妇女揭示,牧白慈也早已显示出一个大字拦在路地方。
年青须眉一看前面有人拦着,左顾右盼地环视了周围,惊讶地发觉仅有前面那一条路。他有一点慌了,可之后便发觉前面拦着他的仅是个体态瘦小的女孩。于是便装着胆量接着往前跑。
别看牧白慈体魄瘦小,可近两年打工训练的她还是有点力量的。
她看准汉子怀里挎包上低垂来的肩带,一把就捉住牢牢握在手里。听凭年青须眉死命地拽,牧白慈也拿定主意要与他纠缠到底。
眼看后面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中年妇女就要追上来了,年青须眉贼眼瞄到后面的水池。也不再使劲拽包,推着牧白慈就往侧面走。
牧白慈这时的心机全在应付抢包贼身上,因此她一个没当心,“噗咚”一声掉落进去了水池里。
年青须眉夺过包对着水池里喊着救命的牧白慈,吐了一口吐沫:“该死,让你没事管老子的闲事!”骂完他便抱起密斯挎包接着朝前面跑。
牧白慈在水里死命地扑腾,若何怎样方才还是很宁静的湖水,里像是长出了一双大手,任她若何抵抗便是够不到千里迢迢的岸边。牧白慈的认识慢慢开始含糊起来,昏倒以前她看到那其中年妇女先是惊慌的大呼救命,之后便惊恐地跑开了……
等牧白慈最后复原认识时,已不知晓过了多久。
痛,好痛。屁股连着大腿处那火辣辣钻心的痛苦悲伤,让牧白慈没忍住想要张嘴放声大呼,若何怎样声音喑哑再加上口干舌燥,让她的声音像是被人卡住喉咙普遍,变成了阵阵嗟叹。
懵懂的时候,牧白慈感觉仿佛有一人坐在了她的身旁,伸出手探着她的额头。
“哎……造孽哟,烧的如此凶猛,落下了根子可怎地才好。”
听到这话,牧白慈才感觉本人满身滚烫,不只屁股就算额头都疼得凶猛。
她嗟叹一声,想要张开眼睛,惊讶地发觉本人满身软绵绵的,就算将眼皮撑开的力量也没有了。含糊间,仿佛听到远处有女人的叫骂声,牧白慈心里一急,便含模糊糊的说道:“刘姨,您别怄气,我睡一觉悟了就去差事!”
之后她便堕入了无际无边的幽暗之内。
牧白慈再一次醒来,已然是三天后,屁股还是那钻心的火辣痛苦悲伤,可那痛苦悲伤之内却带着丝丝清冷,仿佛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难熬难过感觉了。但她却不敢有一点的粗心,由于只要虚微地轻轻扭出发体,那种炽热的痛苦悲伤感便会舒展她的满身。
牧白慈徐徐地撑起沉甸甸的眼皮,面前目今的所有却让她没忍住惊呼出声。
这里不是她昏倒前所属的公园,乃至不是她家或病院。
房间小的除却她身下这个只容一个人的小土炕,就仅有个脸盆和黑不溜秋的小木桌,木桌上还燃着一小半截的黄蜡。
牧白慈用力地闭上眼睛,又徐徐地张开,可面前目今的风物没有一点变迁。她再也顾不得躯体上的痛苦悲伤,伸出双手用力地揉了揉揉眼睛,还是一样,土房土炕小木桌??????
这是哪里?她明明记得本人是无所畏惧后被人推动了水里。怎么眨眼间却到达如此个地方?
牧白慈伸出手臂看了看本人的双手,却被吓的连大气都不敢再喘一下。
这哪是本人因全日差事操劳而有一点毛糙的手掌。
这双手白嫩柔嫩,一看绝非她的啊!
并且最要紧的是,这双手……好小。
牧白慈感觉本人必然是在做梦,她闭上眼睛预备好好睡上一觉。
睡醒了就到达了公园,睡醒了屁股就不会如此痛。尽管这双小手很优美,可她还是喜爱本人皮粗肉厚的手。
吱呀~
牧白慈被这个声音惊得张开眼睛,她侧过火惊讶地发觉那扇陈旧到风雨飘摇的木门被人推开了。
之后出去一个躯体轻轻发福的生疏女人。
女人身穿灰色夹袄,深蓝色的遮脚长裙,跟着走路的动作能瞥见她脚上踩着一双玄色的布鞋。她的神气看上去仿佛相当疲劳,一手端着药,一手轻轻揉着额角。
门开启之时,牧白慈透过门缝看到表面一片银白。
女人脚踩着碎步,将那碗热火朝寰宇冒着白烟的药放到了木桌上,之后又走到门前把门带上。
她走到炕边,对上牧白慈那双瞪得圆溜溜的大眼,显著地愣了一下,之后便拍了下大腿,欣慰地笑道:“牧白慈!醒了?屁股可还痛?等着,姨娘给你拿药去!”
说着,女人便匆匆地跑了出去,跑过灰玄色的木质地板时,发出的咚咚音响。
半晌后,女人哈着气搓着胖乎乎的手,再一次到达牧白慈所属的房间。
她手里拿着个白底青花的小瓶子,慢步地走到牧白慈的身前。站在炕沿边,女人伸手就要掀起她身上盖得被子。
牧白慈心里一急,扯着有一点喑哑的嗓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别……别碰我。”
女人的手僵在半空中,之后她叹着气坐在了床边。
盯着牧白慈,眼睛里是满满地疼爱:“牧白慈啊,别置气了,姨娘把药给你涂上就不疼了。丢了事情不打紧,咱可能把小命丢了。”
话是如此说,可自称是姨娘的女人却迟迟不敢伸手再去触碰牧白慈。
稳下心里的心情,牧白慈试探地叫了声:“母亲?”
只见女人方才还是颦眉匆匆额的胖脸,立即笑成了花:“唉!我地好闺女,乖乖横着别动,母亲会轻点。”
这次女人试探着拉开了牧白慈身上的被子,见她没有什么反馈才徐徐退下她身上有一点泛黄的亵裤。
牧白慈咬着牙没有再回绝,由于屁股上凉丝丝的感觉已然逐步消逝了,那种火烧火燎的钻疼爱痛,再一次让她疼的满身颤抖。
女人听见她咬紧牙关,却还是油然而生发出的嗟叹声,登时没忍住红了眼眶:“天杀的坏丫头,日夕会遭报应的!这打得……啧啧啧,真让人糟心哟!我告知过你什么来着,那贱丫头算不上好东西!你却偏偏只和她交往,廉价被人拣去也即便了,这万一落下什么根子……哎……”母亲一边涂着药膏,一边喃喃自语地嘟囔着什么。
牧白慈却一直紧咬紧牙关关,忍耐着那种让她欲哭无泪的钻疼爱痛。不用一会,她就感觉那种清冷的感觉又回来了。
之后,女人逼着牧白慈喝完那碗苦到掉落渣的药后,便匆匆忙忙地离去了。临走之时还说要给她送早饭。
房子里再一次复原了宁静,牧白慈趴在炕上再一次细细地端详起这个房间。
事实上,不必再睡觉了,她已然肯定本人不是再做梦,由于身上的痛苦悲伤是这样的明晰。
牧白慈想到一个可能,不会是她本来的躯体已然死掉落,魂魄附身到了这个古时小女孩身上了吧?
牧白慈没有这小孩的记忆。无奈之下,她只能假装失忆了。从那个现实的母亲嘴里得知。她现在生活在一个山寨里。
可能是牧白慈命运太苦的缘故,在他穿越了没多久,目前便去世了。从此牧白慈在这个小小的山寨里孤独地生活着。
牧白慈既然老天对她如此不公,那么她再也不要做以前那种乖乖女,她要做一个女流氓,搅乱这不公的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