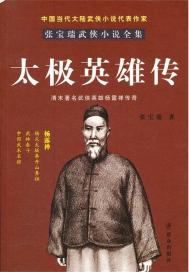→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
张謇中状元是1894年,离1905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有10年,因此,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
中国科举,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中国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荣辱,大多与它相关。一切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对这项制度都十分重视。《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曾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彀中”。骆宾王所讨伐的武则天也很看重科举,还亲自在洛城殿考试举人。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可以设想,即使骆宾王讨伐武则天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废弃科举,中国文人的群体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观。
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张謇中状元时41岁,已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逆的历史信息。他实在不错,绝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瞭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大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念。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他毕竟看到了世纪的暖风在远处吹拂,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强胜弱灭。
我们记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謇来实现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副石刻对联:
登高一呼,山鸣谷应;
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南通博物苑是中国首个私人博物馆。
一个状元,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Paradox——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义近反论、悖论、佯谬吧。其实,骆宾王身上也有明显的Paradox的,出现在他的文事与政举之间;不同的是,张謇的Paradox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他的眼光有限,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经济旋涡所淹没,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真会让一抔黄土之下的骆宾王羡煞。
近现代南通第一名人——张謇。
不管怎样,长江经过狼山,该入海了。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上海,比张謇经营的南通更走向现代,更逼近大海。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么我想,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